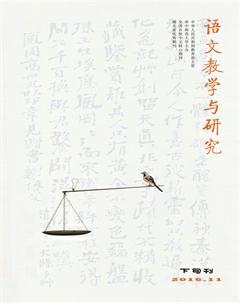记忆里的味道
陈梵瑀
在我的记忆里,有许许多多鲜活的气味,偶尔一个不注意,它们就会跑出来撩拨我的心弦。我会轻轻罩住鼻子,不想让那些我记起的味道在空气里消散不见。
我最喜欢的就是过年,不仅因为可以和家人团聚,更是因为一堆小小篝火。那堆篝火成为了我小时候为数不多的期盼的东西。
每年最喜庆的时刻,悠悠柴火香就会跑出来。
小时候每次在外婆家过年,我们就会在泥巴地上点起一堆篝火,看着火花一点点升腾,映亮每个人的脸庞。燃烧的木材会啪啦响,而燃烧着的樟木或桔木特有的香气更是让人心里发痒。这个时候大人就会拿出一堆小红薯放在火底的沙土里炆。烤熟的红薯香味连沙土都盖不住,我们这些孩子就被勾得忍不住用火钳扒拉沙土。“出土”的红薯不加油盐佐料自带诱人清香,待它在空气里冷却后,我们就会迫不及待地伸手抓着吃,黑黑的炭灰糊在脸上也顾不上,吃完一个再拿一个,生怕自己抬手擦擦脸,“珍馐”就不见了踪影。吃完后的“小花猫”还会忍不住舔舔手指,非要把手指上的残渣舔得干干净净才罢休,那个馋样逗得一家人哈哈大笑。
我想我记住的,不仅仅是那一股柴火香,红薯香,更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欢笑打闹的小温馨。现在的外婆家,早已铺上了冰冷的厚厚的水泥,再也不能生起篝火。而家人也只会窝在家里烤火箱,没有欢声笑语,充斥在耳边的,是哗啦哗啦的麻将声,是叮叮咚咚的手机提示音。我记忆中过年的小欢乐,就这样被现代化科技化生生割裂,支离破碎。我唯一记住的,也只有那一股淡淡的清香,再无其他。
姥姥的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像极了艾叶的香气。大概是得了老年痴呆的姥姥常常把大小便拉在身上,为了让洗过的衣服没有味道所熏的艾条。妈妈曾笑说那是姥姥身上的“老人香”。嗯,可是不管是什么味道,每次只要我依偎在姥姥怀中,她用枯瘦的手轻轻梳着我的头发,为我念一首不成调的童谣的时候,那种香味就会不自觉地跑到我的鼻翼,让我留恋不想离开。
但是后来姥姥病了,躺在床上的日子越来越多,我依偎在她怀里的日子也就少了。偶尔学校放假,我会靠在她肩上,陪她在阳台晒一会太阳,听她说说往事。这个时候,那种香味就顺其自然地跑到了我的鼻子里。有时候浓郁的让我眼睛发酸,因为香味越浓郁,也就意味着姥姥的老年痴呆越发严重,生活越来越不能自理了。
不过遗憾的是,我既没能留住她怀抱里的温暖,也没能留住她身上的味道。偶尔湿了眼睛时,我可以记起她笑起来弯弯的眉眼以及她身上淡淡艾草香。
记忆深处,我还记得奶奶亲手晒的被子里阳光的浓郁味道;外婆家菜地里泥土的清香味道;妈妈早起为家人煲的汤的淡淡味道;爸爸指尖边为我削过水果留下的甜甜味道;外公二胡弦上的悠悠松香……它们在平常的日子里不会很浓郁,却在被我回忆起时,喷涌而出,噬人心神。
我长大,我走入水泥钢筋布满的城市,我走入离家越来越远的社会,步子越迈越快,记忆却越来越淡。只有偶尔泛起的回忆伴着一股香味,绊住我匆匆的步子,要我回头,看看我那曾经年少幼稚,曾经天真烂漫,曾经美好如今再也回不去的时光。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可是有的味道,我再也找不到。
长大的我,似乎已经遗失了太多美好……
(导师:林雪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