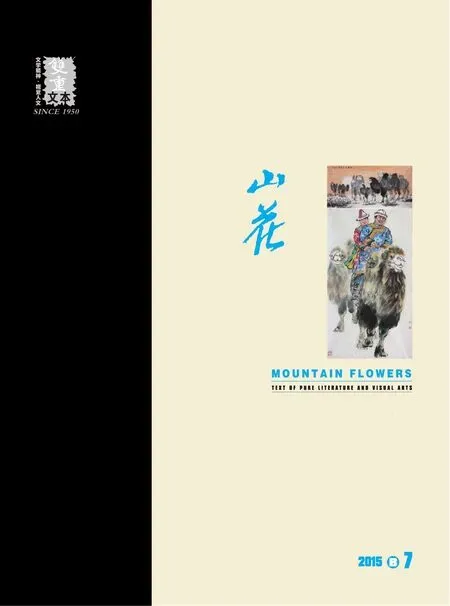洞庭路上的有轨电车
焦红琳
洞庭路上的有轨电车
焦红琳
1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下班后,我会坐电车回家。电车吸引我的,除了定时定点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慢。
我不喜欢开车,就是不想太快——
在车上我喜欢倒坐着,看窗外的风景前行。那样便是逆行,似乎是真实的穿越。过了第九大街,车里的人已寥寥无几,我摘下耳机,也不关掉声音,因为已不会影响到别人。
今天在我的前面,不,应该是后面还有个女人,因为她和我一样倒坐着。
心里希望她回下头,我好看看她长什么样。她越不回头,我的好奇心越强。可惜一直看到的是背影,她戴一顶米白色的毛线帽子,长发分在两边,一件卡其色的羽绒服。
十三大街的终点站,我们一起下了车。这时我才发现她拉了只行李箱,戴着防雾霾的口罩。我重新戴上耳机,三两步赶在了她的前面。还是能听到她皮箱咯嗒咯嗒的声音。下车的人太少了,况且是末班车。
太冷,我已完全没有心思关心她的相貌了。况且路上很暗,路灯昏黄不明,它们和天上可数的几颗星星一样,像是被冻得集体瑟缩起来。
我竖起大衣领,双手插兜,大步向前走着。没想到那个咯嗒咯嗒的声音一直在身后跟着进了小区。这没什么奇怪,小区内有几十栋楼。
我三两步跑上台阶,借着手机光摁楼宇门的密码——门厅的灯坏了。当我打开门的时候,那个声音竟然从行李坡道上绕到我的身后,我大惊,心想,这么巧啊!转念一想,三十多层,每层三户人家,共有一百多户,不认识太正常了。
出于礼貌,我开着门,等她把行李箱提了进来。电梯里,同样出于礼貌,我为她摁着电梯,感觉她的行李箱很重。
我按下19——我的楼层,她并不按也不说话,只是向我点点头,这时,她才把一直戴着的口罩摘下来,我看到一张很是年轻、白净的脸庞。
到了19楼,我不再绅士,大步跨出电梯。掏钥匙开门,我住的是1903。心想,这是两梯三户的房子,她是1902的,还是1901的?
搬来三个多月了,我一直没见过1901家的人,只见过1902家的。她或许是串门的亲戚朋友?管她是去哪儿的!我用力地关上了门。
上卫生间、换衣、打开电视……把自己交给沙发。电视里正播着,最近几天将遭遇五十年来最低气温。竟然听到了轻轻的叩门声。没错,是在敲我家的门。
会是谁啊?公司的人会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找我?不可能,他们会打电话的。
我大喊:谁啊?没人应答。再敲,我从猫眼儿里看了一眼,吓了一跳:竟然是那个女子!
2
我没有贸然开门。
隔着门高声问:有事吗?
门外回答:我……有事要和你说。请问,能不能打开门?
什么事?我安慰自己,她不过是一个弱弱的年轻女性,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一个大男人怕啥?
可是打开门的那一瞬间我有点后悔,万一她是专门跟踪我来的?她有什么企图?
开门后,她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退到自己的行李箱旁边,可能是为了消除我的疑虑,干脆坐在了上面,还向电梯门靠了靠。
确实,我的疑虑有所消减。
我希望1901或1902的房子里能有人出来,哪怕是出来倒垃圾,好为我做个人证。我又后悔刚才没悄悄把手机的录像功能打开……
她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打扰你的。我……
我没有迈出门槛,也没有放开门拉手。灯熄了,我立刻大声喊了一下,她原地没动,脸色看上去更白了,整个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神情,我的心竟突突跳了起来。
我尽量压制着内心的恐慌,说:你到底有什么事?
她说:我不是坏人,这是我的身份证。她递给我,眼睛盯着我,目光中有一丝的怯意,又有一丁点儿的犟。最初是一只手,后来另一只手也伸过来,就这么两只手端着一张小身份证,在我的眼皮底下站着。
我不接,也不正眼看,只是盯着她。我为什么要看?我的声音很粗鲁。
她说,请你看一下吧!她站起来,双手几乎碰到我的衣服。
身份证的照片比本人看上去更漂亮一些,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身份证照片。尤其这双眼睛,如果排除双胞胎什么的,应该是本人了:1991年生人。我顺便看了一下名字:温清婉。
我……请你能不能……给我一杯热水?她嗫嚅着。
我感觉自己的心那么地动了一下,没想到她开口说的竟是这样一句话。是的,这确实是最冷的一天,想想她在外面待了有二十多分钟。这个楼的设计有点特别,两部电梯中间是一个公共过道,过道的两边不是封闭式的,说白了就是一个小天桥。也就是说,这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她等于是在户外。
她递给我一只Hello Kitty图案的杯子。我转身进屋,顺手带上门。
温清婉,温清婉,这个名字我听过吗?外面那么冷到底要不要让她进来?
我盯着厨房墙上的一幅粉色的贴画,上面也写满了Hello Kitty和它的头像,一住进来就那样贴着,我也懒得理它,反正从来不在这里开火做饭。
她接过水杯,双手捧在手里。返回屋——我其实是想加件衣服。
感觉她在身后猛地站起来,伸手拉住门。我紧急回身,她几乎撞在了我的身上,上身紧贴在了我的右臂上,我感觉碰触到了一种柔软。但我还是侧了下身子,鼻尖正好扫到她帽子前露出的发丝,一股清清凉凉的香味,淡淡地被吸到我的肺里。一瞬间我的心“万马奔腾”起来。她缩了一下身子,但没退后,像犯错的孩子,赔了笑脸,但那个笑脸是很勉强的。请听我说一下好吗?一只手拉住门,其实她的手已放在我的右手上,我的右手依旧拉着门把手。
我说:你该不会是有意跟踪我,才来到……
她打断我,急促地说:绝对不是!请不要误会。我其实有很多话要和你说,太多了,我一下子想不起来说点什么才能让你相信我!
太多?和我?这是什么情况?哪里出岔子了?我被这个几乎贴到我怀里的陌生女子弄得迷迷糊糊。但立刻告诫自己不要头脑发涨,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你这个房子是不是两室啊?请你去小卧室的床头柜里看看是不是有一本《日本蜡烛图》?她一连串地说着,一反最初的柔,慢。在我的眼皮底下!完全是仰视。我有点……享受这种感觉?《日本蜡烛图》?我脑子飞快地转动着,股票?期货?贵金属?投资分析师?可她怎么会……这也太意外了!
她盯着我,就是目不转睛的那种,眼眶里湿湿的,反了几点光。我想干脆利落地说,没有!却没想到半道结巴了:没……有,我住进来之前,中介……都收拾过了。
她眼里的光瞬间消失,我似乎感觉到她吸了口冷气。喃喃地,又似乎是自语道:那就是说,那些被子、衣服、书什么的都不在了?
我的心软了下去,说:嗯……应该在吧!有一些包裹、箱包都放在那个房间。
她呆立在那儿,好像还在费力想那“许多”中的一点儿什么。对了,客厅里那幅画……《夜间露天咖啡馆》还在吧?《夜间露天咖啡馆》是我亲自装裱的。
我回下头,从这个角度是看不到墙上那幅画技还算不错的临摹画的,因为我把它挪进了卧室。
这女子没什么阴谋,只不过是我之前的房客罢了!我完全松懈下来了。
转而有些许的自责:算了,自己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一个漂亮的女子在我的家门口瑟瑟发抖,我却在这里不住地审问,况且我自己也冻得够呛。
但是让她进来,意味着什么?
3
看看表,九点。接待一位客人还不算太晚,不是吗?
我帮她把行李箱拉进来,确实不轻。又给她加满热水。
过了一会儿,她不再发抖。对我说,谢谢你信任我。我想……用一下厨房?
我当然很意外。但嘴上说:随便用。所谓的厨房除了有水、有火,什么都没有。冰箱里连一颗鸡蛋都没有。
她脱去外边的大衣,似乎比想象中稍微丰满了一些,但不影响她身材的匀称。
她走进厨房,站定,四下看了一眼,转而打开一个柜子,从里面找出一条碎花围裙!抖了抖,系在身上,抬头往上看,顺着她的眼光,那里是和抽油烟机同高的一排壁柜,她踮起脚,打开其中一个,里面竟然有几个放着各种杂粮的小罐子!她踮起脚,再踮起……最终也没够到一个。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才意识到自己走神了。我上前,站在她的身后,前胸贴着她的后背,她本能地抖了一下,想躲开,但空间太小……刚才在门口时的那股气息又钻进我鼻孔,刹那间,我竟想入非非。
这到底是不是自己住了三个多月的家?
她只用了一种食材,小米。
很快两碗小米粥摆在了桌子上,她又从自己的皮箱里拿出一袋红糖,各放了一点儿。很奇怪,我们竟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了桌旁,喝着热粥,尽管我只是象征性地喝了一小口。屋内蒸汽袅娜,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甜甜的米香味,这可是我的住所内从没有过的情景,我觉得自己……还好是清醒着的。她第一次仔细环顾屋内,我见她看墙上,我告诉她:哦,那幅凡·高的画……我用手指我的卧室。我的卧室有点零乱,我关着门。
她又披上大衣。说,之前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年。半年前,我们出门……她移开目光,眼神似乎有那么一点儿飘忽。接着说,后来出了点意外……我的手机丢了,很多号码,所有的都找不到了,又没能及时赶回来……接下来一直低着头,也没喝粥。
沉默了那么几秒,她抬起头:我本来只是想碰碰运气,看看这个房子还在不在了。她说这两句话时稍提了语速,似乎要弥补那几秒的空当,并且脸上露出笑意,我这才发现她的牙齿不是想象中那么整齐,门牙旁边有一处两颗挤在了一起。
我也笑了,房子又没长腿,能跑哪儿去?
我盯着厨房那张粉色的贴纸出神,她也往那边看:哦,多幼稚!以后肯定不会这样了。
她的脸不像刚才那么惨白了,但依旧没有血色。
窗外飘起了清雪,西北风越刮越急,后来竟然呼呼地嘶鸣起来。这样的黑夜,应该是拒绝所有外出的。眼前是位有一双漂亮眼睛的女子,而且略带病态,我无论如何也不忍心把她撵出去。
我说反正这里有你的被子,你要是不想走的话,就在这里休息一晚?
她睁着一双大眼,亮晶晶的,很纯,显现出笑意。是意外的惊喜,还是在她意料之中?走神儿般地盯了我片刻。急忙说:谢谢你,谢谢你信任我。
我笑笑,绅士般地。说了句:你随意吧。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靠在门上,盯着那幅画,我不懂油画,但还是喜欢在自己的居室内布置一些这样或那样的色彩。上面那片深蓝色的夜空,有些神秘,感觉隐藏了一些秘密的符号,再转眼细看却又什么也看不到了。我问自己,假如这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我会留她吗?当然不会,可是……我没法自圆其说,弄得坐立不安。我看到被扔在床上的暖宝宝,那是新上任的女助理买给我的。
门没有插上,开着一条缝。我敲了下门。
她问有什么事吗?我把暖宝宝递给她。说,屋里冷不?冷的话,可以把空调打开。
她已把那些打包的东西拆散开,坐在床边整理一堆书,见我进来,急忙站起来说“谢谢”。眼睛红红的,略显出泪痕。
4
清晨,我踏上电车,像往常一样倒坐在座位上逆行,看昨天消失的风景再次一一出现。有时我在想,如果有一项工作,不,是有一种生活,以一种速度逆着地球自转的方向前行,我们会不会越来越年轻。
女助理的笑脸越发动人。桌上,一杯咖啡,微弱的热气袅袅娜娜,怎么看都像女助理出门前扭动的腰肢。咖啡的香气,很是诱人,轻呷一口:可惜是速溶的。
晚上,我像昨天一样又回到了家里,不同的是没有一个女人再尾随着我,也没有一个女人在不久后来敲我的房门。
我的房间,被子散在床上,电脑、衣服、书桌、鞋子都是我早晨临走时的样子。
除此之外,客厅、厨房、另一间卧室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但是那些被子、衣物什么的并没有全部被拿走。有一个揉皱的纸团,扔在垃圾桶里,展开,是一张男子的侧身速写,男子面部轮廓分明,瘦削,梳着一个很长的马尾,如果散开,应该是长发及腰的效果,一件开衫上衣,自然敞开着……
男子侧身坐在类似制作音乐的机器旁,我猜想是DJ那种吧。
昨天她是不是捧着这张画落泪?
一个漂亮的陌生女性在我的家过了一夜,我们竟然什么也没发生……就是那一段时间,我总有种不真实的错觉,自己是不是不正常了,晚上下班后,我总要去那间屋子看看,那幅速写我没有扔,它应该是真实的……
我从南方的内陆,来到北方的海边。沽,小海也。算命先生说我五行缺水,小海也是海,离海近一点,更近一点,一定会交好运的。以往过年回家,家人对我总是那句话:一个大男人,还是那么慢性子,以为全世界都会等着你,凉了的黄花菜好吃吗?
我忽然想到我们竟然没互相留下联系方式,除非她再来这里找到我。
说心里话,我内心一直等待她的再次造访。但是过了很久都没有。我在饭桌旁不止一次地设想:我们就着热粥交谈,谈论着她口中的“我们”。
画上的人是谁?是不是那个她口中说的“我们”之一?
我甚至设想她慢慢告诉我,他们相识的过程、方式:我有时会在豆瓣上看看人们读什么好书,有一阵子人们都在找一本书,然而一直没有找到。过了一段时间,有个人说他有,为了表示客气,我们就聊了几句。没想到我们是校友,他先我几年毕业,但我们不是一个专业。没想到我们竟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聊到后来我们见面,再后来我们租了现在的房子,再后来我们一起出去,再后来就……出了……那次意外。甚至会想象她对我讲述这些时的神情。
我甚至还臆想她会真的再次来找我,约我到时尚路的“牛子牛”书店,边看书,边吃街对面一种名叫“潘朵”的手工冰淇淋球。
我会在她专心吃冰淇淋时突然问她:那是本什么书?
她略思考一下说:《沙岸风云》。你要吗?
我当然会说:我也想要。
很多次我甚至没有在外面吃晚饭。回到家,用那些小米,回想着她的样子,自己煮粥。但怎么吃,都没有那晚的香味,我把这个归究于没有放红糖的缘故。甚至总在晚上提醒自己明天买一袋红糖回来……
我终于忍不住,从为我租房子的工作人员那里找来了租房合同。找到房东的电话,房东并不买我的账,因为和他签合同的人不是我。我只好让女助理去办这件事,帮我查找一下房子的前任租户。

欧阳可人 天桥
5
公司每年的预算安排里,有一笔资金是要用在公益捐助方面的。当然就是税前可以合理扣除的部分。
通过几次开会商讨,我们决定还是就近解决。身边未必没有需要帮助的人,何必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去贫困地区。据以往的经验,有些地方的官员们很讨厌这种事,他们一点好处也捞不上,还要陪吃陪喝陪走路。其实我们只是想让他们给牵一下线的,那样双方会省去不少猜测和顾虑,便于尽快达成共识,根本不用他们陪什么。有一次,通过一个朋友介绍,我给一位乡镇学校女校长打了电话,女校长不屑一顾的语气——边通话,边嘴里咀嚼食物,令我大为光火。虽然是公司的资金,我这个曾经的财务处长,现在的行政处长也想至少捞点尊重和面子吧!
于我们公司,也就是捞几张照片或几段视频,贴在公司的会议室墙上、放在公司的网站上。
为了真正地把善心行到实处,那一阵我和另一个部门的同事,马不停蹄,接连考察了几家福利院。最后我们把目标锁定在附近的一家儿童福利院,这家儿童福利院的硬件设施还不错。实在拿不准到底是给孩子们怎样的捐助,才是他们真正的所需、所求。是给每人解决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还是把资金给他们?当然我并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院长。
我们从最小的育婴室开始,到幼儿的小班、中班、大班。孩子们高低不一,大小当然不一,买衣物绝不是事先想的那么简单。
大一些的孩子都去附近的学校上学了,剩下的就是还在上幼儿园和学前班的孩子。
育婴室里还有吃奶的孩子,我想这些孩子至少应该得到安全营养的奶粉吧?
同事说,我们不可能想那么周全,即使能想的都想到了,到了这里不见得能执行得那么尽善尽美。你能保证保育员们不会把奶粉给偷了、换了?
我说,是的,尽量做好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可能负担这些孩子的全部费用。最初的热情又被现实之冰水降了温。
从一间育婴室出来,路过另一间,向里随便望了一眼,就这一眼,我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看看院子里来往的几个粗手大脚的护育员,脑子里闪现的是一双柔弱纤细的手。觉得自己可笑。
回到公司,电脑上贴了一张便利贴,上面是一个人名:陈永强,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我迫不及待地按号码拨过去: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停机。查了一下,是本市的号码。
因为前一天大致有了意向,隔天我们又来到那家福利院,以便最终签订一个捐赠的书面文件。
借着上厕所的空当,我在那间育婴室里竟然又发现了那个背影。
是她,没错。她正抱起一个七个月左右的婴儿,因为我实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能大致估计月数。
我悄悄拉过一位护工。她说,自己不是太清楚。又说,她肯定不是这里的职工,应该是志愿者,最近一直能看到她。不过她好像不是一般的志愿者,这里有一个孩子可能是她助养的。
我没再多问。
回到院长室,我有意往这个问题上转,我问,个人怎么资助这里的孩子啊?
院长说,除了志愿者外,也可以专门资助某一个特定的人。
我问,能随时来看吗?
院长又说,原则上是要有规定的时间。
但是有的志愿者对某个孩子特别关注,和门卫混熟了,也会随时来看的,不过这种情况很少的。
温清婉,这是她的秘密吗?
6
公司给我配的助理,是刚从另一家公司跳槽来的。很年轻的女孩,像所有现在的女性一样,同时有高学历,高智商,大胆、张扬,她毫不掩饰对我的好感。
说实在的,我很难分得清她对我的好是因为工作的上下级关系,还是我本身的魅力所在。
我不想和她浪费时间和那份感觉,也就懒得主动理她。但毕竟她是个美女,又有着细腻的皮肤,姣好的身材……有时还真是揪扯不清,我打心眼儿里不喜欢这种关系。
快餐,看上去都是色香味俱佳的,非常诱人,但当你吃过一次后,总有一种被表象欺瞒的感觉。我知道这样想有点无耻,可对于她我何尝不是另一份色彩颇有点诱人的快餐?
自己不主动,又不喜欢过分主动的女孩,我到底想要什么呢?我自己也不清楚,还是因为有过一些不足为道的经历了?
我不喜欢MSD(Modern Service District)里不分白昼的灯火辉煌,二十多部电梯总在忙碌之中。当然任何一家有野心的公司都尽力进驻这里,以彰显其实力。
好在我有自己的格子。好在我有我的电车。我依旧是每天沿着电车的轨道回到我的世界,同时和这个世界隔开。从一大街,到十三大街,我感觉就是另一个世界了,没有MSD的富丽、宏伟,同时让那种过分逼人的现代气势散淡开。
我一直在想,要是那天我们发生点事,她会不会这么一去就杳无音信呢?我们为什么没发生点什么?当然我是讨厌一切快餐式的,从骨子里讨厌。
我无处排遣心里的烦闷,对女助理大发脾气:这么简单一点事儿,怎么就办不了?拿个空号来糊弄我,之前的工作都是以糊弄为主?
女助理愁苦地对我说:对不起!那确实是我查到的真实情况。有那么一瞬间她几乎快急出眼泪了,我并不为之动容。说实在的,我感觉她那份痛苦和急切里表演的成分多了点。相比那夜的温清婉,那才是真实的。
女助理沉默着,似乎是在偷读我脸上的表情。赶忙说,我知道这个号码已经是个空号了,明天我带合同再去区房管局咨询,看会不会有收获。
不仅晚饭吃不进去,白天的工作餐我也吃得很少了。
我一天比一天烦躁起来。
竟然还流起了鼻血,总是和衣服、金属门把手、出租车车门擦出莫名其妙的火花,我被电到了!
有时一天洗两次澡,还是觉得浑身干燥难忍。后悔自己不该从公司总部来到这个海边的分公司。直到有一天助理对我说,一位女士打电话找我:问哪里不说,只说姓温。我很奇怪,在这个城市我认识的温姓女性只有一人,她怎么会找到我的公司?
我忽然觉得自己一下子温润起来,整个身心就像沐浴过一场南方的春雨。
是她,温清婉,约我吃饭。
我特地去“金手笔”做了一下头发。
这阵子以来,我心底所有胡乱想象的那些……是不是机会来了?我脑子里想着她那天坐在行李箱上,很疲惫,甚至一副病态的样子。
回转寿司。她说去这里,我没有反对。反正是她请我,地点她定很正常。她又说离我公司近。
很久没去这家店了,自从他们闹出食材过期的丑闻,我就没再去过。
7
她把茧形大衣脱下来,随手搭在后面,里面穿着一件淡紫色连衣毛衫,宽松,随意。一条围巾长长地从颈上搭下来,颜色和毛衣很协调,每一件衣服原本都不怎么出色,经她这一搭,就显出了几分素雅,竟无端地显出几分落寞。比半年前明显瘦了很多,妆是精心化过的,粘了假睫毛,怎么看都像一位当红的明星,却说不出是哪位。相比之下,那晚她不仅是素面的,而且显出病态的憔悴。
见我盯着她,落座后对我微微一笑,我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吃寿司我一般会吃很多,原因是芥末酱。我有一个特异功能,不知道为什么对芥末没有免疫力。
我的吃法会吓到很多人,那天奇怪,没有吓到她。回转台上的芥末有两次转过来我吃过的空瓶!
她对我的行为一点也不吃惊,竟主动示意服务员给我加芥末酱。
吃寿司有个好处,就是不管怎么吃都不会杯盘狼藉。在这里吃饭,确实关系应该是很熟的,但我心里当然明白,我们并不是那么熟。也可能是我们“同居”过,放得很开。一点也没有拘束的感觉,所以吃起来毫不造作,直到旁边的盘子摞到看不到对面我才住嘴。
我说你看起来,神情状态比之前好很多,更漂亮了。她笑着说:谢谢。你也很不错。没想到你这么爱吃芥末。
我说,是啊,本来是想要刺激点的,可是发现没有什么刺激的可以刺激到我。越对它的刺激充满幻想,越是达不到幻想中的那个感觉。
她笑笑,说,这只能有两种原因:第一,你天生就对这个没有免疫力;第二,吃得多了,味觉对这一感觉失效了。
我说,要是两个原因都不是呢?
她说:这种情况当然不存在。她轻呷了一口酒。放下杯说:吃东西,现在多少人是为了果腹?当然都是吃感觉。至少你还是有感觉的,或许你只是想回味它曾经给你的感觉。没有感觉吃它就没意义了,这里有这么多可吃的,更有你喜欢吃的,你绝不会是用它果腹。没有感觉说明你在陪我。陪我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对我有感觉;另一种是出于礼貌。
我的脸肯定红了。大概、可能是青酒的原因……一瓶青酒她只喝了一小杯,其余的都被我喝了。
你希望我是哪种?我说。我想从她的眼里找点特别的东西,但是很遗憾,没有。
她低头,打开包,我抓住了她拿钱夹的手说:我来。我的手有意在那只绵细的手上多停留了一会儿。
她抬起头,对我又是一笑,只是这一笑,从那双深深的眼睛里还是没找到我想要的。说好的,我请!她说着,轻轻推开我的手。
我把最后的也是唯一一杯青酒喝进嘴里,感觉,青酒的温润正滋过全身。心里想着,温清婉,温清婉,有两个三点水的温清婉。
这时忽然过来一个很另类的女孩儿,和她打招呼:温姐,好久不见,你也在吃饭啊?女孩扫了我一眼,并不理会我的点头致意。
我盯着女孩子在远处落座后,又起身上洗手间。
我也上洗手间。回头看看温清婉,她正低头摆弄手机。
她说她住在旁边的小区,谢绝我送她。
只把一个厚厚的文件袋交给我:这是我托你的事。
很显然,已过了电车的末班车时间。我希望她邀请我,也希望她像上次那样跟上我,可惜这两种情况都没发生。我的心里很落寞,这份落寞和一瓶青酒带给我的骚动让我越发难受起来。
我打车回到了十三大街。直到躺在床上,我都感觉自己是迷迷糊糊的。
我在卫生间门口堵住了那个女孩儿。
美女,你是怎么认识我女朋友的?
女孩儿愣了一下:女朋友?你是说温姐?她上下打量着我。那温姐住医院时怎么一直没见你?
医院?
是啊,温姐是从急诊转到我们科的,那天我正好值班。据说是被什么人打了,左臂骨折……后来早产。
你真的是她男朋友?她被人打时,你在哪儿?住院期间一直没见你!新交的吧?还是小三儿?
我张口想辩解,却不知道说什么,但我的脸一定红了。
虽然七个月早产,孩子倒是挺好。但子宫没保住。
那……孩子呢?
女孩儿照着镜子整理头发。
后来好像听说孩子没了,死了还是被什么人抱走了?那几天我正好休假,详细的我也不太清楚。
我问:后来,怎么了?
女孩扔了纸巾,不屑地回头看我一眼,她不是你女朋友吗?问她啊。
女孩的这些话翻来覆去地在我脑子里出现。我竟然越来越清醒了。
8
下车。打开文件袋。
请求你和我结婚。后面就是一串电话号码。文件袋里有一沓文件,这是最上面的一句话。
看这一眼,我觉得好笑,不就是向我求婚吗?至于这样?好像大笔的交易,还附这么一沓文件。
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吸引力的,便沾沾自喜起来。我把这些扔一边,站起来照镜子。
拿起手机,我想给她发条信息:太夸张了吧?发送键却没有摁下去。
眼前出现她把这些交给我时的样子:好好看,不急于答复。
莫非她很有钱?要做婚前财产公证?
好奇害死猫。又往后翻。
我要借你半年。借的方式,真结婚,假夫妻。“假”字是加粗加大的。
绝不是儿戏。我,温清婉,现年二十四岁。(身份证件及其他相关重要证件附后)
这是一个交易,与一切和婚姻有关的财产、感情均无关系。
我的目的,领养一个孩子。
因为我们国家法律不允许单身女人领养孩子。
等婚姻存续期内条件达到领养孩子的所有要求,并办理好所有领养手续后,婚姻自动取消。婚姻中、离婚后,你不负有任何抚养义务,这些相关细节都会详细说明。
很严肃,万望谨慎思考。
后面还有一些证件,什么硕士毕业证,本科毕业证,技术职称证书,中级的、初级的不小一摞。甚至还有收入证明,存款证明,她老家父母的收入证明,这些可能是要说明她有绝对的经济能力抚养孩子。
最后面是一份离婚协议,其中一项,女方自动放弃男方应付的任何形式的抚养费。被用红笔圈起来。
所有涉及时间的地方都是空白。
她把什么婚前财产,婚后财产的规则,非常详细地写了进去,总的来说,是绝对维护我的利益。
最后强调:不让你在经济上有任何亏欠。不干涉你的任何私生活。
你放心,是我求你帮忙。我绝不会要挟你。我会以你的名义存一笔款,离婚的同时你就能得到这笔资金。求你先别急于拒绝。三思、慎思。
我用一晚上的时间看完,用半夜的时间思考。
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真他妈的莫名其妙!我叨念着这四个字沉沉睡去。
9
第二天,到公司时比往常迟了半小时。
先是一个“90后”的小子,闹情绪过来辞职。对这些孩子我一般都是先安抚,说服教育那是不能沾边的。
助理说,越来越糊涂了,这个房子是第一次出租,根本没有什么前房客。我都懒得理她了,面无表情地扫了她一眼。她或许见我对此事一下变得冷淡而大惑不解,但又有些诚惶诚恐,我明知道是冤枉她了,心里没有歉意,反而有一点报复的快感。
过后财务部的人送来支票,说是给福利院的资金两天内到位。除了资金外,还有一部分实物。因为按照规定,交付的过程要有一个简单的仪式。我就带着行政部的几个人又来到了郊县的那家福利院。赠送方,接收方,拍照合影,一一按流程进行。
我又找机会来到了那间育婴室。一个年龄稍大的阿姨,正在里面收拾。
我说我很喜欢孩子,想看看这些孩子。大部分孩子都有点残疾。
他当然是一个非常健全且漂亮的男婴,正在婴儿车里抓玩一个玩具。我蹲下来逗他。
我说这孩子真漂亮。阿姨说,是啊,多可爱。这么好的孩子硬是被扔到大街上,那天一早,是个清洁工抱来的,他说一个女人在路上捡到的,交给他让他抱到这里来。我们在孩子身上什么也没找到。这父母是存心不要孩子了,连个纸条都没留下。不过有位姑娘,来这里做义工,一直资助这孩子,要是能给孩子找个家就好了。话说回来了,这么健全的孩子在福利院待不久,很快会被领养的。
我从孩子的眼睛里看到了清清的、清清的一汪泪。
一封邮件引起我的注意:有人举报你在捐款一事上,有徇私嫌疑。最近监督部门有可能找你,请有所准备。
我脑袋一下大了,这才刚刚办完没几天啊!不过捐赠计划是之前就做好的,我拿出捐款的至少五分之一来专门资助那个男婴!
我没有做贼心虚的害怕心理,但不知为什么还是惊出一身汗,后背、前胸、额头湿溽难耐。
进来一个年轻人,这是为我办理租房子的工作人员。他向我歉意地微笑:您恐怕要搬家了。说着交给我一份写着某区法院的信函:
您租住的××花园小区89号楼9单元1903房间,该不动产涉及产权纠纷。此出租和承租合同属于无效合同。限在收到本告知函××个工作日内搬出该住宅。
我强挤出笑容,安慰眼前这个年轻人:没关系,抓紧时间再租一套,房子多的是。
我呆立在窗前。对面,同样的摩天大楼外,在低层装饰了郁郁葱葱的绿植,当然是假的。早上飘过一场若有若无的小雪,此时已无影无踪。雾霾和阴云亲吻得肆无忌惮。灰暗、低沉,像我的心情。
走出温暖如春的空调房,街上阴冷得让人措手不及,身上的湿热瞬间被吸走。十二月,寒冷的季风途经内陆,光顾渤海湾,带着雀跃和几分疯狂,没有目标,就像刚来时的我。路过昨天的回转寿司店,心里掠过一丝暖意。不知不觉又走到了轻轨站,这是我每天乘车的前一站,同样的干净,同样的复古,同样的让人有淡淡的惆怅。专用的站点,专用的轨道……
我不喜欢开车,就是不想太快。
在电车上我喜欢倒坐着,慢慢地看窗外的风景前行,像一幅画,总想自己也进入画里,做现实版的穿越。
网上说塘沽成陆只有八百年的历史,黄河数次改道,“浊水所经,即为平陆”,即使穿越了,会去哪里?况且这里是开发区,很多地方都是人工填海造陆的,要想穿越恐怕只能穿越到空空如也的大海上去。
电话响了好久,我看了一眼,是助理打来的,迟迟不想接,对她破坏我这份好心情甚是恼火。但看看手表,毕竟这还是工作时间,我溜出来是有点早了。
电话那头,她兴奋地对我说:终于搞清了,房东的房子是第一次出租,第一次就租给我们公司了。那个所谓的前房客陈永强,才是原来真正的房主。因为把房子抵押给现在的房东,借了一大笔资金救市。据说之前还挪用了所任职公司的几百万元资金,前一段时间股市大崩盘,全部资金所剩无几。后来竟自驾出游,结果发生车祸。也有人猜测是自杀。而他老婆此时因为故意伤人被判刑,正在服刑。
我打个激灵,故意伤人?
对面说:哦,据说是在街上,和一个怀孕的女子发生争执,致使对方流产、右臂骨折。
因为房产证一直在债主,也就是现在的“房东”手里。陈永强死后,“房东”试图把产权过户到自己名下。但此房是陈永强夫妇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抵押合同至少有一半是不合法的。不过你别担心,我们是通过正规的中介……我把电话从耳边拿开,后面助理说什么,我早没了兴趣。
没有目标的我,竟然又回到了“家”。
我一骨碌趴在了那晚温清婉睡过的小床上,身子发轻,脑袋发沉。在闭上眼睛的那一刻,看到夹在床头和柜子之间的一个似乎文件夹的东西,被死死地挤在了墙角,费了不小的劲儿才抽出来。竟然是份保险合同,险种是身故险,投保人:陈永强;受益人:温清婉。
我几天来都想拨,却犹豫不决没拨出去的电话。通了,我说我想穿越!
对方“啊”地叫了一声。
我说我想穿越回那晚喝小米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