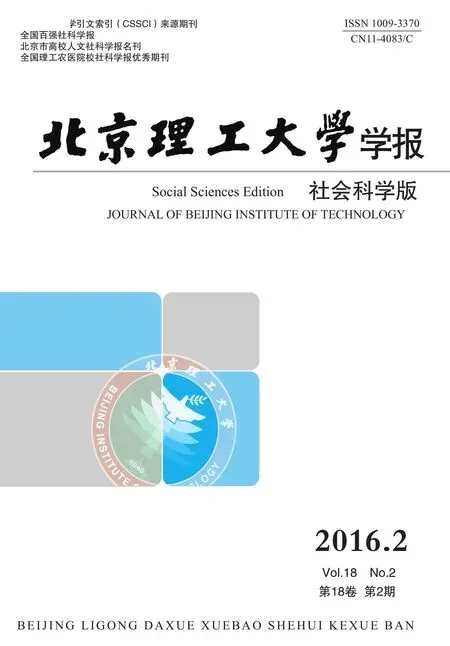制度供给视域下的英国南极参与:实践与借鉴
鲍文涵,赵宁宁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武汉 430072)
制度供给视域下的英国南极参与:实践与借鉴
鲍文涵,赵宁宁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武汉 430072)
作为传统的南极大国,英国参与南极治理的历史悠久,成果丰硕。自1908年在南极提出领土要求以来,英国通过积极参与各阶段南极治理机制的塑造和完善国内参与南极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强化了其制度供给的能力。对南极治理的制度供给已经成为英国实现其在南极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中国应不断培育南极制度供给的多元主体,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加强对南极治理的制度供给,为中国实现南极国家利益提供保障。
南极治理;英国;制度供给;启示
英国进行南极探险最早可以追溯至1772年英国海军中校詹姆斯·库克指挥HMS决心号(HMS Resolution)的南极远航。但在南极探险的“帆船时代”,英国南极的探险活动通常都是出于商业目的的民间自发行为。1908年,英国政府率先对南极提出了领土要求,南极局势开始变得复杂,阿根廷、智利两国与英国在南极领土问题上屡有争端,甚至爆发军事冲突;“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企图把南极变为新的军事力量的展示区域和世界霸权的竞争舞台,南极政治局势一直处于紧张态势,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英国为了保障其在南极的国家利益,一直寻求运用制度创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积极通过对南极治理进行制度供给维护南极地的稳定局面,为英国实现在南极的国家利益开辟了 “快车道”,100多年来,英国在南极治理制度供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对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维护中国的南极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制度供给的内涵、主体与动力
(一)治理语境下制度供给的内涵
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和有效的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生态和安全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1]。南极作为国际公共空间,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潜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价值,且南极作为全球气候变暖的“寒暑表”还与全人类的共同命运息息相关。随着各国势力在20世纪初相继进入南极洲,在南极的争夺产生了诸多涉及到全球公共利益的问题,为南极的政治局势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有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参与,而且还需要私人公司、公司联合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有效合作。同时还要借助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制度来规范各个主体的行为。因此,解决南极问题的过程是一个“治理”的过程,南极治理已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一部分的南极治理,在本质上是为南极提供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一种良性的制度安排是南极是否可以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制度供给,是为了避免国家、社会组织、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制定的政治、法律或经济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制或准则。在全球治理的语境下,这种被供给的制度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际制度一旦落实,其带来的利益由遵守该制度的各方共同分享,没有办法把参与的某一方从国际制度带来的利益中排除出去,因此具有非排他性;而一个新的国家加入到某一个国家制度的框架中来,接受该制度的制约,也不会导致该制度成本的明显增加,因此,国际制度具备非竞争性。国际制度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
(二)制度供给的主体
传统观点认为,在国内公共事务的管理当中,制度供给的唯一主体是政府。西方学者提出治理的理念,是因为政府作为国内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权威主体已经无法单独面对日趋复杂和多样的公共问题。探求新的公共事务处理范式,保障有序稳定的公共秩序,促进公共利益最大程度的实现,成为西方学者思考的新问题。
罗伯特·罗茨、格里·斯托克、詹姆斯·罗西瑙等西方学者提出了全球治理理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与传统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政府统治)相比,在主体或者权威来源上是有根本区别的,传统的政府统治的唯一权威来源便是作为政府本身,而治理的权威来源未必是政府,也可以是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是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联合。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国内公共事务的治理进程当中,制度供给的主体已经打破了过去政府垄断特征,私人机构等公民社会也开始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制度供给。
在国际层次,传统现实主义乃至新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认为,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导行为体。但在当前的国际公共事务中,国际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2]等非国家行为体所发挥的作用已经逐渐显现,国家已经不能垄断国际事务的治理权力和权威,国际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角色。
数量众多和种类丰富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使国家不再是国际舞台上唯一的行为体。这些非国家治理主体都能在各自的领域发挥或大或小的作用,因而不能盲目地排斥非国家治理主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3]。尤其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已经不仅仅可以满足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对其存在的需要,在某些事务领域更可以影响和塑造国家的政策和行为,结果便是“将来出现的任何治理模式都将不得不是网络性的,而不是等级制的,都必须将目标最小化,而不是野心勃勃的目标”[4]。因此,国际事务中的制度供给主体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已经从国家单一主体演变为包括国家、国际组织等行为体的多元供给主体,并且“国家和其他的非国家行为体一样,要努力在日益动荡的世界政治中争得自己的威信和权力”[5]国际制度供给在语义上,已经从以往的霸权维持的手段或工具,逐渐转变为国家等国际事务主体处理国际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成为通往世界新秩序的重要路径。
(三)制度供给的动力
由于国际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在“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支配下,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活动的主权国家具有与“经济人”相同行为动机,会产生“搭便车”的行为。如果所有国家都试图采取“搭便车”的行为,那么具备国际公共物品属性的国际制度将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供给。但在现实生活中,制度在全球治理中比比皆是且运转良好。因此必然存在着某种有效的激励,促使治理主体能够进行源源不断的制度供给。在全球治理中,这种动力主要来源于两方面:
第一,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新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降低国家间的交易成本。在全球治理的语境中,国家间的交易成本指为了防止国家间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发生的成本。试想在一个没有任何制度规范的国际环境中,各个国家为了争夺各自国家利益可以根据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采取任何投机取巧、随机应变的行动,这种行动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一国在对另一国的行为缺乏准确预期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他国的机会主义行为,该国就需要进行一定的投入,包括说服、诱导和强制,这些投入产生的成本就是全球治理中的国家交易成本。在国际事务中,如果在这些国家“交易”缺乏一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那么国家间的交易成本就因机会主义行为而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降低高昂的交易成本,就产生了创设一个双边或多边的约束性安排来降低交易费用的动力,而且交易成本越高,国家倾向于一种更加有约束性的安排的可能性越大。当创设一项新的制度带来的收益超过新制度产生的成本或者旧制度安排的成本高于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时,制度供给就会发生[6]。
第二,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主动进行制度供给有机会获得国际制度溢价。国际制度溢价是指主权国家通过创设出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制度而获取的额外的制度红利。例如在20世纪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的殖民者地位与殖民地国家签署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攫取了殖民地大量的资源而获得的利益,就可以看成获取制度溢价的现实表现。由于国际制度是一种对当下利益的分配机制,而这种分配中的公平往往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在全球治理中,一些综合国力更强的国家,通常也具备更强的制度供给能力,可以凭借其自身政治经济的优势地位,在参与制度供给的过程中掌握话语主导权,使新的制度朝着更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而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制度一旦产生,将会在一段时期内对制度供给方产生持续的制度溢价。这种额外的制度红利是促成主权国家进行制度供给的重要动力来源。
管理南极事务的过程是一个“治理”的过程,南极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方面,其核心就是为南极提供一套合理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安排。由于制度供给具有降低国家间交易成本和获取国际制度溢价的激励,主权国家是南极治理制度的主要供给方,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也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在南极事务中,较早进入南极的国家通常也具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优势,不仅有降低国家间在处理南极问题上的交易成本的诉求,也受着南极治理机制带来的制度溢价的利益驱使,因此这些国家会积极对南极治理进行制度供给,以期在南极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
二、英国参与南极治理的实践
南极历史上无常住居民和人类活动,没有任何体现人类文明的制度规范。伴随着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南极洲,且随着对南极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南极的争夺日趋激烈。但由于缺乏一整套可以依照的制度规范,各国都具有为了本国利益最大化而从事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英国作为最早对南极提出领土要求的国家,这种混乱的充满机会主义行为的局面不利于其南极利益的实现。因此,英国一直积极地对南极治理进行着制度供给,希望通过塑造和完善治理南极的相关法律、规则和国际惯例,强化其在处理南极事务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增强其面对南极复杂局势时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最终为其实现在南极的国家利益奠定了制度基础。
(一)国际层面的制度供给
1908年英国对南极提出领土要求时就提出用“扇形原则”来为当时各国争夺南极领土提供一个划界依据,即以南极点为心顶,以径线为腰并以纬线为底所形成的扇形范围内的区域,归主张该扇形空间的国家所有。这是英国在早期争夺南极领土的过程中第1次制度供给的实践。此后,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挪威、智利、阿根廷等6国相继依据该原则对南极洲83%的领土提出了自己的主权要求。虽然国际法从未承认“扇形原则”为获得领土主权的合法途径,但是这开启了英国在南极治理制度供给的先河。更为重要的是,此次由“扇形原则”确定的英国南极领土让英国成为南极事务的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初步确立了英国日后南极大国的地位,奠定了英国未来一百年南极政策的基调。
英国对南极治理机制的第2次制度供给是在冷战时期,该阶段英国对南极治理的制度供给主要是依靠着其亲密盟国美国来进行的。一方面,当时虽然有7个国家都对南极领土宣布持有主权,但是这些国家的主权要求或保留态度彼此之间不能平衡,英国、阿根廷和智利3国在南极领土还存在着重叠,各国在南极洲的关系日益紧张;另一方面,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苏联的势力不断进入南极洲,两国不断升级在南极地区的对抗性竞争行为,对南极领导权的争夺逐步成为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一个方面,南极洲正逐步成为一个新的国际竞争的新舞台,加之当时世界笼罩在核武器的阴影之下,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不符合英国在南极的利益。在这个情况下,作为美国战后的盟国,英国积极与当时的超级大国美国磋商,提出了由美国出台南极“8方共管”的方案,即美国同其它7个主权要求国成立一个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共同管理南极,避免苏联的进入[7]。此次英国和美国共同提出“8方共管”的方案虽然遭到了其他5国的共同反对,但是该事件确是成为《南极条约》出台的一个关键环节,该方案的被否定促使美国寻找新的解决南极争端的途径,加速了《南极条约》的出台。
最终,美国决定放弃过去建立由西方国家主导的领导集团的解决方式,提出了一项多边国家条约来共同限制和规范各国的行为,即推动《南极条约》的出台。英国在《南极条约》的出台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美国的号召下,1958年11月18日到12月底,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法国、日本、新西兰、挪威、苏联、南非、英国在冻结南极法律现状、条约是否应该包括公海、非军事化条款、非条约国的接纳等问题上进行磋商。其中,就非条约国的接纳问题上,英国提出扩大南极条约参加者的范围,但限制参加管理的国家数目的建议。该建议后被各国接受,《南极条约》之后规定“对于联合国任何会员国,或经其代表有权参加本条约第9条规定的会议的所有缔约国同意而邀请加入本条约的任何其它国家,本条约应予开放,任其加入。”英国的这一建议将《南极条约》变为了一个开放的条约,客观上防止了美国等超级大国操纵《南极条约》,有利于之后南极多元共治局面的形成。
英国对南极治理的制度供给的努力对日后英国南极利益的实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扇形原则”在南极瓜分领地时的运用确立了日后英属南极领地的主要范围,这些以“先占原则”占有的领土范围成为日后英国坚持和重申南极领土主权的主要依据;《南极条约》的出台虽然冻结了各国领土主权的要求,但是并没有否定英国在南极的领土要求,这就保留了英国在南极的核心利益,同时促使《南极条约》向所有国家开放,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在南极的霸权,有利于扩展英国在南极的“实质性存在”地位。
(二)国内层面的制度供给
在国内,英国也积极地出台新的法律和制度,用以规范国家和公民在南极的行为,为英国科学合理进行南极开发,保持南极大国良好形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英国政府先后出台了1989年《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命令》,规定了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的领海范围是从领海基线量起的12海里;1990年《司法管理条例》规定只要当地条件允许,英国的法律就将适用于英属南极领地;1994年《南极法》分为4个部分,1个附件,包括对南极的定义、环境保护、矿产资源活动、南极动物和植物保护、相关活动的许可证、适用于英国人的法律等规定,该法还在2009年进行了修订,在2010年出台了《南极法草案》;1997年《环境保护条例》规定了南极环境及其资源的保护,包含了进入英属南极领地、南极矿产资源和动植物保护等方面的规定。2013年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还出台了《英属南极领地战略文件2009—2013》,从宏观上阐述了英国在南极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路径。这些国内法规制度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支持英国参与南极治理的丰富的制度资源,使英国在采取南极行动的过程中有法可依;英国在南极的国家利益得到了国家法律和战略文件的确认,保障了国家南极行动的一贯性和持续性。同时,这些国家出台的正式制度可以有效提升国民的南极国家利益的意识,促进国民形成积极参与全球南极治理上的共识,逐渐塑造出有利于实现英国南极利益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下,英国参与南极治理的丰富的国内制度资源已成为其南极国家利益实现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更为重要的是,在100多年参与南极治理的实践中,英国政府管理南极事务逐步形成了多方参与、合作治理的格局,这就为英国参与南极治理提供了多元的制度供给主体。英国政府通过改革适应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早已不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尽管影响英国公民的大多数决策仍然出自于白厅和威斯敏斯特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之手,但还有一些决策出自别处:有的出自英国国家层次之上,例如由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是欧盟作出的决策;有的则是处在英国国家层次之下——地方政府、地方议会、制定机构或是诸如医院联合体(hospital trust)、中小学以及高校做出的决策[8],由此可以看出,英国国家的治理方式是多层次治理,需要各个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南极政策作为英国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自然是多层次治理下的产物,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等主体在相互沟通和妥协的基础上再输出最终的政策。在英国政府系统中,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是主管南极事务的主要部门,也是负责出台相关南极政策的主要部门,外交部通常只负责英国在南极的主权维护和外交事务等政府事务,其他的如南极遗产保护、科学研究等事务则由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英国南极遗产信托基金、自然科学研究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南极调查局都是参与南极治理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此外,英国众多科研机构也是英国参与南极治理的重要支撑力量,如英国剑桥大学的斯科特极地研究中心为代表的科研院所为英国南极政策的出台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智力支持。
总之,在南极事务的管理中,英国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而是充分发挥了“元治理”的角色,为英国的南极事务进行宏观指导和制定相关规则,各个公共和私人的机构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形成了权力中心,对本部分的南极事务的管理行使着权力,拥有足够的权威。参与南极事务的各方已经形成了一个自主的网络,与政府在南极事务的管理中进行合作,分担部分政府的管理职能,“多元共治”的图景表露无遗。这种南极事务的多方合作、共同治理的格局为英国实现在南极的国家利益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基础。
英国在国际层面上对南极治理的制度供给为英国实现其南极利益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内层面上对南极治理的制度供给促使英国形成了实现南极利益的制度资源,为英国“走出去”参与南极政治舞台的角逐奠定了良好的国内制度基础。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使英国无论在过去的“南极领土争夺战”中,还是在当下的全球共同治理南极的的环境中都始终占据优势地位,有效维护了英国在南极的国家利益。
三、对中国的借鉴价值
通过制度供给或者参与制度供给来保障国家利益的实现,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国际制度可以为一国追求的国家利益披上合法的外衣,是增强国家实力的一种“投入小、收效大”的方式。对于一个和平崛起的国家来说,通过参与南极治理进程中的制度供给,其“最小的结果便是增加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最大结果便是增强在国际制度上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参与南极治理制度供给,推动南极治理机制或规则的修改,应该说是中国参与南极治理、保障南极地区国家利益的极佳途径。对中国来说,应当积极吸取英国在南极治理制度供给方面的有益经验,把有效进行制度供给作为实现中国在南极国家利益的有效途径。这就要求中国能够敏锐把握南极治理的制度需求,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加大对南极治理的制度供给。
(一)在国际层面
首先,中国应当利用当前南极治理机制的不足之处,增强制度供给的能力,积极等待和找寻制度供给的时机。一般而言,制度的重新安排是在单个行为主体为谋求在现存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而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所引发的。中国作为参与南极治理的“后起之秀”,当前的南极治理机制下虽然能够保障中国实现一部分南极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在该治理机制下中国在南极的国家利益的实现仍然会受到一定制约。这是因为在南极国际政治舞台的角逐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少数南极大国一直主宰南极事务,依据国际法中“先占原则”维持其在南极的绝对优势地位。这种局面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保持当前南极稳定的多元共治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南极变为少数国家“俱乐部资源”的危险。如果按这样的态势继续发展,美国、英国等传统南极大国很有可能成为主宰南极政治的寡头,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将不得不按照它们所制定和创设的规范和制度行事,国际南极政治舞台单极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9]。如此一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南极的利益将得不到保障,就会增加这些国家对新的更加合理的南极治理秩序的需求。在全球政治多极化趋势增强的今天,国际社会不会容忍南极政治呈单极化发展。这种需求将成为未来南极治理制度发生变迁的最大推动力。中国要在未来的南极治理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维护中国在南极的国家利益,就需要敏锐发现南极治理机制中的不合理之处,找寻到南极治理机制中制约中国实现南极国家利益的不利因素,发挥国家智库的作用,积极进行学理上的探讨和研究,不断加强中国进行南极治理制度供给的能力,以便在未来南极治理制度变迁的“政策之窗”打开之时,把握时机助推南极治理机制的更新,参与新一轮南极治理机制的塑造,维护中国在南极的国家利益。
其次,中国应当积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共同推动南极制度供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实现南极领地的和平、稳定和非军事化,要实现中国在南极的国家利益,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显然远远不够。当全球化成为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特征,跨国组织(tra nsnational organizations)和超国组织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的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在这样的环境下,南极的“善治”在全球化时代同样需要代表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的制度来塑造,但这种代表新的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的制度,单靠一个国家来推动和供给显然是不够的,还应当积极与各个国际组织沟通和协调,尽可能地让中国的国家意志被更多的国际组织接受和传播,让更多的南极国际组织成为代表中国国家利益的南极制度供给的主体,一道形成制度供给的“合力”,为中国实现南极国家利益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国内层面
应当加大对支撑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制度资源的供给程度,尽快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国家南极战略。和英国相比,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时间较短,国内的南极治理相关制度资源存在着短缺。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从国家层面出台系统的南极战略,也没有进行南极立法,在行政法规中,直到2014年6月,国家海洋局根据国务院2004年的412号令制定出台《南极考察活动行政许可管理规定》,对当下日益增多的南极考察活动进行了规范,而英国早在1994年的《南极法》中就已经确立了南极许可证制度,中国在南极立法上已经落后英国20年。
中国在南极治理方面的制度资源稀缺的同时,对参与南极治理的制度需求却在与日俱增。多年以来,中国南极考察活动主要由国家海洋局组织的科学考察活动为主,考察队人员主要由相关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组成。但是近年来随着南极活动日趋多样化,参与南极考察活动的人员数量不断增多,组成和考察活动方式更加社会化,人员构成也日趋多样,尤其是社会团体组织的南极旅游、探险和科普考察等活动成上升趋势,这对南极考察活动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10]。以南极旅游为例,根据国际南极旅游者协会的最新统计,在2013—2014年度,中国登陆南极的游客人数已达3 367人,仅次于美国和澳大利亚[11],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南极旅游国,同时也是南极旅游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但与南极旅游不太协调的情况是,中国在南极旅游方面的制度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到目前为止,南极洲并未被中国政府列为中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对南极旅游的相关管理制度法规至今也没有出台,政府在在对南极旅游市场管理过程中处于无法可依的窘境,而相关企业在从事南极旅游市场活动时也无章可循。
其次,中国应当努力促成南极治理制度供给主体多元化局面的形成。目前,中国南极事务管理体制政府主导的色彩还比较明显,无论是南极事务的行政管理、科学研究,还是资源分配都是由政府主导。这不利于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中国可以从两方面入手来扩大制度供给的主体。一方面,理顺政府在南极治理中的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元治理”的角色。在未来的南极治理中,中国应当逐步在南极事务的管理中贯彻“简政放权”的原则,将一部分社会组织可以承担的相关职责重新分配,国家海洋局极地办应当集中运用国家权力去引导和规范公民的各种参与南极治理活动,为各方参与南极治理提供可依据的规范和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另一方面,积极培育社会力量参与南极治理。由于中国涉足南极事务的历史较短,目前尚未出现专门的从事南极相关事务的非政府组织,这制约了中国南极治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中国应当积极鼓励和培育一大批从事极地科学研究、环境保护以及极地软科学研究的非政府组织,用以承接政府的职能转移,培育新的参与南极治理的主体。
中国对参与南极治理的制度需求和现阶段的制度供给、制度供给的参与主体和需求主体两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国内层面的支撑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制度稀缺引发的不利因素正在逐步显现。中国加快对参与南极治理的制度供给的步伐,尽早制定形成系统的国家南极战略,完善法律体系,形成中国南极事业“多元共治”局面,为南极国家利益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1]俞可平.全球治理的趋势及中国的战略选择[J].国外理论动态,2012(10):7-10.
[2]戴维·赫尔德.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6.
[3]李景治.全球治理的困境与走向[J].教学与研究,2010(12):32-40.
[4]约瑟夫·奈.全球化世界的治理[M].王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33.
[5]郑安光.从国际政治到世界社会:全球治理理论与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81.
[6]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43.
[7]胡德坤,唐静瑶.南极领土争端与《南极条约》的缔结[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63(1):64-69.
[8]比尔·考克瑟,林顿·罗宾斯,罗伯特·里奇.当代英国政治:第4版[M].孔新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7.
[9]李升贵,潘敏,刘玉新.南极政治“单极化”趋势——以美国南极政策为中心的考察[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8,25(10):75-78.
[10]曲探宙.谈 《南极考察活动行政许可管理规定》[EB/OL].(2014-06-04)[2014-08-06].http://www.soa.gov.cn/xw/dfdwdt/ jsdw_157/201406/t20140604_32060.html.
[责任编辑:箫姚]
The UK Antarctic Engagement base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Supply:Practice and Reference Value
BAO Wenhan,ZHAO Ningni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China Institute of Boundary and Ocean Studies,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s a traditional Antarctic state,the United Kingdom has a long history in its participation in Antarctic governance,which turned out fruitful.Since Britain made the territorial claim in the Antarctic Pole in 1908,it constantly enforced its institutional supply ability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stages of shaping Antarctic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s and regulations of domestic participation in Antarctic governance.Antarctic governance system supply has become a critical platform for Britain to realiz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Antarctic Pole.The paper intends to expound on the British practices in Antarctic governance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system supply and gain enlightenment from its act on the current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Antarctic governance.
the antarctic governance;the united kingdom;institutional supply;Enlightenment
D815.9
A
1009-3370(2016)02-0139-06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6.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