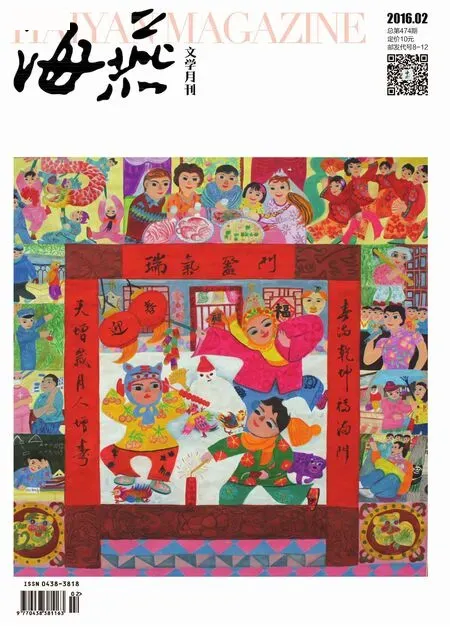逆水而行
□卓慧
逆水而行
□卓慧
一条河的生命线到底有多长?它原本的颜色、质地是怎样的?它经历过什么样的遭遇有过什么样的委屈什么样的呐喊什么样的诉求?
一个人脑子里忽然蹦出这样的问题,在某些人看来,有些傻。无疑,这样的问题,能答者寥寥,怕也没有人想要去回答。
在此之前,我也从没想过这样的问题。前次从成都去康定出差,二郎山隧道因为工程修建原因控制车流量,怕被堵,我们只得舍近求远,放弃从天全钻二郎山隧道直达泸定,而从海螺沟绕过去。过雅安,经荥经到汉源,车驶上新近被网友戏称的“逆天工程”“云端上的高速公路”——雅西高速后,在崇山峻岭间蜿蜒,大渡河就像一只林间穿行的小鸟,一会儿闪左,一会儿行右,似有若无,悠悠然然地跳入了视野。趁飞快驶过的闪回远远望去,大渡河河面宽阔,水幽蓝,流淌得平缓沉静,两岸果林、野生林织就的青色倒影深深浅浅地辉映其间,清幽幽的,整体气质就仿若一个温婉沉稳的女子,一派现世安好的样子。但自石棉下高速转入211省道后,即是另一番景象:道路没有高速路宽、平,这是自然的。关键两岸的山更高了,宽阔的河谷变成了窄窄的峡谷,迤迤逦逦的车道,必需小心翼翼紧紧依傍着山才能稍感稳妥。一路过去,大渡河形成被两岸的高山紧紧拥持之势,仿佛想伸个胳膊腿儿都得费劲挣扎一番。河面离车道倒是近了,有时就在咫尺,下车去完全能够进行零距离接触。但我没有丝毫兴致,因为这时大渡河的水,无复半点儿先前隐约看见的青幽,而是又浑又黄,混浊粘滞,裹满了泥浆,一忽儿奔腾跳荡如谁也驾驭不住的脱缰野马,一忽儿又平静安宁得连处子般的呼吸也没有,俨然一个大泥潭,把个人扔进去立马拎起来就能是一尊泥雕。
大渡河,你何以竟变成了这般模样?
巨大的疑问,如六月燥热的天空中忽然出现的闪电,猛然间撕开一道口子,深潜在那缝隙里的一只只飞蛾,翩然轻扬而出。
平生第一次知道“大渡河”其名,应该是从那篇著名的课文《飞夺泸定桥》上,记得彼时在为我红军勇士不畏艰险冒着枪林弹雨强渡成功的英雄气概感动振奋之余,对文中所写的大渡河“水流湍急”四个字,印象尤为深刻。“水流湍急”,“湍急”的水流是什么样子?“湍急”得有多厉害而至于“险峻”难渡?是如夏天暴雨过后猛涨泛滥势如破竹汹汹滔滔不可遏制的洪流?河流于我并不陌生,家旁边就是四川之一川的沱江(与沈从文家乡的河同名的一条河),我们自小就看见过它和缓流淌,也见识过涨水时它的汹涌之势——那时,不知是新闻少还是什么原因,大人们似乎对涨水特别关注。每到夏季涨水时节,关于水位的话题就成了挂在大人们嘴边的热门话题,相互间见了面,有意无意总会谈论,今天水到什么位置啦……一旦传闻到什么位置了,听者常作出惊叹状,晚饭后便会兴奋地携着家人,以散步的名义,相拥着跑去河边,亲身证实、亲眼目睹。这样的节目年年上演,虽然了无新意,但每每还是乐此不疲。作为小孩的我们,那时总会兴奋地跟着大人去河边。看见陡然变宽了好多的河面,伴着轰隆声响波涛汹涌奔流而下能把人瞬间席卷而去的洪水,也常发出惊叹,以为那就是“汹涌”,那就是“湍急”。大渡河的“水流湍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形?我小脑子当时似乎想过,无从得知,不清楚,想象不出,也就扔一边了。彼时也知道了它就在我们四川省,但幼时的我,对课本上的东西,不只“大渡河”,所有的统统都是符号,是镜花水月,是虚幻缥缈,是与现实不相干的虚拟存在。从没有想过,虚幻与现实会发生交集;更没想到,有一天它会落在我眼前,我会实实在在走近它。
“大渡河”真切地从书本上下到我的生活中,是在20余年前。
那是一次“少年游”。一个假期,我和一个同学去西昌找一个朋友玩,然后三人又一起去汉源拜望另一个朋友。从西昌坐火车在乌斯河下时,记不起是下午还是什么时候,只记得天色比较昏暗,时值大夏天,感觉却有些阴森森的。从车站出来过一座桥,走一小段路,到达一个客运站,才能坐上去汉源的大巴。过桥时,瞄了一眼脚下欢然流淌的河水,我随口问道,这是什么河?朋友说,大渡河。猝不及防,像被什么东西意外砸中,我愣了一下,不相信似的追问,这就是大渡河?朋友瞥我一眼,仿佛我的地理是门房老头教的,答道,当然。不然你以为是什么?我不由倒抽一口冷气,虚拟之物竟这样没有预兆不由分说地就与现实对接起来?我惊疑、郑重地把眼光投向河面。河面宽有好几十米吧(对数字我一向缺乏准确的概念),水面泛绿,水流激越,河中似潜游着无数龙蛇,时而任性地翻卷水花,时而咆哮着奔腾,恣肆奔涌,左冲右撞,霸道蛮横,谁也不放在眼里的样子。桥离河面有几十米高,桥面是钢筋水泥筑的,看起来结实平稳,明知自己是安全的,心却还是不由自主揪得紧紧的,总担心一不留神就会掉下去被它吃掉。
到了客运站,在大巴上,我们坐在最后一排。依稀记得大巴有些破烂,肮脏,座椅斑斑驳驳,东一块西一块的长有锈,窗玻璃残缺不全,昏黄模糊,积满了灰尘、泥巴。那年月县区的大巴几乎都这样,也没别的选择,我们没法嫌弃,也没想到要嫌弃,就入乡随俗地坐了上去。记忆中那时天好像不再阴了,有灿灿的阳光笼着车身。我们恬然地坐在那里,闲闲地东拉西扯聊着天等车开。“砰——”,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接着一股白烟腾空而起,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视力瞬时没有任何用处。几秒过后,烟雾散开,只见满车的人,除我们外,都已从车上跳到了地上,只有我们三个安然不动。我们傻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阵子烟消尘定,仿佛有人来查看了一下,也没作什么处理,就恢复正常了,车下的人又纷纷返回车上,才知刚才是大巴上的干粉灭火器爆炸了。可笑我们三人,从没经历过,常识也欠缺,第一时间竟然没作出任何反应,事后想想都后怕,少年时的懵懂、无知可见一斑。
车开后,大巴沿着大渡河往汉源县城方向行驶。后来才知,这一段称为大渡河大峡谷,已列为国家地质公园,全长有20多公里,因横断山脉东缘地壳强烈上升而成,是我国最大型的、河流上最为典型的嶂谷和隘谷。峡谷里谷坡直立,谷地深窄,最窄处仅10米左右,比30米宽的虎跳峡还窄;最大谷深超过2600米,远远超过美国科罗拉多(2133米)大峡谷。当时我只觉两岸的山好高大、伟岸,时或是树、草覆盖的幽幽青山,时或又是刀斫斧劈般的岩石壁立千仞。车行山腰,一侧是陡峭的山,另一侧则是奔腾咆哮的大渡河。道路很窄,供一辆车通行都很艰难。车在道上蜗牛样踽踽伏行,我总感觉它只有一侧轮胎、只有半个身子是着地了的,另一侧是悬空的,而我坐的那一边,正好在“悬空”的那一边,在“悬着”的后轮胎上。对面有车驶来,要错车。我高度紧张,我的天啊,怎么错得开?彼时更觉车掉下去是分分秒秒的事。可难以置信的是,车竟然顺利地错开了。在惊叹、佩服司机高超的驾驶技术之余,我仍然心惊胆战,眼不停地在前方的路和窗外的河水之间睃巡,思谋着一旦出现臆想中的情形我该怎么办。能怎么办?大渡河就在脚下、就在身旁咆哮,路还是那样狭窄、崎岖!除了听天由命,除了暗暗祈祷平安、顺利,我没想出任何办法。
一路过去,见车虽颠簸着,却并没有掉下去,就知仍是安全的,是自己想多了,是感觉的误差。于是一边安慰自己没事,一边仍不免把心攫得紧紧的。重复、疲劳是麻木神经最好的武器。一阵子过后,我就放松了一些警戒,把安全有所保留地扔给了司机。恍恍惚惚中,还打起了盹。只在遭逢上大坑,身体像惊起的小鹿,随车子像弹起的石子一样跳起来又荡下去,划出一个美丽而惊心动魄的弧线后,才复又警觉地盯视着河水、悬崖、道路。
快到汉源时,转过一个山坳,眼帘里忽然出现一整匹巨石构成的山,横矗在一段白云之上,红砂色的底上黑褐色的嶙峋凸起,高高低低、深深浅浅,就像一群历经沧桑、有无数故事的血性汉子。下方,一片黛绿。背后,一轮即将隐去的夕阳,似一枚浸润得刚刚好的咸蛋黄,绚丽的霞光把一大盆红红黄黄的颜料以不容抗拒的势头倾覆过来,映照得山石坚韧、粗粝的质地愈加磊落、怆然,镂刻上去的一般,还极富层次。不远处奔腾的浪花,哗哗的水流,奏鸣曲一样在耳边回荡。猛然看去,整个儿就是一幅极具质感的巨型风景油画,构图简练,气势磅礴,线条粗狂、奔放,色彩浓烈、深沉,整个画面质朴而明晰,很有些列维坦油画的意味。一瞬间,我有种强烈的震撼感——被美,如蒋勋说的,这个看不见的竞争力所震撼。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被现实中的山水美所震撼。那画面,我至今记忆犹新,也再没看见过,到目前为止可说是我生命中感受到的一曲“绝响”。
其后,再度遭遇大渡河,是几年前参加“重走长征路”的一次活动。那次,循着当年红军走过的一段路线,我们先去了安顺场,后去泸定。站在安顺场河边的码头旁,目光所及,河面不算很宽阔,有几十米吧,水清澈,水流平缓,怎么看也像一个性格温顺的女子。彼时,我人生阅历已有所增加,知识储备也相对多一些了,知道安顺场这个曾被叫做紫打地的地方,历史上在这里上演的著名事件不只有红军的,还有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的。
1863年5月,厌恶内讧愤然出走的翼王石达开,辗转广西、滇黔进入四川到达安顺场时,本就人疲马乏,兵残卒减,物资匮乏。看见并不湍急的河流,翼王打算修整一下,补充配给,造好船筏,再渡河上路。孰料,风雨陡袭,一夜之间,平静的大渡河突然打断向来的节奏,罕见地提前暴涨,使得他数度率部强渡都未成,生生阻断了求生之路。为保全几千部下性命,他投诚就擒,终被清廷捉到成都凌迟处死。有勇有谋,识见超迈,果敢决绝的一代豪杰,就此陨落。
时隔72年之后,1935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到达安顺场——这个石达开败北之地时,也遇上风雨夹击,时间上,红军比石达开部还晚十来天,理论上更有涨水可能,可结果是红军成功渡过。
这同一块地,同一条河,戏剧性地,竟成了石达开的“悲剧地”,红军的“胜利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河虽分枯、丰期,但这前后两次“大戏”,季节也大体差不多,只是时间相差了72年,它怎么就对一者说“YES”,一者说“NO”呢?这同一块地,同一条河,它怎么就是一群人的“滑铁卢”,另一群人的“诺曼底”?天命?除了天命,我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罢了,世事无常,拨弄人间命运的那只手到底依据什么范式、什么准则在运作,谁能知晓?
去泸定桥。双脚怯怯地踩在泸定桥的木板上,我仍有些不真实的感觉。这座康熙年间建成并配享过御笔题写的桥,听介绍说外观没怎么变,还是由13根铁索当经,一块块有间隙却也结实的木板作纬。人走上去,桥有些晃荡,但显然安稳。桥下的大渡河,河面有100余米宽,水色清亮,水奔流得也欢实,虽不时可见涡旋,却感觉不是很“湍急”,还没有当年去汉源那次见到的“急”。据说可能因气候变化、降雨量变化的原因,现在的大渡河水量已没有当年红军飞渡时丰沛。之前在安顺场,也说是气候、降雨量等原因,河水量比原来少了许多。
暗自嘀咕,这个现象,这个话题,这些年不知遇到过多少次!
长江如此,黄河如此,鄱阳湖水在减少,洞庭湖水也在减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河流,水量都在逐年递减,而反之者,依我寡见,经年来从未有闻。就连我家乡那条河,沱江,我也明显感觉出,它在越来越苗条,越来越远离我记忆中的模样——最直观的,水面没有那么宽阔了。不说夏季丰水期,就是平常,记忆中,它一直有些敞阔,虽说只是长江的一个支流,但阳光直射波光粼粼的时候,“浩大”的感觉并不缥缈。两岸的人,彼此要打个招呼,还是比较费劲的;就算冬季枯水期,若没有船之类的渡河工具,几乎没人能涉水过到对岸。但现在,河道明显变窄了,冬季枯水期,有河段甚至都要断流了,目测挽起裤腿就能涉水抵达对岸。挖沙的船,这一处,那一处,一年四季都在它身上开掘。完整的河面,早被分割得零零碎碎,三三两两。一堆堆沙,一坨坨石,一截截断流的裸露的河床,看上去就像是一道道扒拉开的伤口,在流血,在淌泪,满目疮痍。每每见此,心总莫名地感到一种疼。这河,有厉害的时候,不说涨水天,就是平常时,也有凶狠潜藏。早年,我曾亲见它吞噬过我熟悉的鲜活的生命,那些年,几乎年年都有人葬身其腹。可是,每到河边,脱掉凉鞋,双脚一触上柔柔的沙子,凉沁沁的水一没过脚背,一股温暖、亲切、舒服油然而生,就感觉它是邻家良善的大婶、大姐。而今,潦草看去,水倒还是清花亮色的,但大家都知道,水质早不一样了,早年人们还在这河里淘菜、洗衣,现在这种景观早已荡然无存,别说淘菜、洗衣,就是洗脚、戏水的,也少有见到了。这可不单是社会进步,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大家用上了自来水、更注重卫生、安全的结果,而是上游某化工厂长年违规直接向它排放,它的水质确确实实已变坏,已根本不能饮用,某年甚至还出现过恶臭。人们反映、投诉,甚至请电视台曝光,但仍未见怎么改善。人们无奈,只得听之任之,敬而远之。估计它更无奈。也许,消亡将是它表达愤怒和反抗的最后方式。
眼前大渡河这浑黄的河水,据说是近期连降暴雨、山洪暴发的结果。而那些泥淖一样的平静河段,则是水电站堤坝阻拦所致。是的,早闻听过报道,大渡河、金沙江、岷江,四川省内的这些著名河流,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筑堤造坝,这些年纷纷被改造,被肢解,修建了不少梯级电站。一方面,它在被造福于民;可另一方面,生态也遭到巨大破坏。植被变差,水土流失,山洪频发,是最明显的证据。眼下这难看的身子,估计它们自己早都不堪目睹。我相信,它的泪,肯定已淌过不少;它愤激的抗诉,也发过不少。可惜我们听不懂,看不见。它呢,除了隐忍,还是隐忍。或许,到再也不能承受那一天,它就会爆发,或者消亡。我相信,彼时,它的爆发,肯定会是我们人类难以预想、难以控制的;其结果,会相当惨烈,会是我们不可承受之重。那,或许就是它对我们的一种彻底清算。
绕过牛背山,海螺沟,到达康定时,天已黑。康定是三山两河夹一城。雅拉河依傍在城边,折多河穿城而过。次晨一早出来溜达,看见规整的河堤内,折多河欢畅地奔涌着,争先恐后、无忧无虑的样子,就像个在尽情嬉戏玩耍的孩童。一朵朵碰撞而出的莹白水花,就是他发自心底的欢快笑声。河水青碧澄澈,了无瑕疵。在这大夏天里,我仍能清晰嗅到缕缕晶莹冰凉的雪的气息。是雪水吧?一问,果不其然,这是折多山流下来的雪水呢。
到网上一查,发现折多河和雅拉河汇合后流入了大渡河。原来这也是大渡河的支流!仔细一捋,方知大渡河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阿尼玛卿山脉的果洛山南麓,上源足木足河(麻尔柯河、阿柯河)经阿坝县于马尔康县境接纳梭磨河、绰斯甲河(杜柯河、多柯河)后称大金川,向南流经金川县、丹巴县,于丹巴县城东接纳小金川后始称大渡河,再经泸定县、石棉县转向东流,经汉源县、峨边县,于乐山市城南注入岷江,全长1062公里。
猛然惊觉,若问大渡河的初心,它原本的质地是什么样,眼前这河水,应该可说就是一种答案。而我们这一路,原来一直在逆水而行。
责任编辑 董晓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