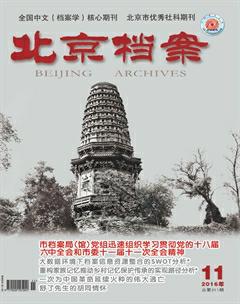重构家族记忆推动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实现路径分析
陈静
摘要:本文在介绍家族记忆概念的基础上,阐述了家族记忆在乡村记忆保护传承中的作用,并提出通过重构家族记忆推动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家族记忆乡村记忆工程家庭建档
乡村记忆工程是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一体化日趋明显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各文化单位发起的对乡村传统、乡村文化、乡村历史和乡村变迁采取的保护传承性行为。[1]在此背景下,我国部分地方档案部门顺时而动,组织开展乡村记忆工程,保护抢救乡村记忆。如威海市环翠区档案局开展“城乡记忆工程”、浙江省档案局发起实施“浙江记忆工程”、上饶市档案局开发“上饶记忆”网、天津市档案局组织实施“天津乡音记忆工程”等等,凸显出档案部门积极参与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主体责任和时代意识。乡村记忆工程的持续推进需要依托各种文化媒介才能得以保护传承,无论是有形文化媒介如祠堂庙宇、家谱村志、渡口桥梁,还是无形的文化媒介如宗教信仰、方言俗语、风俗习惯等都可以成为推进乡村记忆工程的载体。从上述由档案部门发起并主导的乡村记忆工程中,笔者发现家族记忆是乡村记忆工程的重点保护对象之一,基于此,本文希望借助家族力量,丰富乡村记忆工程建设途径,深化乡村记忆工程的建设内涵,在国家——乡村——家族的“记忆连续体”中,建构和谐、共赢的乡村记忆。
一、家族记忆及其在保护传承乡村记忆中的作用
(一)家族记忆的概念
“聚族而居”是我国乡村社会的一种传统居住方式,这种居住方式是以家族为产生的自然基础的。因此在界定家族记忆概念之前,笔者首先对家族的概念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家族的历史源头需要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其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的父家长制家族、殷商时期的宗法式家族、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宋代以后的近代封建家族。”[2]现代意义上的家族则发端于改革开放之际,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修谱祭祖、建祠等家族活动的日益增多,不仅说明家族成员对家族活动的热情日益高涨,而且反映出近年来村落家族复兴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3]
随着家族复兴、家族活动的增多,家族记忆随之生成和重塑,这种家族记忆的生成和重塑为乡村记忆传承提供了重要载体和乡村记忆空间。换句话说,乡村记忆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的祖先拥有一套独特的存储记忆的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就是家庭记忆,它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一旦被社会群体所认同,便会通过某种程度上具有仪式性的操演传递和保持‘社会习惯”。[4]具体而言,上述行为方式主要有编修家谱、祭祀仪式与祭祀活动、修建宗庙与祠堂、立石碑与牌位、制定族约族规、讲述祖先的传说故事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族记忆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它不再局限于同一个社会群体的记忆,还包括家庭这个社会单位的记忆。如果说古代所形成的家族记忆是为了缅怀先人,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家族记忆内涵更广,既包括对祖先的记忆,又记录着自身“小家庭”的记忆。“小家庭”的记忆一旦被家族推崇到一定地位时,便会被打上家族记忆的烙印,如挖掘出的各种杰出人物的手稿、日记、信件、旧物件,旧住址等。除了以上所介绍的记忆形式和内容外,现代家族记忆还来源于照片、录音、视频,各种家庭聚会、家规家训、家庭优秀人物的事迹等等,这些记忆经过提取、编码最终内化为家族记忆。
(二)家族记忆在保护传承乡村记忆中的作用
1.家族记忆与乡村记忆存在互构关系。家族记忆与乡村记忆之间的互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族成员重塑家族记忆需要从乡村记忆中提取相关记忆资源,重构家族记忆;二是家族成员在乡村范围内展开的记忆活动,间接构建了乡村记忆。在推进乡村记忆工程的过程中,这种互构关系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浙江省平湖市新埭镇鱼圻塘村利用该村的刘公祠建成了“乡村记忆示范基地”,将原来用来保存家族记忆的展览室改建成“乡村记忆馆”,对外宣传该村的历史文化。此外,档案部门、村委会还向村民征集各种家谱、老照片、老物件等,利用既有的档案材料、历史文献、实物影像等包括家族记忆资源在内的众多记忆资源,来反映村落发展历史,构建乡村记忆。在乡村记忆与家族记忆的互动过程中刘公祠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成为鱼圻塘村地标性建筑,该村也成为将家族记忆保护与构建乡村记忆充分结合的典范。
2.家族是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重要社会力量。中国乡村具有较强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家族观念深深植根于广大乡民的心中,家族文化活动甚至会在一些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徐建华在《中国的家谱》中提到,近年来编修族谱者一般是本族一些辈分高、热心公益事业且有较高威望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教师、退伍军人、医生和基层干部。当家族精英参与编写村史、村志,以多种途径参与记录乡村记忆文化时,乡村记忆保护传承工作所遇到的阻力会大大降低。
二、重构家族记忆推动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实现路径
乡村记忆工程作为延续乡村文脉的文化保护传承工程,不仅是地方政府或档案部门的责任,更需要各方的共同参与。笔者在阅读大量中国传统家族延续家族文化方面的文献中,选取出较具代表性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两种家族行为方式,并创新性地提出家庭建档、数字家书等方式,将其作为重构家族记忆的实现路径。
(一)重构家族记忆的传统路径
1.编修家谱。中国自古以来就很注重用文字记录历史,用档案传承后世。“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的观念从古至今得到了普遍认同。其中,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作为有着丰富文化积淀的徽州古村落,保存了自明清以来的族谱、宗谱、祠谱,包括堪称孤本的明嘉靖版龙井胡氏族谱、清乾隆版明经胡氏统宗谱、民国版龙井派宗谱,这些宗谱真实地记载了宅坦村明经胡氏家族的发展历史和地方风情。村长胡维平完成了反映宅坦村历史变迁的村志《龙井春秋》,在内容上形成了志谱结合的“特殊体例”。可以说,编修家谱对村史、村志的编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记录、传承乡土社会的风土人情及乡村演变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为此,在推进乡村记忆工程的过程中,档案部门需要对编修家谱这种群众自发组织的活动给予指导,如吸纳文化部门以及历史学家、档案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等参与,为家族修谱和保存提供专业意见;鼓励档案馆、文物部门接收民间族谱进馆保存,为家族记忆的保存提供更安全的保障。
2.重修祠堂。祠堂是一个家族乃至村落发展的内核和象征,它见证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承载了深厚的乡村记忆。同时,祠堂也是家族活动的重要场所,家族的很多仪式活动都需要借助祠堂来完成。正因为此,保护祠堂文化也成为村落文化保护的重点。201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要保护、传承和利用好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建筑风貌、自然生态、民俗风情,彰显乡村建设特色,并将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后世。浙江省档案局亦围绕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有针对性地将村落中原来的家族祠堂进行修缮并改建为文化礼堂,使其成为综合性的文化场所,吸引更多村民参与乡村文化活动。
(二)重构家族记忆的创新路径
1.家庭建档。家庭是构成家族的基本成分,家族是以核心和扩展家庭为主要形式的。家庭建档是家族记忆流传后世、继承家族记忆的创新形式。比如,《徐霞客游记》《鲁迅日记》《曾国藩家书》等文学作品就是将家庭档案中的日记、书信等收集整理成书。同时,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制作一份家庭档案,其实就是留给未来的一份宝贵记忆。随着乡村记忆工程的不断深入,家庭建档的观念会日益加强,它不仅会成为一种保护家族记忆和乡村记忆的新形式,而且将是乡村记忆工程保管乡村记忆的新形式。
2.数字家书。传统的民间家书被认为是社会变迁、文明演进的微型档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和符号。为了抢救这些将要消失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大学开展了“抢救家书活动”,并在十年间征集家书四万余封。为了方便家书的信息服务与利用,中国人民大学还启动了“数字家书”项目,以便留存家庭记忆。“数字家书”项目不仅仅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传统纸质家书的数字化与网络环境下的传播,更重要的是通过建设数字家书管理和利用服务平台为每一个家庭提供“记忆账户”。
此外,为了鼓励家族成员可以深度参与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过程,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承办各类活动或创办电视节目,来吸引家族传承者主动分享家族故事。其中,这个故事可以是一个老物件、一段传奇经历、一组家训或家族礼仪等。如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文化类节目《我有传家宝》便是以传家宝为载体,讲述家族传承故事,从不同角度展现中国优秀的传统家族文化,进而实现了重构家族记忆的新路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乡档案记忆工程推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ATD009)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丁华东.论城乡档案记忆工程的性质与特点[J].档案,2016(2):14-19.
[2]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2.
[3]郭南南.宗族势力复兴对于村民自治的影响[D].安徽大学,2013.
[4]李雯.客家池塘龙舟赛的仪式展演与集体记忆[D].赣南师范学院,2014.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