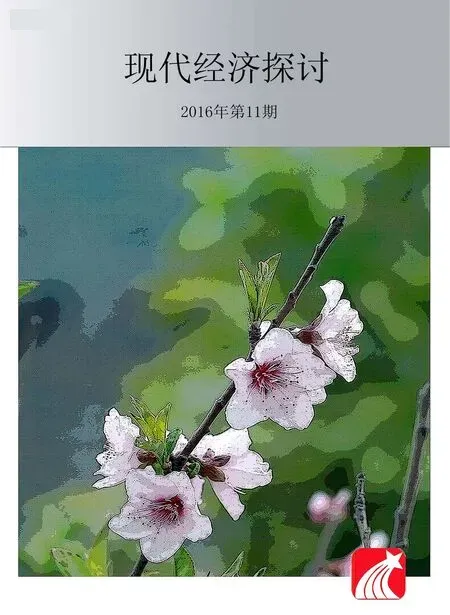资产证券化、金融稳定与银行低风险承担的“三元悖论”※
王晓
资产证券化、金融稳定与银行低风险承担的“三元悖论”※
王晓
在新常态背景下,资产证券化创新已经提速,其与金融稳定的组合将是未来较为明确的“政策组合”,在此过程中,银行将不得不承担较高的风险。为了防止银行高风险承担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及金融稳定的维护过程衍生的种种负面效应,我们必须转变监管理念,强化宏观审慎监管在监管体系中的地位,这是解决“三元悖论”中相关政策矛盾的重要支撑点,同时在策略上也需要明确流动性管理核心地位,以有效配合宏观审慎监管,也要构建统一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以实现金融稳定的“可持续性”。
资产证券化 金融稳定 风险承担 三元悖论
2015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以改革创新盘活存量资金”,充分显示了决策当局对资产证券化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将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动能支撑。但是,银行的风险偏好也会由于资产证券化的实施发生变化,并影响到金融稳定。有必要把握资产证券化创新、金融稳定及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逻辑关系,力求使资产证券化创新不仅成为银行实践“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推手,更要成为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途径。
一、文献回顾及理论假说
1.从微观向宏观的过渡:关于资产证券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研究
在危机爆发之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资产证券化微观功能的研究,比如增加流动性(Thomas,2001)、风险最优配置(Benveniste and Berger,1987)、优化资本结构(Leland,2006)等。但在后危机时代,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研究逐步转向金融不稳定等宏观效应,学者们一方面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造成金融不稳定的路径,比如内生流动性扩张(Bervas,2008)、资本市场挤兑(陆晓明,2008)、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辜朝明,2008)等,也有学者将资产证券化视为影子银行的范畴(Gorton,2010)。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从实证角度给出了资产证券化对金融不稳定影响的证据(庄毓敏等,2012)。
2.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争论
从创新初衷来看,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转移功能旨在通过减少银行风险承担来降低银行风险(Jiangli and Pritsker,2008)。但随着危机的爆发,持“资产证券化增加银行风险承担”的观点逐渐占据主流,主要体现在:第一,银行通过证券化仅实现了低风险转移,为此总风险承担变大(Nadauld and Sherlund,2013)。第二,银行通过提升杠杆率作为对资产证券化创新的反应,由此提高了风险承担水平(Shin,2009)。第三,资产证券化与信贷资产之间存在自我强化的“加速器效应”(刘丽娜,2014)。第四,资产证券化创新通过增加银行流动性,以鼓励银行承担高风险(Wagner,2008)。
3.关于资产证券化、金融稳定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假说”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既然资产证券化创新能同时影响到金融稳定和银行风险承担,那么银行风险承担与金融稳定之间也存在必然的联系,而将三者放在一
起研究的成果并不多(庄毓敏等,2012)。我们既希望推动资产证券化创新,又希望维护金融稳定,并保持银行低风险承担。理论上讲,金融制度需要在效率和稳定之间追求平衡,只要金融体系出现内在创新需求,则必会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存在(陆磊、杨骏,2016)。为此我们假设存在一个理论命题,即资产证券化创新、金融稳定与银行低风险承担之间不可同时兼得,只能取其中两项,这如同一种“三元悖论”①“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Mundell)提出,主要涉及的是国际金融问题,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只能选择其中两个。。如同在一个三角形中,若选择每两个“顶点”,“顶点”之间的边即显示无法实现的政策。由“三元悖论”所显示的三角形中,我们能够选择三种政策组合(见表1)。本文后续内容即是对这三种政策组合进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应采纳的政策组合,同时提出相应的监管建议。
二、金融稳定与银行低风险承担:“抑制”资产证券化创新
若要实现金融稳定与银行低风险承担,就必须放弃资产证券化创新,因为资产证券化不仅会对金融稳定产生“负外部性”,也会对银行低风险承担产生具有“争议”的影响。我们对该政策组合的逻辑阐述如下:
一方面,若单独考虑“金融稳定”或“银行低风险承担”,资产证券化创新均有可能产生“负外部性”。对于“金融稳定”而言,学术界关于“资产证券化创新导致金融不稳定”的观点已不存在争议,并且研究视角也较为丰富。但总体来看,资产证券化对金融不稳定的影响机制,一般是通过自身的两项基本功能,即风险转移和增加流动性来进行,若无法对功能的效力进行有效抑制,则将产生“负外部性”。对于“银行低风险承担”而言,在后危机时代,持“资产证券化创新导致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增加”的观点占据主流,可见,资产证券化创新是否会引起银行风险承担增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若无法对资产证券化创新实施有效监管,其必将引致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
另一方面,若同时考虑“金融稳定”和“银行低风险承担”,资产证券化创新确实需要受到“抑制”。因为:银行只有保持较低的风险承担,才能保持存款人或投资者不受外溢性影响,并且在我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中,银行低风险承担的维持也将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实现。为此我们必须实施较为严格的业务准入规则,或者直接实施行业限定,由此形成对金融创新的“抑制”,这对资产证券化创新也不例外。

表1 “三元悖论”所对应的政策组合与政策后果
总体而言,不管是单独实现“金融稳定”或“银行低风险承担”,还是同时实现“金融稳定”与“银行低风险承担”并存的局面,必须对资产证券化的创新行为采取必要的抑制措施,当然这种措施不仅会对资产证券化创新形成“抑制”,银行其余的金融创新也会受到“压抑”,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持银行低风险承担的同时,实现金融稳定。
三、资产证券化与金融稳定:“排除”银行低风险承担
次贷风波的出现证明资产证券化很难实现与金融稳定的“共荣”。从理论上讲,两者的“平衡”,将难以维持银行体系的“低风险承担”,这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在鼓励资产证券化创新的同时,为了确保金融稳定,必须强化中央银行的救助责任。同时,金融稳定的实现也必须要求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显性化”,这将使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大而不倒”的态度更加固化,必将引起银行的“道德风险”出现,这无疑会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第二,中央银行的救助责任及最后贷款人承诺将更加“常态化”,这必将导致机构层面的“道德风险”不断向宏观层面的“道德风险”演变。与此同时,随着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上升,将强化以转移风险为目的的资产证券化创新偏好,若无法有效控制创新边界,银行所转移的风险将在宏观层面上扩散。为了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中央银行将不得不进一步承诺救助职责,这样整个宏观经济将进入金融稳定——银行风险承担上升——金融稳定受到威胁——央行救助承诺固化——金融稳定……的“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必
将导致银行风险承担的“指数化”增长态势。
第三,在鼓励资产证券化创新的同时维护金融稳定,必须构建一个风险承担主体,以隔断风险向金融不稳定传染的路径。理论上讲,商业银行为专业化的风险经营机构,所经营的业务均具有不同的风险类型,为此银行无疑成为相应的风险承担主体。按照“三性”目标,只有在“风险”的环境中,银行才有可能获得足够的盈利机会,为此在风险边界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银行可以通过风险承担渠道来创造盈利机会,以实现盈利多元化,并缓冲不断上升的风险承担水平,以实现自身竞争力的提升。
鉴于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资产证券化创新与金融体系稳定的“组合”,其代价就是不断升高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当然,该组合还会导致另外一个后果,即中央银行最后贷款救助承诺与宏观层面“道德风险”的“双层刚性化”。
四、资产证券化与银行低风险承担:“容忍”金融不稳定
目前,“资产证券化创新将会对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若在此背景下继续使商业银行保持低风险承担,那么只能采取“容忍”金融不稳定的态度。可见,资产证券化创新与银行低风险承担的“组合”,将通过若干渠道导致金融不稳定,主要体现在:
第一,银行资产证券化创新的目的即利用相关基本功能,以实现风险权重的降低或风险转移,这也是银行保持低风险承担的主要途径。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功能利于帮助银行降低风险权重,并通过“真实出售”剥离高风险资产,可见基本功能能使银行风险承担降低。从历史经验可知,基本功能降低风险承担的过程,充斥着风险链条扩延、资产价格泡沫及内生流动性扩张等问题,这均是金融不稳定的重要诱因。
第二,任何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均与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密不可分。综览资产证券化创新历史,其迅速发展的时期,均出现了货币当局干预行为的“弱化”。同时金融创新的制度安排会对货币当局的干预行为产生或多或少的“排斥”偏好,这种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以及货币当局干预行为的“弱化”,无疑不利于金融稳定的实现。
第三,自由主义交易的制度安排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求交易双方自行承担风险。在货币当局干预行为“缺失”的情况下,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就显得极其重要,金融体系出现的各类金融创新(包括资产证券化创新),均会被银行当做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从而实现自身风险的规避与转移。但这些风险转移或规避行为均会威胁到金融稳定,可见,银行低风险承担的管理目的势必要求一定的金融不稳定承受力。
五、强化宏观审慎监管:解决“三元悖论”的支撑点及归宿
资产证券化创新不仅有利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有效应对“三期叠加”的冲击,更重要的是通过该创新渠道构建维护金融稳定的路径,为此,鼓励资产证券化创新与维持金融稳定将是未来较为现实和明确的“政策组合”。但该组合不可避免会导致银行高风险承担,以及中央银行救助政策的“固化”和宏观层面的“道德风险”。因此,为了减轻中央银行的压力,抑制由于政策救助导致的宏观层面道德风险,防止银行不稳定,需要构建宏观审慎监管系统。针对资产证券化创新及银行高风险承担,不仅要实现监管理念的转变,也要在策略上明确流动性管理的核心地位,同时在制度上构建统一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
1.理念上实现“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革命性转变
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理念出现了革命性转变,即监管主体逐渐摒弃“只要单一金融机构是安全的,整个金融体系就能保持稳定状态”的观点,而是认为“单一金融工具或机构的安全并不代表整个宏观金融体系的稳健”(周小川,2011),即逐步认同“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若采纳“鼓励资产证券化创新与维持银行高风险承担”的政策组合,更凸显了向宏观审慎监管转变的重要性。一方面,资产证券化创新与银行体系均会导致顺周期性,甚至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也具有顺周期的特点,为此需强化宏观层面的审慎监管予以应对,并采取逆周期缓冲制度来改变经济预期,以避免价格泡沫破灭或其他的负向冲击导致的不稳定问题。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创新及其衍生工具,使金融体系中各类金融机构实体形成一个闭合的信用网络结构,其不仅导致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同质性”,同时对于网络稳定的维护也不得不要求银行承担高风险水平,这就凸显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
2.策略上明确囊括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流动性管理”的核心地位
目前,中央银行的“货币供应量管理范式向金融
体系的流动性管理范式转变”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可见,为了更有效配合宏观审慎监管,必须明确“流动性管理”的核心地位。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构建具体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对于时间维度,流动性管理工具主要集中于针对“顺周期性”的逆周期监管工具;对于空间维度,流动性管理工具主要针对各类金融工具或机构“同质”的风险敞口,以及系统重要性机构“大而不倒”等问题实施的监管工具。
对于时间维度,首先,确定资产证券化创新边界,构建针对参与资产证券化创新金融机构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制度,以抑制金融机构过度创新资产支持证券,同时缓解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性。构建前瞻性的拨备制度,以防止银行风险承担导致的周期性波动。对高风险承担金融机构以及资产支持证券等金融工具的杠杆率进行动态监控,防止杠杆率周期性波动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对于空间维度,首先,强化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更为严格的资本监管。基于资产证券化及其衍生工具的杠杆率、交易量等指标构建一个系统重要性工具清单,针对这些指标有选择地对金融工具实行注册登记和结算。基于一系列流动性指标,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征税,目标即降低系统重要性机构或工具的“大而不倒”。
3.制度上构建统一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
强化宏观审慎监管同时,还需要在制度上构建一个统一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并防止央行和监管机构之间的各种利益或目标冲突。具体,可以考虑构建金融稳定协调委员会,注重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的结合。各类微观性监管机构,比如银行业监管机构、证券业监管机构和保险业监管机构等,必须根据各类金融机构或工具的功能实施监管,目的是消除监管“真空”及多重监管。各类微观型监管机构之间必须实现良好的协作分工和信息共享,并实现与宏观层面监管机构的信息传递;而宏观层面的监管机构通过对信息的加工与判断,对系统性风险或有可能影响到金融稳定的因素进行分析预测,从此形成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预警,然后将相关信息传递至各类微观型监管机构。此外,微观类和宏观类的监管机构必须囊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针对系统性风险的统一协调监管机制,由此形成基于“宏观审慎”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流程。
六、结束语
本文通过分析,可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资产证券化创新、银行低风险承担和金融稳定之间存在一种“三元悖论”,即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两个,放弃另外一个,三者之间很难实现一种“均衡点”。第二,鉴于我国新常态的背景,随着“三期叠加”冲击不断深入,资产证券化创新与维护金融稳定将是可选的“政策组合”,这个充满“矛盾”组合的代价必然导致部分金融机构承担较高的风险水平。第三,为了有效防范银行高风险承担带来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必须通过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来转变监管理念,这也是解决所选择“三元悖论”中相应政策组合的支撑点。第四,为了有效配合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在策略上明确“流动性管理”的核心地位,并在制度上构建统一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同时形成一套系统的,囊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针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流程。
1.陆晓明:《从金融产品异化角度解析次贷危机的特征、发展和前景》,《国际金融研究》2008年第11期。
2.[美]辜朝明著,喻海翔译:《大衰退——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幸存和发展》,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3.Gorton,G.,Securitized Banking and the Run on Repo[R].Yale and NBER Working Paper,2010.
4.庄毓敏、孙安琴、毕毅:《信用风险转移创新与银行的稳定性》,《金融研究》2012年第6期。
5.W Jiangli,M Pritsker.The Impacts of Securitization on U.S.Bank Holding Companies[J].Journal of Finance,2008,26:617-752.
6.Nadauld T,Sherlund S.The Impact of Securitization on the expansion of subprime credit[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3,107:454-476.
7.Shin,H.S.Securitiza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J].Journal of Economics,2009,309-332.
8.刘丽娜:《信贷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发展实践及政策思考》,《金融监管研究》2014年第4期。
9.Wagner,W.The Homogeniza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Financial Crisis[J].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08,17(3):330-356.
10.陆磊、杨骏:《流动性、一般均衡与金融稳定的“不可能三角”》,《金融研究》2016年第1期。
[责任编辑:张震]
F830
A
1009-2382(2016)11-0084-05
王晓,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济南25001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经济下行期资产证券化创新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6CJY070)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