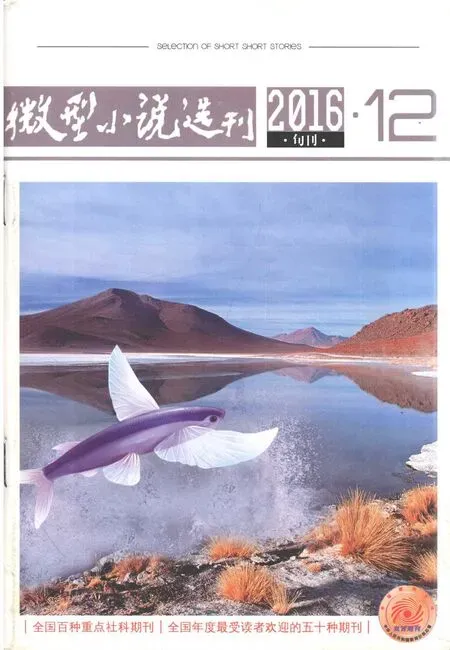较量
□高 军
较量
□高 军
十年后,保善还清楚记得,那次和检察官的较量中,他的心理防线是在一口浓痰下彻底崩溃的。
太阳有一竿子高的时候,他走出家门。在县城里,楼房高低错落,地平线早已被混凝土建筑物遮挡了个严实。这一竿子从哪里丈量让他感到无从着手,太阳现在是在楼与楼之间的缝隙里被挤压着,好似随时都能被挤碎沿着楼体流淌下去。但他之所以有这种一竿子高的感觉,是因为回到家中,觉得一切是那么美好,连亲近大地的感受都不一样了的缘故。
昨天回来后,他万千的感慨再次涌上了心头。家中的家具变得陈旧了,老婆的皱纹更多更深了,孩子也早已中断在国外的自费留学回来自谋职业了。他的家,已经变得和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没有什么两样。
一晚上并没有睡得太扎实,到接近天亮的时候他才进入了真正的睡眠状态。醒来后,他决定到公园里去走一走。已经是初夏时光,不到七点太阳就这么高了。他走在大街上,再次回想起自己十年前的那一切。
那时候,他在单位当着一把手,什么都由他说了算,不知不觉间慢慢就胆大起来,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最终因贪腐被送进了检察院。
他的牙关一直咬得很紧,检察官们几次讯问,他是死活都不说。他想只要自己坚决不承认,谁也拿他没办法。可是,办案人员也都是老手,又是严厉审问,又是心理疏导,几天后他就觉得有点招架不住了。
这天深夜,对他的讯问再次开始。他发现,这次审问他的核心人物换了,是一位接近六十岁的老检察官,那斑白的鬓发在电灯光照耀下,黑白更不分明了,好像全部变成了铁灰色似的。看着他,保善心中凛然一惊,知道这是一场缠手的较量。例行的讯问由年轻的检察官逐一进行着,老检察官的眼光只要扫过来,他就有一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渐渐地,他一直梗着的脖子开始发酸发软,需要强撑着才不至于低下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周围一点动静也没有,玻璃窗外的夜色在微弱的街灯照耀下显得更浓,室内的空气更加压抑。由于他不说话,检察官们也沉默了下来,双方无声地对峙着。最终,在几人明亮的目光长时间注视下,他的头终于低了下去。
室内越来越静,保善能听到几名检察官的呼吸声调各不相同,其中劲道最大的就是老检察官发出的。他仔细琢磨后,觉得这里面就是自己的喘气声有些不均匀,在越来越清晰的几个人发出的声息中,他的是最虚弱的。
“哞—”,保善听到一声长长的震响破空而来,他惊讶地抬起头来,只见老检察官微仰着头,用浑厚的鼻音使劲吸着气,鼻翼在持续翕动,随后微微张开嘴,喉咙和鼻腔共同用力,猛地咔一声,咳出一口痰来。他清晰地看到,老检察官撮起嘴唇,“噗—”一下,那口浓痰直直地向着四米开外墙角的一个痰盂准确飞去。静谧的空气生生被撕扯开一道缝隙,发出震耳欲聋的破裂声,那口浓痰准确地落进了目标之内。
“说吧—”在保善还处于一种被子弹射中的浑噩状态之中的时候,老检察官开始发话了。
在老检察官严厉目光的注视下,他再也绷不住了,把一切都坦白了出来。
自由是多么美好!走在去公园的路上,保善更加真切体会到了这句话的丰富内涵。他的住处与公园离得很近,不一会儿就进入了公园。
蓦地,他的眼光凝住了,在不远处的一个座椅上,坐着那位让他难忘的老检察官。十年过去,老检察官的头发全部变白了,着便服的他和县城里的普通老头也已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是自己的囹圄生活和他紧密相关的话,保善是认不出他来的。他看到老检察官的眼睛已经变得浑浊了许多,体力也大不如前。
经过这么长的牢狱改造,保善已经彻底悔过。但面对老检察官,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握紧拳头一步步向前走去,目光直视着已经有些老态的老人。
就在他走到离老人还有五六米远的时候,老检察官微微仰起脸来,鼻子向上一紧,“哞—”、“咔”、“噗—”,动作连贯,一气呵成。只见从他口中飞出的一口浓痰,又像飞旋的子弹一样,准确落入了前方三四米处一个尚未盖上盖子的垃圾箱内,劲道之大,令人惊讶。保善猛然哆嗦了一下,紧攥着的双拳慢慢松开,脚步停了下来。
他再次看了一眼安静地坐在长条椅上的老检察官,慢慢转身向回家的路走去……
(原载《羊城晚报》2015年12月14日 山东田文英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