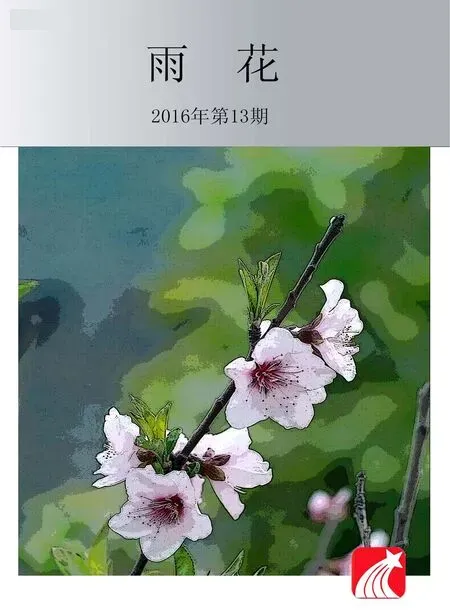文学这场婚姻
——毕飞宇工作室第五次小说沙龙实录
文学这场婚姻
——毕飞宇工作室第五次小说沙龙实录
庞余亮:我们生命中第一次的婚姻是跟生活结婚,第二次婚姻是与文学结婚。今天让我们跟我们庸常的生活离婚,进入第二次婚姻,与文学结婚。在文学的婚姻中,有很多东西纠缠在一起,就如我们今天和《雨花》读者俱乐部的同仁一起要探讨的小说《柴锁平的第二次婚姻》中的婚姻一样,那里面,既有灵与肉的纠缠,又有日常与远方的纠缠。
顾文敏: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小说里的男主角在外人看来艳羡的婚姻里过得并不幸福,但是我觉得从小说的角度讲,故事的叙述偏沉闷,情节发展中冲突不足,缺少画面感。就像看一部电影,情节的发展大部分靠的是旁白,观影人的感受,视觉的冲击力度就不够。我觉得贾燕人物的特征比较模糊,作者交代了她进入婚姻的无奈,但是有些铺垫还是不太够,比如孩子的出生没有激发她作为女人的这种母性。小说的写作一定要通过冲突来触动读者的心弦。这个小说的冲突不是很够,小说的结尾不错,但是余味不是很够,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暗示通过这次冲突让他们产生了交流,最后有产生圆满的可能性。或者贾燕在打了这两巴掌之后可能想彻底地挣脱婚姻的牢笼。同样柴锁平感到惊诧和愤怒,这样余味更重一些。
蔡永祥:小说的开头并不好。她说贾燕几次流露出不满,可是小说中没有显示出不满。小说的背景可能是模糊的,或者说是可疑的。柴锁平对第二次婚姻中的孩子并不是很亲近,他摔了电视机,孩子才被吓哭了。在吵架的过程中,儿子就已经要哭了,我觉得这个场景是不准确的。
庞余亮:这个小说是有追求的,她用一种静水深流的方法,慢慢地将小说往前推。但是她往前推的这个力量不够。两个人是生活中的孤岛,孤岛与孤岛之间有水,但是之间的浪花没有激出来。小说中人为地制造了一些浪花,比如摔电视机,小说更讲究的是逻辑性。小说中有很多地方显得太过随便,比如女性的角色都是小学老师,第5段她讲到了摔电视机,一直到了第33段再次讲到了摔电视机,中间隔了这么多段,这就说明小说的节奏感是有问题的,小说的作者可能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想到了结尾,这是一种写小说的方法,但是这种写作方法容易固化,她的目标就是一直向着贾燕反抽的目标而去。如果让我来写,我第5段就是第1段,然后围绕这个摔电视和耳光开始。
何雨生:其实一万字对于一个短篇来说,是非常舒服的,不论是情节的展开还是人物的刻画都应该是很从容的,但是小说的情节很平,本应该看得很流畅的,但是小说我们读起来很吃力。这个小说其实就是两巴掌的事情,假如我写的话,可能两三千字就解决了。我觉得小说叙述的节奏应该改换一下,她的目的性很强,直奔着两巴掌而去,有点像军人的步伐,比较单调。站在小说的角度,应该是文人的步伐,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或者回回头的写法。人物比较扁平。其中两个次要人物,一个徐晓红,一个马秀丽。我觉得徐晓红可以深入下去,贾燕之所以现在这个状态,应该与闺蜜有一些关系的。假如我写的话,要加强她们两个人的互动性。
郭翠华:我觉得作家在代替自己说话,她在叙述,人物没有成长背景,比如贾燕最后的结尾看起来非常好,但是她为什么会甩这两巴掌,小说中没有交代。小说中缺少文学的东西,叙述太多,她在替这几个人说话,应该是人物自己说话,尤其是心理的描写。人物没有成长的过程。
葛安荣:这篇小说表现了当代婚姻的一种尴尬与无奈的存在状态。两个人的生活习惯以及价值观念都不一样,性格脾气不一样,因此缺乏沟通,无法包容理解对方。平静中蕴藏着波澜。柴锁平的内心还是比较丰富的,经过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他用心用情呵护这个家庭,为后面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假如我来写,不会这么过于琐碎,现代婚姻投影的写法,单纯地写婚姻,写生活,如果加入文化的、经济的投射,比如柴锁平在单位上的状态,小说可能厚度上更重。小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写柴锁平与前妻的交往回忆,我觉得有主次颠倒的感觉。
毕飞宇:判断一个小说好不好,首先要看小说的密度。如何让它的密度提高,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短的第一段写柴锁平对第二个老婆的不满,可就在这么短的文字里这个信息他重复了两遍。比如“……这样不是挺好吗?”这句话一出现就将小说的质地拉空了,粗毛大孔。假如这个小说一上来,柴锁平是这样的状况,紧接着一个抱怨,这个小说的密度会紧密得多。小说的开头很重要。这个小说的四分之一才出来,我就知道这个小说是松的。如何让它变得紧致起来呢?小说的信息量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要尽可能多的提供信息,信息越多,小说密度越高,小说越好看。如何让小说密度高呢,就是要节省文字,如果你这个地方已经表现过了,用同样的文字就要寻求新的内容,如果你不能提供新的内容,那么就要立即把它删掉,一点点都不能保留。第二个问题。这个小说写的什么?不就两巴掌嘛?这两巴掌完全可以让这个小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走向和精神气质。一种可能是这个两巴掌是一个微型小说的体量,写了夫妻两人的故事。另一个走向,可以从两个巴掌上升到女权主义的高度,上升到女性主义的觉醒,上升到女性争取平等,争取尊严的高度,它都是可能的。那么小说究竟选择怎样的可能我们不知道。读者在等待第二个嘴巴出来的时候,小说一定是好看的。这个嘴巴下去之后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情绪行为,它是有价值取向的,但这个价值取向也不是作者在那说道理,是性格,小说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性格,最最重要的是由性格所体现出来的价值精神。如果仅仅有性格,小说是低级的,如果仅仅有价值取向,小说是低级的,如果由性格行为呈现出价值取向,小说就是高级的。
易康:我觉得小说是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人性问题,小说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小说缺乏必要的描写,使得小说的文学性有所削弱。小说对人物的精神世界是有所探究的,但是深度还不够,小说有表面,但是没有内在。这个小说人物在动,但是精气神好像没有动起来。小说的题目为“柴锁平的第二次婚姻”,那么主要人物应该是柴锁平,但是相比较他的两任妻子,好像人物形象稍微弱了点,而且人物的性格有点前后不一致。还有柴锁平的前妻,一开始都是称“柴锁平的前妻”,后来突然给她起了个名字。
汪夕禄:细节的缺失使得整个小说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给人留下印象的往往是一些经典的细节,而小说的作者并没有在这一方面多下功夫。细节的缺失使得整个小说缺乏深度。看得出作者是一个善于观察生活的人,但是作者并没有将小说的艺术和生活的真实巧妙地结合,虚实失衡,过于写实了。小说的节奏感不太强,最主要体现的叙述风格和情节推动上。人物的个性很鲜明,但是在塑造的过程中缺乏力度,对他们过于仁慈,下手不够狠,也不够准。
顾开华:我感觉这篇小说功底平实,主人公的两任妻子代表了生活中最典型的两类女性形象,前任好动、感性、浪漫,富有生活情趣,却与长期生活中的平淡有了冲突;不同的是现任很好地完成了生活中主妇的角色,两耳不问夫君事,却没有尽到一个女人、妻子的义务,生活如白开水,淡而无味。如果让我来写,我会把他们调过来写。
毕飞宇:一个经历过两个女人的男人,内心一定会有非常微妙的东西,写哪怕是不堪的东西。我特别渴望你们在写小说的时候将道德抛开,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不堪的东西,到小说中却是极其精彩的。第二个,这个小说的叙述太多,描写太少,小说是有两个东西构成的,一个是描写,一个是叙述,结合时空的具体刻画叫描写,脱离时空的作者交代叫叙述,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面对第二段正在进行时的婚姻时,一定是描写要多于叙述的,反过来,对于前妻一定是叙述多于描写的。如果这样写,小说一下子就是两个层面了,一个是画面,一个是画面的背景。
董维华:卡佛在《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中描写很多,叙述很少。这可以借鉴。这篇小说的结尾完全可以这样设计,让贾燕的那一巴掌下去,然后,柴锁平是继续回到这段婚姻中,还是开始了下一段婚姻呢?不说,留给读者去想象。
张晓惠:通篇我并没有看到一片飘动的叶子,小说没有给我们一个形象的东西,人物的形象比较模糊。
周新天:小说的结尾太带劲儿了,当小说中某一个细节特别有劲的时候,小说都不会太长。既然是最后两巴掌,前面费那么大劲儿干嘛呢?
邵明波:这篇小说与其说写的一个男人的两次婚姻,不如说写的两次婚姻中的女人。在小说中,这个男人看似为主角,其实他无关紧要,反而是他的前妻和现任妻子在生活中的状态才是更重要的,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一下。作者把握到了婚姻与家庭、婚姻与生活、婚姻与孩子,这些可能是一般写作的人愿意多着眼的东西。这篇小说还提到了婚姻与性,婚姻与金钱。那些内心所谓的龌龊和小说的创作,它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选对挖掘的重点。第二任妻子很有意思,为什么丈夫对她不满意,仅仅因为她不说话?因为她不会照顾孩子?我觉得可能不是,作者在暗示,他们在性活动上有问题。性活动可能是我们现代人婚姻生活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也是区别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的重要特征。小说中讲到了婚姻中妻子拿丈夫的工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她还拿得那么坦然、心安理得。我们的社会怎么了?我们的婚姻怎么了?我觉得可以更深入地挖掘这个东西。
毕飞宇:小说中丈夫给老婆开工资可能是个庸俗不堪的东西,你把它处理好了,能成为一个非常出彩的细节,在这个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文化经济背景下,丈夫给妻子开工资怎么了?他就能。他开了以后,不仅不脏,不仅不龌龊,它充满了温情,都是可能的。作家要有这个自信,告诉这个世界,我的虚构它就是真实的,小说的真实性永远不由现实去验证,而是由小说家的能力确定。
王锐:这个小说的逻辑还是非常合理的,只是结构有点欠缺。它用了足够多的铺垫,谈到婚姻与金钱的关系,一开始我觉得柴锁平与社会的环境把贾燕变成了这么一个人。贾燕的父母认为这个婚姻很划算。柴锁平的妈妈病危,贾燕的婚姻类似于冲喜。小说中写到贾燕的第一个男朋友车祸死去了,她不得已嫁给了比自己大很多,离过婚,有孩子还有家庭暴力史的男人,她的内心应该是很不平静的,柴锁平有个表达,他想好好珍惜一个人,好好过日子。而贾燕最后不要钱而是要去扇他两个巴掌,其实她是想挣脱她内心的困境。换成我写的话,一个男人有过暴力,是很难克制的,柴锁平在和贾燕的婚姻中克制了那么长时间,虽然有不满,但是他没有把那巴掌扇出来,我想他是有过日子的信心的,我写的话我会把他对这种冲动的抑制,把对生活过好的渴望表现得更强烈一点,他这两巴掌扇出去也是非常艰难的,在他感觉不到这份爱的婚姻里,他觉得特别难受。
顾维萍:好的小说应该可以让我们遇到另外一个自己,这篇小说没有呈现出它自身的可能性。好的小说应该有它表达的意向或主旨,可是我没有看到小说流淌出来的主旨。一个作家有权利与责任,这个小说作者没有用好自己的权利,过度地使用全知视角叙述,另外我觉得她不太负责,不太严谨。究竟由谁来讲这个故事,这篇小说我觉得视角值得商榷。我觉得不用第三人称会更好。
冷玉斌:我觉得小说体现作者内心的慈悲。小说是否有一些被压缩的东西,是否可以再添加一些东西,可能变成一个中篇,甚至是一个长篇。它把所有的故事压缩在了一次冲突里,从砸电视到甩巴掌,这个中间它的时间和空间一直是交错的,交代了柴锁平的两次婚姻的来龙去脉,由此看来,结构上还是蛮有张力的。在迂回的几乎独白的叙事当中,把两次婚姻中纠结的人描摹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它很平呢?因为作者考虑的方向始终是单向的,始终都是柴锁平在观察贾燕,而没有观察到他自己,如果从这个角度挖掘,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声部。自己对自己内心的推动是缺乏的,这就少了很多力度。语言是琐碎的、零散的,但是和整个小说很契合,生活是个谜,充满了矛盾和很多琐碎的东西,作者用琐碎的语言把它组织起来,也是很有风格的。静悄悄的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关键是在对这个不为人知的东西的描写中缺乏了力度,缺乏了一种勾住我们继续往下掘进的能量。
张王飞:语言中有很多的重复,第一段和第二段重复,太拖沓。开头没有把人抓住,看她在那绕来绕去,绕了半天才进入主题。
王笋:我觉得首先小说的逻辑不是很清晰,另外那一段“……做爱的时候……”转得太快了,没有情境,没有铺垫。如果多一些情境进去,可能对后面的叙述会更好一点。一万字的小说里,塑造的主要的人物是柴锁平,次要人物是贾燕、孙晓月,配角是柴锁平的母亲、贾母、姐姐、哥哥、嫂子、孩子。贾燕既然是老师,难以沟通,不爱学习,不会育儿,有点异议。人物的性格难以统一。另外从柴锁平砸电视机到买电视机,从甩巴掌到想用钱补偿,这是一个男人对自身的思考,是一个亮点,我觉得应该深度挖掘。
李心丽:这个小说没有典型的人物、典型的环境、典型的故事,为什么我要写这个作品呢?柴锁平是一个有过婚姻、有过爱情的男人,贾燕是有过恋爱的人,两个都经历过爱情的人,进入婚姻后,两个人不来电,他们的节奏始终不在一个线上。我想表达的就是每个人都是一座封闭的城堡,要想进入另一个人的城堡,没有一个正确的通道,他是进不去的,柴锁平有过爱情的经历和体验,但是面对贾燕,他就没有那个通道。两个人曾经的经历与经验都用不上劲。进入婚姻之后,他们都在偷偷地观察对方,猜度对方。我觉得大家给我的建议特别好,给了我这个小说更多的可能性。在小说中我还写到了柴锁平的母亲,我想表达的是那种看不见的疼痛,别人觉得他的第二次婚姻一定是幸福的,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对自己失去的东西反而更怀念。
王大进:我们每个人在写作中都有缺陷,但是通过自身的学习,每个人都有提高的可能。我们写作有两种途径,一种听了一个好玩的故事,很容易就上手去写了,这个故事本身就吸引我,只要稍加虚构就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另外一个就是不好干的活,就是作家通过阅读和对生活的理解,有自身的发现,这篇小说就是从自身出发,或者是从观察生活出发,写这样的小说是非常难的,这是需要勇气的。这个小说故事性并不强,而是作者想要对生活有所表达。一个作家没有怀疑精神,小说是写不好的。这篇小说可以看到经验的不足,就如小说开头如果写到了猎枪,那么小说中你的猎枪一定要响。人物出现得太突兀,没有对人物有所交代。缺少了对主人公的命运或者故事情节起到促进作用的细节。第二次婚姻应该是第一次婚姻的递进,或者是对比关系,没有对比,递进不强烈。另外视角的不稳定。我们写小说不能快,在思考的时候要想得透一些。张爱玲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作家要写出这种慈悲感。
庞余亮:谢谢此次沙龙的嘉宾作家王大进先生。今天三个半小时的讨论令人难忘。记得李心丽曾写过一篇小说叫做《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我们爱上文学的心都是很顽固的。经过五次小说沙龙洗礼的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这颗顽固的忠诚于文学的心,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与文学厮守的苦乐时光。
(郭亚群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