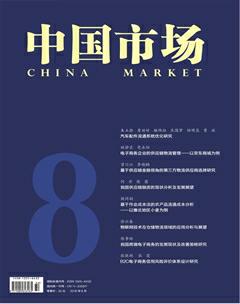论死刑缓期执行的适用条件
吴泽新+谢天莲+张泽凯
[摘 要]为了实行慎用死刑的思想,我国首创了死缓制度,这一制度使得死刑适用有了缓冲之地。死缓适用的条件包括罪当处死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这两个条件。是否达到罪该处死的条件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立场,从罪质、罪量和责量等因素进行判断。在判断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时候应该从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及主观恶性两个方面进行。
[关键词]死缓;罪当处死;主客观相统一;人身危险性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2.291
1 前 言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国首创了死缓制度,其雏形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死刑保留”,正式形成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在1979年正式规定在刑法典。至此,死缓制度完成了从政治斗争策略到法律制度的转变。对死刑的控制有立法途径和司法途径,在学界的大力呼吁和我国的社会治安现状稳定等因素影响下,我国与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一次性地在立法上废除了13个经济犯罪罪名,2015年在《刑法修正案(九)》又废除了9个非暴力犯罪罪名,这两次刑法修改中我国一种废除了22个死刑罪名,占废除前死刑总罪名(总共68个)的32.35%,可以说我国的死刑立法控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大量而又恰当的适用死缓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慎用死刑的死刑政策应有之义。一般认为,死缓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所以其适用首先应该到罪该处死的程度满足罪行极其严重的前提条件,然后满足“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实质条件。由于刑法条文对于这两个条件规定的比较模糊,所以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明确。
2 死缓的适用的前提条件:罪当处死
2.1 罪当处死的正面规定
罪当处死是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条件,同时也是死缓适用的前提条件。我国现行刑法即1997年刑法第48条第一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由于对极其严重的罪行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导致了学界和实务界对此理解不一,主要形成了以下观点:一是社会危害性说,该说认为极其严重的罪行是强调犯罪的客观危害。该说主要强调犯罪所造成的客观的损失严重和侵害的法益性质严重,由于该说只强调犯罪的客观危害,但是我们现在的刑法学强调对犯罪的评价不能只看客观危害,还要看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二是主客观标准统一说,该说认为应当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考察极其严重的罪行。如“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犯罪的情节极其严重、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的统一”。[1]刑法学家赵秉志教授,在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立场下,认为极其严重的罪行要从罪质、罪量、责量三个方面来确定。[2]三是法定刑标准说,该说主张应当将法定刑中的法定刑设置作为衡量刑法轻重的标准。“罪行极其严重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行”。[3]笔者认为,受重刑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刑法对死刑的设置过多很难说反映了罪行极其严重,比如对非暴力犯罪、经济犯罪设置大量的死刑,这两次刑法修正案正是在当代反思我的死刑规定过多的背景下认为许多犯罪不符合极其严重的罪行才做出废除死刑达22个罪名之多。
笔者赞成主客观标准统一说,该说认为应当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考察极其严重的罪行,符合我国一贯主张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罪行极其严重不仅要具备社会危害性大,而且要具备主观恶性大和人身危险性大,可以借用1979年刑法规定的“罪大恶极”,不仅要“罪大”即造成严重的后果,对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大,犯罪性质严重如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人身安全犯罪,而且要求“恶极”即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当然人身危险性是一个既包括主观要素也包括客观要素,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客观归罪和主观归罪的错误倾向。赵秉志教授在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立场下,认为极其严重的罪行要从罪质、罪量、责量三个方面来确定,该我们提供了有益参考。
2.2 特殊主体死刑的免除
本文所称的特殊主体是指老年人、妇女、儿童、智力障碍者等人。1997年刑法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对该条的理解如下:一是未成年人和怀孕的妇女绝对不适用死刑。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这体现的我国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对未成年人的年龄把握实行严格标准,必须十八周岁生日的第二天才视为成年人,要求必须对未成年人的年龄查证属实。对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既是保护妇女本人,也是保护未出生的胎儿,让其在自己母亲的抚养下成长。国际上有些国家规定对新生儿的母亲也不得适用死刑,而且有的国家设置了从新生儿出生后的36个月不得对妇女适用死刑,笔者认为像这样好的立法案例值得中国学习。二是对老年人原则上不适用死刑。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了对年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原则上不适用,这是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一次立法完善。国外有的法律对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年有界定为六十五周岁、七十周岁或八十周岁。
3 死缓适用的实质条件:不是必须立即执行
正如梁根林教授所说,“虽然死缓并非独立于与死刑的一种刑罚方法,而是区别于死刑立即执行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但是适用死缓,却是一个生死两重天的不同结果”[4],所以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理解对于正确适用死缓意义非凡。学界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理解不一,主要的观点如下:一是老一辈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认为死缓是罪大恶未极,“可否判处死缓‘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主要看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考察其主观恶性大小和人身危险性深浅,这是犯罪分子的人格状况”[5]这种理论借用1979年刑法43条规定的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保持了理论解释的一贯性,虽然1997年刑法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从文字表面上看仿佛只强调对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但是我国1997年刑法是受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慎用死刑、坚持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影响并没有扩大死刑适用的意思,所以宜理解为包括犯罪的客观危害严重,主观恶性大,人身危险性大。所以适用死缓的实质条件(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应该是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不是太大。二是认为只有人身危险性是不是立即执行的实质标准。“人身危险性程度是死缓适用的分界线”[6],这种观点看到了适用死缓的实质条件的一个方面,对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一种途径,但没有看到主观恶性对死缓适用的影响。三是社会危害性说,认为是否立即执行必须以社会危害性来进行判断。该说认为构成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区间,而死缓是刚刚达到这个区间的下限或超过这个下限不远。[7]该学说看到了社会危害性对适用死缓的影响,但是没有看到是否适用死刑由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决定的。四是任志中博士在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即宽恕理论,“决定对死刑犯是否适用死缓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二是影响死缓适用的从宽因素。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会组成适用死缓的充分必要条件”。[8]可以说宽恕理论这种新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考,为传统刑法学理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重刑主义影响比较深远的中国尤其需要宽恕,以一种宽恕的心态来对待社会中出现的不好的行为,这也是以德报怨这一传统美德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笔者认为,判断是否必须执行的实质标准是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和主观恶性相对而言比较小。就像上文中介绍储槐植教授认为可否判处死缓“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主要看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考察其主观恶性大小和人身危险性深浅,这是犯罪分子的人格状况。
参考文献:
[1]高铭喧,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56.
[2]赵秉志.死刑研究报告[M].法律出版社,2007:17-24.
[3]赵廷光.论死刑的正确适用[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3.
[4]梁根林,王军.死刑立即执行与缓期执行的界限[J].人民检察,2009(4).
[5]储槐植.死刑司法控制:完全解读刑法第四十八条[J].中外法学,2012(4).
[6]仝其宪,孙娜.死缓适用条件的梳理与评析[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7]胡云腾.死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235.
[8]任志中.死刑适用问题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