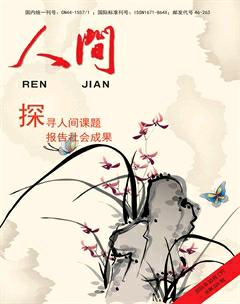陶寺文化族属刍议
摘要:陶寺文化是一支分布于山西襄汾县的龙山时代考古文化,内涵丰富,出现了国家雏形。学术界不断探讨陶寺文化的族属,并且形成陶寺文化的尧都说和夏文化说,本文认为古代典籍对于尧舜禹时代的记载多难以确信,陶寺文化的内涵也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其是尧都或夏朝文化,陶寺文化因外族入侵发生变化并走向没落,最终去向成谜,二里头、二里岗等夏商文化并没有继承陶寺文化,因此陶寺文化并不是尧都或者夏朝文化,而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古代方国。陶寺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之一。
关键词:陶寺文化;尧都;夏朝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 271 -02
陶寺文化是一支分布于晋南地区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30多年来,考古学者对陶寺遗址不断进行发掘,并且发现丰富的文化遗迹,学界就陶寺文化的特征、分期、年代、性质、族属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专家学者们尤其重视陶寺文化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源头的意义。
一、目前学术界对陶寺文化的族属争论
目前学术界在陶寺文化族属问题上,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陶寺文化是“夏文化”,即陶寺文化是夏朝先民创造的,陶寺遗址就是夏墟。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王克林、何建安等人。另一种观点认为陶寺文化是“尧舜文化”,其创造者可能是历史上的尧舜。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俞伟超、董琦、高炜等人。
二、陶寺文化族属并非尧舜禹
认为陶寺文化是“夏文化”或者是“尧舜文化”的两种观点均把史书上对尧舜禹的记载当作信史来对待,把陶寺文化和古代典籍对应起来,找出典籍中有关尧舜和夏朝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用来与考古发掘所呈现的特征进行对比,寻求两者的交集,然后进行推测,这样相互论证非常有必要,但是容易从古代典籍先入为主,容易忽视了从陶寺遗址本身表现出来的文化特点进行考察。
(一)典籍对尧舜禹记载不明确。
古代典籍关于尧活动和居住地的记载主要集中于山西境内,但具体地点难以确定。《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中引《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汉书·地理志》载:“晋阳本唐国,尧始都于此。”
古代典籍关于舜出生地多有争议。《史记》、《竹书纪年》等都说生舜于姚墟,但是姚墟到底是何处,唐《括地志》记载是今天河南濮阳,另有在余姚说、在今山东菏泽说、在浙江上虞说、在山东诸城说、在山西临汾说,各种说法差别较大,由于没有考古证明,难辨真伪。
古代典籍关于禹出生地也多有争议:《竹书纪年》载:“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有人认为石纽在四川,也有人认为石纽在今陕西神木。《史记·六国年表》、《帝王世纪》等说大禹为西羌人,由西北进入中原。《史记·夏本纪》中记载大禹“导河于积石”,但具体位置不明确。
尧舜禹距古代典籍成书年代甚远,其故事流传产生变异,同时不排出后人添加新说,篡改历史,歪曲事实原貌的可能,因此古代典籍对尧舜禹的出生和活动地点说法各异,自相矛盾。顾颉刚、刘起釪的《尚书校释译论》就认为《尧典》中的很多情节来源于《山海经》《楚辞》《庄子》等书中的神话①,而儒家更是依据自己的伦理和理想把这些神话进行二度创作,编撰出尧舜禹的传世纪神话②。后世学者在论证陶寺文化的族属时大多没有对尧舜禹这段历史进行质疑,而多是寻找这些记载和陶寺文化的相似之处,这样用来推测陶寺文化的族属,其结果值得商榷。
(二)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考古证明。
陶寺文化出土有祭祀、观察天象、象征最高权力作用的建筑物,墓葬葬品非常丰厚,出土具有“王气”的礼器,大型墓葬约占总墓数的1.3%,这些表明陶寺先民已经知道观察天象用以指导农事,陶寺文化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形成了国家雏形。但是在新石器时代,这样的发展水平不一定只有尧舜禹或者夏朝先民才能达到,远古时部落林立,石家河、良渚、红山文化更是表明上古时期完全可能存在着历史上所没有记载的较为发达的早期文明,因此陶寺可能是一个历史典籍所没有记载的古代方国。
陶寺遗址出土的扁壶上有朱书陶文,学者对陶文内容进行考证,有认为是大禹的名字③,有认为记载尧的功绩④,也有认为其中一个是最原始的“尧”字,另一个可能是“文”字,还有认为其中的陶文就是商代甲骨文的直接祖先⑤,更有认为陶文是“长篇”《尧典》成书之前的一个最原始的简约脚本⑥。这样考释和解释是值得商榷的。战国《荀子·解蔽篇》载古时候“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陶寺上层遗存与后冈二期文化基本上没有多少联系,难以确定两者是同一个文字系统。如果陶文记载的是尧或者禹,很难解释的是,他们如此高贵的名字,怎么可能会写在一个扁壶上,而且还分开,一个字写在前面,一个字写在背面,他们的伟大的事迹怎么就只用几个字写在不起眼的扁壶上,这和他们的身份是不相符合的。中国新石器文化,比如秦安大地湾文化、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就有发现有刻画各种符号的陶片,而这些符号目前难以释读,陶寺遗址的陶文就一定是有关于尧或者禹的记载?
(三)陶寺文化变异的原因。
陶寺文化中期与早期之间、晚期与中期之间发生了两次大的异变,前者被后者所取代,这种取代甚至是通过暴力来实行的,而且陶寺文化中后期有大量外来文化因素⑦。通过对陶片中微量元素、陶寺出土人骨、陶寺动物骨骼进行科学分析得出,陶寺中后期陶土来源与前期不一样,陶寺中后期外来居民分别占当地人口的50%-76.9%之多,陶寺中绵阳骨骼在晚期中大量发现,表明陶寺文化中晚期,特别是晚期发生大规模、大范围、性质惨烈的异变,而且非常可能是来自西北方向游牧民族的侵入、破坏、报复等行为导致的,他们毁城垣、废宫殿、拆宗庙、扰陵墓。陶寺灰坑出土的大多数头骨片上都有裂缝或创缘和创孔,从形态判断,这些现象都是死后造成的⑧。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和破坏,最终导致陶寺文化晚期衰落,这与古代典籍对尧舜禹的记载相差较大,因此很难确定陶寺文化就是尧的都城遗址或者是夏朝早期的都城遗址。
(四)陶寺文化去向成谜。
史书上多载尧舜禹三代相连,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有先后的继承关系,陶寺文化年代的上限约为公元前25世纪,下限为公元前20世纪,前后延续500多年⑨,目前学界多认为夏朝为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⑩。陶寺晚期文化已经进入夏朝纪年,如果是尧舜禹都城的遗迹,陶寺文化的晚期应该就是大禹时代,也就是夏朝的早期阶段,陶寺晚期文化就是夏朝早期文化,那么夏朝后世文化应该延续和传承陶寺文化。目前学术界多认为二里头为夏代文化B11,但是陶寺文化无论同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还是二里头都接不上,虽然东下冯类型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受到陶寺文化的影响,但是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传承关系B12。显然,二里头并没有继承陶寺文化,因此把陶寺文化的创造者认为是尧舜禹或者是夏朝先民是很难成立的。
三、结语
陶寺文化遗址的面积非常大,并且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大型的建筑物,等级分明的墓葬,高规格的礼器,具有“文字“的陶片,这些都表明陶寺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非常发达的一支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历史典籍对于尧舜禹的记载多有矛盾之处,而陶寺文化的建筑、墓葬和陶文等遗物遗迹所表现的文化内涵并不能直接证明陶寺文化就是尧都遗迹或者大禹都城遗迹。陶寺从中期到晚期,一直受到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些游牧民族在战争和冲突中,最终取得胜利,占据了陶寺文化,他们摧毁陶寺原住居民所创造的文化和建筑,甚至捣毁原住居民的坟墓、坑杀原住居民,外族的入侵最终导致了陶寺文化的衰落。被认为是夏朝文化的二里头,和目前所知道的中原其他文化类型并没有直接继承陶寺文化,陶寺文化曾经很发达,后来去向不明,这些都表明陶寺文化不太可能是尧都或者夏朝文化,陶寺文化可能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古代方国。
注释:
①顾颉刚 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一版,第154-230页。
②刘宗迪:《<尚书·尧典>:儒家历史编纂学的“神话创世纪”》,《民俗研究》2014年第6期,第23页。
③李建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解希恭《襄汾陶寺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620-623页。
④罗琨:《陶寺陶文考释》,解希恭《襄汾陶寺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624-629页。
⑤冯时:《文字起源于夷夏东西》,解希恭《襄汾陶寺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630~632页。
⑥何驽:《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三代考古》2004年第0期,第351-353页。
⑦张国硕:《论陶寺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异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9年第18期,第46-49页。
⑧张雅军、何驽、尹兴喆:《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人骨的病理和创伤》,《人类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272页。
⑨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第532页。
⑩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概要》,《文物》2000年第12期,第60页。
B11陈旭:《二里头一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第9页。
B12高炜:《陶寺:一个永远的话题》,解希恭:《襄汾陶寺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作者简介:蓝胤天(1991—),男,瑶族,广西大化人,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方向:新石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