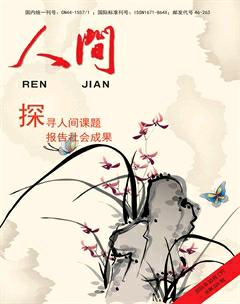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视觉艺术探析
摘要:论文意在探讨张爱玲小说中的视觉艺术特质,并通过分析张爱玲与视觉艺术之联系以及视觉艺术在其小说作品中的具体体现,阐述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对于视觉效果的独特追求和不凡造诣。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视觉艺术
中图分类号:I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 222 -02
一、张爱玲与视觉艺术
谈及视觉艺术,诸如电影、话剧、音乐剧、服装设计等等,都可以归入其范畴。目前,较为有代表性的认识是,视觉艺术是一种运用不同符号的形象语言。从皮尔斯的符号学的角度,大致可将视觉艺术作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旨在传达某种情绪,比如现代主义的抽象作品;第二类在传达情绪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影响观者的行为趋向,例如以宣传为目的的视觉艺术作品;第三类则试图让观者在思维中产生一系列推论,即产生一个联想过程,而这个过程之所以产生必定依赖于作品能够获得观者的情绪认可。[1]从这里可以看出,视觉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对不同符号的运用,这说明在视觉艺术的范畴里,涵括了多种不同类型的表达形式。其中既有二维的静态的绘画艺术,也有三维的雕塑艺术和动态的影视艺术,它们既是对色彩、线条和光影等符号的综合运用,也有着对物质材料和造型技术的严格要求。另一方面,视觉艺术是一种形象语言,它通过视觉形象来传达信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起源于象形文字的中国汉字也可部分归入视觉艺术范畴,比如书法和篆刻等具有审美价值的汉字运用形式。但视觉艺术作为形象语言,其信息传达功能不像语言文字和数据图表那样直接明了,它有自身的结构和规则,接受者必须基于一定的感知能力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和理解视觉形象语言。
在张爱玲的时代,与她有关的视觉艺术主要是电影。
上海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是远东的国际化都市,其现代化程度相当之高。“现代都市生活的绝大多数设施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开始传入租界了;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2]P7其时正值中国国内外局势紧张动荡之际,然而上海在这狂波巨澜中仍然保留了一片醉生梦死的世外桃源,各大租界的消费文化呈现繁荣之像,大光明剧院、南京大剧院、大上海剧院等一流的电影院成为主要的消费场所,直至三十年代末,上海已经有了三十二到三十六家影院。[2]P95张爱玲便生长在这一时期的上海,可以说上海这个特殊的文化场域造就了张爱玲与电影的不解之缘,也为她日后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打下根基。
张爱玲作品中的艺术根基是很深厚的,她是一个内在张力很大的作家。这种张力体现在很多方面,除了作家自身敏锐的感触、独到的构思、细腻的描绘以外,其视角独特的表现技巧、对自身独特生活经验的反复书写,也是很值得探究的。正是由于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内在张力和跨领域的影响力,我们可以从她的作品中挖掘出很多视觉艺术特质。在小说创作中,作家以较为独特的艺术表达给读者呈现出某种视觉艺术的叙事方式,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视觉感受。下面主要从电影语言方面来探讨视觉艺术在张爱玲小说中的具体体现。
二、小说中的电影元素
著名学者李欧梵评价张爱玲时,说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影迷,这一点可从她弟弟的回忆录里得到印证:有一回他们许多人到杭州去玩,刚到的第二天,张爱玲看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的广告,就非要当天回上海去看不可。大家劝不住,只好由她弟弟陪她回去。一回上海就连赶了两场,她看完电影还感慨地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3]P92一九四二年,张爱玲因为经济问题放弃学业,不得不靠写作为生,这时她主要是为英文报纸《上海泰晤士报》撰写影评,其对电影的挚爱可以说得到发挥余地。此后,除了引人瞩目的小说创作外,她也创作剧本。一九四四年,张爱玲将自己的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该剧在上海上演时曾轰动一时。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前期的上海时期,张爱玲主要与导演桑弧合作,创作了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和《金锁记》,除了《金锁记》没有拍成,前两部电影在当时都影响很大。1956年至1964年,这一段时间是张爱玲客居美国的时期,主要是接受宋淇的邀请,为香港电懋影业公司撰写了十个剧本,其中八部被拍成电影。[4]P91-97从张爱玲的这些经历中可以看出,她对电影的了解程度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电影爱好者的层次,她将电影元素运用到小说的创作中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有丰富的实践作为基础的。
(一)蒙太奇。
蒙太奇(Montage)一词源于建筑用语,后被引用到电影创作中,指一种叙述手法和表现手段,即一组镜头的拼贴剪辑,文学作品中也常借用此种手段。张爱玲在《对照记》里曾用蒙太奇来形容人生,她用电影语言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的感悟,抽象中带着一点值得玩味的情愫。
“箱底垫着的却是她当日从乡下上城来随身带着的蓝地小白花土布包袱,她把手插到那粗糙的布里,一歪身坐在地下,从前种种仿佛潮水似的滚滚而来……水乡的河岸上,野火花长到四五丈高,在乌蓝的天上密密点着朱砂点子。终年是初夏。初夏的黄昏,家家户户站在白粉墙外捧着碗吃饭乘凉,虾酱炒蓊菜拌饭吃。……霓喜忽然疑心她还是从前的她,中间的十二年等于没有过。”[5]P294
由一个“蓝地小白花”的包袱引起霓喜对过往穷苦生活的回忆,这有些类似于文学创作中的插叙手法,但不能完全等同。这种蒙太奇往往是两个镜头之间的一种倒退式跳跃,且这种时间上的距离往往较长。在电影中,这种技巧常常被用来表现人物的回忆和追叙这种纯粹个人回忆式的叙写,用片段式的画面描述将小说中的现实与虚拟连接起来,实现了电影中的闪回式表现手法。
“家茵突然双手掩着脸,道:‘你别尽逼着我呀!他——他这一生,伤心的事已经够多了,我怎么能够再让他为了我伤心呢?夏太太挣扎着要下床来,道:‘虞小姐,我求求你——家茵道:‘不,我不能够答应。她把掩着脸的两只手拿开,那时候她是在自己家里,立在黄昏的窗前。”[6]P285
这双手的一掩一拿开,时空已经发生了变化,虞家茵已经从夏宗豫的公馆回到了自己简陋的房间,从夏太太的床边来到了黄昏的窗前。这种手法主要是利用两个画面中的相似造型因素来进行切换,它能有效避免画面切换时的突兀感。利用造型因素进行的画面切换,这种手法的特色是毫不重视时间,它将许多时间距离可能较长的事件并列在一起,但为了说明这种并列,事件之间并不严格遵守同时性。[7]P151
“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5]P232
这段描绘很精练传神,手段高明,十年的时间跨度凝聚在一面镜子里。这种画面剪辑方式在电影中又叫做“叠”,它是把两个画面叠印在同一张胶片上,在一个画面逐渐淡出的同时,另一个画面逐渐淡入。[8]P147使用这种手法,可使两个场景之间的过渡形成自然的联系。
(二)镜头视角的运用。
在电影的拍摄中,根据镜头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和镜头焦距的长度,可以分为特写、近景、中景、全景四大类镜头。[7]P20导演往往会根据预想的画面感来选择不同的镜头效果,这与小说家构思描写景物的视角有异曲同工之处。张爱玲的小说在影像化书写上是独具一格的,她就像一个导演,总能恰到好处地摆放她的镜头。
全景镜头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全景是摄影机在不移位的情况下,围绕它的垂直轴或水平轴的一种旋转”。[7]P43这种镜头的运用,有引入和结束的作用,还常用于烘托气氛、营造氛围。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黄鳝,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5]P148
《封锁》是一篇时空相对封闭但构思精巧别致的小说,主要讲述了上海沦陷时期一对男女在封锁期间于电车上发生的一次短暂邂逅。小说开篇展现的是一幅太阳底下的车轨图,车轨抽长、缩短,让人感受到电车行进的节奏,这其中还有物化了的人——开电车的人盯住了两条蠕蠕的车轨,不发疯。
“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上的故事是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搬演的,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鼻,唱了、笑了,袖子挡住了嘴……然而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5]P160
《倾城之恋》的开篇就是一幅上海万盏灯火的夜景图,配上胡琴咿咿呀呀的苍凉的声音,更显出拉胡琴的白四爷的孤凄和整个白公馆的落败。这种动态的全景镜头式描写,让故事的开篇就显露出引人入胜的魅力,让人隐隐觉得这日常生活场景中有着不寻常的传奇。
特写镜头在电影中起到放大和强调的作用,运用特写来表现的人或者物往往能立刻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在小说中也不例外。
“下午的阳光照到一座红砖老式洋楼上。一只黄蜂被太阳照成金黄色,在那黑洞洞的窗前飞过。一切寂静无声。席五太太坐在靠窗的地方,桌上支着一面腰圆大镜,对着镜子在那里剪刘海。那时候还流行那种人字形的两撇前刘海,两边很不容易剪齐,需要用一种特别长的剪刀,她这一把还是特地从杭州买来的。”[9]P1
这是小说《小艾》的开篇,阳光中的红砖洋楼,金黄色的黄蜂从黑洞洞的窗前飞过,屋中昏暗,镜子中席五太太的刘海是老式的两撇人字形,需要用专门的剪刀来剪。这一组画面中最有特写风格的是窗前飞过的金黄色黄蜂,虽只是简单的一笔带过,但足够引起读者的兴趣,让人迫不及待想要进入故事之中。
张爱玲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电影表达技巧,将电影语言与文学语言近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与她长期担任编剧工作从而熟悉电影的创作手法不无关系。李欧梵提到:“‘五四以后,不少作家在写作中用了电影手法而不自觉,仍奉文字艺术为圭臬;到了三四十年代,上海的都市作家才开始重视电影。”[10]P87这里面就有“新感觉派”的刘呐欧和穆时英,此二人特别嗜爱电影,不但在其作品中大量运用电影技巧,而且对电影美学颇有研究。然而他们的作品“似乎太过洋化,内中的电影技巧直接从好莱坞电影照搬过来;张爱玲的特长是,她把好莱坞的电影技巧吸收之后,变成了自己的文体,并且和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技巧结合得天衣无缝。”[10]P87
三、结语
李欧梵曾从西方现代性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他分析了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不同表现,提出了一条叙事线索:日常生活的叙事美学。他提出:“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是把艺术人生和历史对立的。”[10]P76正是这种对立形成了张爱玲小说艺术中的荒凉美感。我们讨论张爱玲与视觉艺术的关系,挖掘其小说中的视觉艺术特质,会发现她的作品中有着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子。张爱玲的创作植根于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无论是选材、叙事、取景和人物刻画,都弥漫着挥之不去的传统文明气息。但是电影、现代绘画等西方现代艺术元素的加入,使得张氏小说摆脱了传统小说的平面化模式,向立体化和影像化的“纸上电影”发展。从这个层面上,可以说视觉艺术之于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意义,是一种现代性的尝试,使得现代艺术精神与传统小说艺术共通融合,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王志亮.皮尔斯符号学与视觉艺术[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1(3):108-114.
[2]李欧梵.上海摩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4]符立中.张爱玲的文学世界[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5]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6]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7]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
[8]李稚田.影视语言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9]张爱玲.怨女[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10]李欧梵.苍凉与世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陈丽羽(1992—),女,汉族,湖南长沙,文学硕士,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