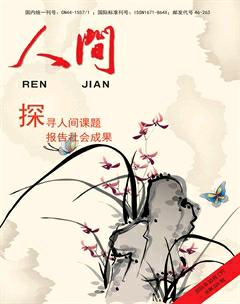浅谈勒克莱齐奥对底层女性出路的探索
摘要:底层女性生活是勒克莱齐奥小说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文化景观,反映着作家对受压迫、受欺凌的下层妇女的深切同情与理解。本文以《金鱼》中的莱拉、《流浪的星星》中的艾斯苔尔和奈玛、《乌拉尼亚》中的莉莉为主要探讨对象,并结合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思想来分析作家对底层女性出路的探索。
关键词:底层女性;生存处境;出路探索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 009 -02
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大多站在世界立场,并用独特的眼光来观察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尤其是被损害的边缘人物,以此来追求现代主题,《金鱼》、《流浪的星星》、《乌拉尼亚》也是如此。下文以《金鱼》中的莱拉、《流浪的星星》中的艾斯苔尔和奈玛、《乌拉尼亚》中的莉莉为主要分析对象,结合这四位女性的生存处境讨论小说中当代文明对边缘女性的影响及边缘女性的出路问题,并对作者的女性观进行整合,从而丰富勒克莱齐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一、底层女性的生存处境
勒克莱齐奥作品中的底层女性各人履历固然有差别,但却有着相似的辛酸遭遇。她们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身处战争与部落冲突之中,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境贫寒,又被迫远离故乡,一方面,她们时时刻刻面临着饥饿、奸淫、死亡的威胁,身体饱受折磨。另一方面,她们被迫离乡,没有名字,没有身份,处于不受关注的边缘地位。总的来说,底层女性的悲惨处境主要体现在身体的损害和心灵的创伤这两个方面。
首先是遭受欺凌与虐待。这与挨打、饥饿、奸淫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莱拉、艾斯苔尔和奈玛、莉莉这些下层女性身上尤为明显。莱拉从被拐卖起就饱受生活的折磨。经常头痛、左耳粉碎性骨折的她在左娅家里不是被女主人毒打,就是被男主人阿培尔性侵。在他们眼里,莱拉不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只是一件可以肆意玩弄的物品。冷峻的现实让她觉得只有坟墓才是自己的栖息地,“墓地非常幽静,没有了城市里的喧嚣和烦乱。我在这里呆着感到安全,好像这里是我早已是我熟知的领地了。”然而就是在这个她认为安全的地方,还是被流浪的老爷爷强奸。以莉莉为代表的红灯区女孩更是受尽所谓的文明人的侮辱,作者痛心地写道:“我想请求她的饶恕,饶恕男人们对她所做过的一切,饶恕那些侮辱,那些耻笑;饶恕他们把她从故乡劫走,交给一帮刽子手;饶恕他们的乱伦、奸污与亵渎;饶恕他们把她的身体当作出卖的对象;也饶恕他们把她的身体作为研究对象,成全了学生、研究者,包括人类学家也叫食人者的下流的目光。”
文中对于饥饿的描写是触目惊心的。在难民营上面的大山上,艾斯苔尔和孩子们不断得叫着:“面粉!面粉!牛奶!牛奶!”,张望着等待装有联合国救济食物的卡车。后来,狗饿死了,人也饿死了许多。在镜子里,艾斯苔尔看见了自己的脸,“这已经不再是一张十六岁少女的脸,不再有那份小伙子迫不及待想要看个究竟的美丽,这已是一个老妇人的脸,皱纹纵横,衰败暗淡,写满了不幸,一张接近死亡干瘪的脸。”莱拉也经常挨饥受饿,为了填饱肚子不得去偷去抢,饿得眼冒金星站立不住是常有的事,偷东西吃被抓住让人家用鞭子抽打的时候也不忘往嘴里塞东西。饥饿和打骂织成的大网将莱拉紧紧包裹,日子过得竟连女主人家里的一只宠物也不如。莉莉更是为了让年迈奶奶和自己的肚子而去出卖自己的肉体。
其次是精神伤害,心灵的创伤与身体所受的损害是紧密相联的。部落冲突和国家战争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让人贫困、饥饿、流落他方,伴随而来的是孤独、恐惧、失根、失语和混乱的价值观念。莱拉说“最令我恐惧的是孤独。朦胧中,我被拐时的情景不时地浮现在脑海,仿佛又回到了那明亮刺眼的大街,又听到了那黑色大鸟的尖叫,或者又听到汽车撞我的刹那间头骨碎裂的声音。”这是莱拉的孤独,亦是作者内心孤独的写照。冰冷世界带给莱拉的除了孤独还有恐惧,“记得有时候子夜醒来,惊恐之情就像一条冰凉的蛇袭来,吓得我不敢喘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畏惧大街,甚至不敢到院子里去,连大门也不敢跨出一步。”
现代文明把她们抛向世界的角落不受关注,从而使得她们处于失语状态。作者对莱拉、艾斯苔尔、奈玛进行了很多丰富的心理描巧,她们用女孩的视角来解读这个她们懵懂的世界。当莱拉叫喊着要离开的吋候,她根本“不知去往何处,也不知什么时候再能够回来。”可是除了离开她别无选择,正如西蒙娜对她说的:“莱拉,你和我一样,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的身体也都不属于我们自己。”艾斯苔尔犹太人的身份给了她不一样的生命体验,小说中这样描述了她认识到自己身份后的心理:“这是第一次,她明白过来她己经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的爸爸再也不能叫她艾斯苔尔了,也不会有人叫她艾莲娜了。”这是艾斯苔尔对自己身份的第一次困惑,孩童的体验浅显而深刻,她不知道一切为什么会这样,但她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她们在喧嚣的世界中被迫游走,也为了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中生存下来学会了种种处世之道,随之而来的则是混乱的价值观。这在莱拉和莉莉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奶奶拉拉阿玛摔倒快要死了,莱拉回答得异常冷静,为了不挨打撒谎隐瞒奶奶的病情使其错过医治时间死亡;她能明辨商品真假,所以在朱佩塔、法蒂玛这些女性和商贩之间两面收利;她以偷东西为乐,把在男人间卖俏挑拨视为游戏。莉莉永远保持着她的微笑,说话奶声奶气,对自己的顾客毕恭毕敬,任凭男人凌辱她的身体,并且将这视为正常的事情,不知反抗。这些女孩子永远走在流浪的路上,没有归属感,没有自己的根,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这是现代文明给她们的又一心灵伤痛。莱拉说:“我不知道我真正的名字,此时我已经习惯了女主人给我取的‘左娅,就像母亲给我取的一样。”除此之外,战争带来的伤口会伴随着人们一生一世,会瓦解掉一个人的情感,让人有如行尸走肉一般,“艾斯苔尔那时没有哭。也许那时在她的身体里已经没有眼泪了,是战争造成的。”可见,尽管战争已经过去,但战争留下的心灵伤口却是永久的。
二、小说对底层女性的出路探究
社会学认为边缘人物有以下几个社会属性:第一,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没有能力来改善近况;第二,对社会的影响极其微小,基本上没有话语权利;第三,边缘人群体具有传承性,没有丝毫的生存安全感。“边缘人”不仅是对这一身份的称呼,同时也是对这些人的生活状态、情感愿望、心灵心理的形象刻画。作者对这一阶层尤其是边缘女性充满了同情,并积极探索这些女性的出路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主人公们对自我的寻找上。达卡迪和朱丽娅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命运,便把希望寄托在莱拉身上,她们让莱拉上学,希望她将来能做医生或者博士,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这种教育对莱拉的追寻留下了深刻影响。她面试时诚恳地对面试官说到:“我是个孤儿,没有钱,又聋了一只耳朵。我什么都愿意学,以便能够旅行,能够成才。我愿意以做卫生或写信封的劳动来支付学费,也可以到图书馆去整理书,总之,为了能学习,我什么都可以做。”莱拉坚信,只有不停地学习和离开束缚自己的地方才能寻找到自我。通过努力,她最终如愿以偿,成了一名歌手,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当作职业。艾斯若尔和萘玛因为战争而远走他乡,这为她们寻找自我带来了悲凉意味。她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度过的,并在宗教的感召下学会了坚强和等待。在旅途中,她们逐渐认识到:“没有我们的位置,哪里也没有。”因此,她们一直都在寻找自我的道路上。面对残酷的世界,莉莉仍然保持着自我,“他们每一次都会从她身上夺走一些生命和芳华,而她始终保持着温和的目光和温柔的嗓音。她的微笑,她那女人的身材和孩子的脸蛋,仍旧保持着她来自土地的芳香。”除此之外,这些边缘女性也倾向于从自然中寻找最初的美好,艾斯苔尔在流浪途中对故乡溪水丛林的回忆就是明证,莱拉热爱旅游也有从自然中寻找自我的意味。
勒克莱齐奥对女性的地位十分关注,这与他对女性的依恋和同情相关。作者自己曾说道,“这和我个人的经历有关,因为我出生在战争朋间。男人在我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不是去前线就是当了逃犯。当时我只是一个孩子,跟外祖母和母亲一起生活,每一天真正面对日常生活的人是女人,所以在一个经历巨大困难的国家里面,真正的主人是女人。”作者对边缘女性的写作立场是明确的,他关注的是历史与战争给这些不同时代的女性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及由此勾起的永久记忆,并通过人物历程给边缘女性指出出路。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他用客观的笔触传递真实的边缘女性生活状态,从而扩展到对整个人类生存命运的思考。从这个角度上审视作者以及作品,我们可以得出:他对所有人类的生命关怀超过了对性别的选择,他所希望得到的是所有人对这个世界以及人类未来的思考。正如作者在一篇题为《大地上的陌生》的论文中讲道:“我要为一种新的生活而写作。”这种新的生活便是保持一种人与自然、环境以及自身之间的所达到的平衡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不只是女性和孩子,所有人类的生命的欢乐都不会被疲于奔命的追逐和占有欲所扼杀掉。这个时候,人们就可以回到家乡,踏踏实实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边缘女性真正的快乐和自由。
参考文献:
[1]袁筱一.勒克莱齐奥在沪印象记文汇报[N].2001年8月26日
[2]勒克莱齐奥著.袁筱一译.流浪的星星[M].人民文学出版社
[3]勒克莱齐奥著.郭玉梅译.金鱼[M].百花文艺出社
[4]陈路.行者勒克莱齐奥[J].译林:2009(1),36-39,29-33
[5]勒克莱齐奥著.紫嫣译.乌拉尼亚[M].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刘妍妮(1992.11-),汉族,甘肃平凉,硕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