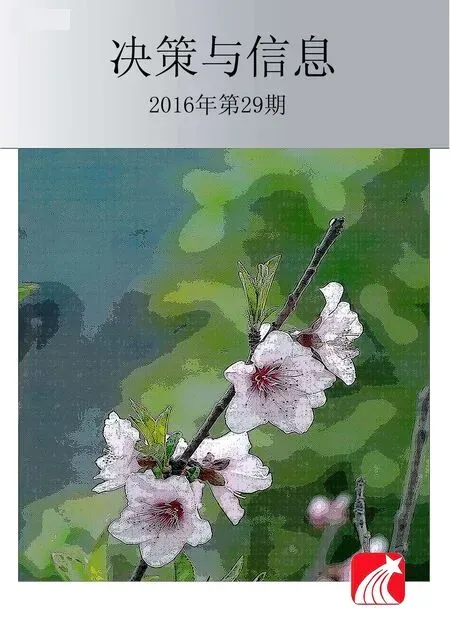村落空间形态与公共文化生活变迁调查
——以福田村为例
高敬恩 何玉梅 程 皓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0
村落空间形态与公共文化生活变迁调查
——以福田村为例
高敬恩 何玉梅 程 皓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0
村落空间形态是一个村落在精神文化、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具体体现,而公共文化生活则是以空间形态为依托所形成的公共性、共享性的文化活动。公共文化生活以实体的空间形态为依托,当空间形态发生改变时文化生活也必然发生变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福田村在经历了工业区聚集、村组合并、汶川大地震、机场高铁占地后传统的村落形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公共文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动。以该村落作为个案进行研究有利于了解和记录转型时期下传统村落的变迁与发展过程,并为村落转型背景下的社区治理提供经验资料。
空间形态;公共文化;转型;城镇化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赖以生存的古老村落正发生着急剧的变迁,正如孟德拉斯所说:“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9亿多农民、近70万个村落的农业大国来说这个问题便显得尤为突出。近年来,许多村落在经济上已由传统的农业生产发展为以工业为主农耕为辅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聚落形态上已由散居院落转变为聚居楼房,在文化生活上古老的乡村文化不断地被融入城市世俗文化元素。文中笔者所调查的福田村便是一个具有这样典型变迁特征的村落,本文旨在以空间形态和公共文化生活的视角为切入点对该村落的变迁过程及其现状进行剖析。
一、概念厘清——村落空间形态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
国内外学者关于空间形态的观点有很多,日本建筑学家原广司认为空间形态是一种生活体验,能够让人感悟到空间形成的原因,“人类存在方式本身就具有空间性,表示特定场所就成了谈及一个空间的思路”。美国文化考古学家戈登· 魏利认为聚落空间形态的形成在于居民与该聚落环境之间的互动,并在《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一书中做出了如下定义:“人类将自己所居住的地面上处理起来的方式,它包括房屋的安排方式,其它与生活有关建筑物的性质与处理方式。这些聚落要反映自然环境,建造者所适用的技术水平以及文化所保持的各种社会交接与控制的制度”。我国人文地理学家金其铭定义的村落形态是人们对其所居住的地点加以整理的方式。从外观上看,村落形态表现为村落平面的形式以及村落在空间高度上的形态,可充分反应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村落之中人的意识和精神追求。邓春凤等认为,“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作为时代生活方式在物质空间上的投影,是其社会经济、意识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等在地域空间上的折射,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承载着地域性的传统公共文化”。
综合这些观点我们可以认为空间形态应当具备以下几个要素:第一,聚落空间形态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有形实体环境,是公共空间的物质化表现,如房屋建筑格局、街道空间分布等,它们是可以通过某些尺度被衡量的,也是人与环境互动和精神文化的载体;第二,聚落空间形态是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被感知的,没有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就不存在聚落空间形态;第三,空间形态可以体现特定时期下的意识形态、民风民俗与社会经济情况等等。
在已有公共文化生活研究中,吴理财等认为公共文化生活呈现着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现象,有丰富和衰微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主要是把农民个体(或农民家庭)的文化生活与群体性的公共文化生活混淆在一起造成的。从资源上界定,“公共文化生活是指超出家庭以上的单位(如村庄、社区、政府或民间组织)组织的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活动,如庙会、歌舞会、民俗表演等活动”。而赵艳梅等认为“村落公共文化生活是在传统社会下,一种以农村村民群体为活动对象,以农民世代聚居的自然村落为活动地域的文化艺术娱乐活动”。张金平则把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分为两部分: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场地、设施等资源)、公共文化活动和公共文化组织。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公共文化生活”并没有一个清晰和通用的概念。在本文中笔者所认为的村落公共文化生活就是发生于实体空间形态中的文化生活,它至少具有两个基本特
征,即公共性和共享性。具体地说就是无论是这项文化生活的参与者还是文化生活本身所占用的空间、资源都超越了个人和其整个家族,同时公共文化生活还是面向某个特定地域的人们所敞开的,只要符合某种预设条件,则这个地域的所有居民均可以自由选择参与亦或是退出某种公共文化生活。
就其存在形式而言,乡村公共文化生活既包括自发形成的文化习俗,如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红白喜事、少数民族地区的祭祀仪式、江浙地区的乡村社戏等等。也包括由政府、社会组织或个人所主导的带有宣传意识形态功能和公共服务性质的文化活动,如民国时期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活动、近些年的“法治电影进乡村”活动等等。就其现实作用而言乡村公共文化生活不仅对乡村社会的个体意识、群体意识和整个乡土社会起着“塑造人格、实现社会化”、“规范和行为整合”以及“社会整合与社会导向”的作用,而且居民也通过参与公共文化生活表达了自己的某种文化诉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自身精神世界。
二、福田村空间形态与文化生活的历史与现状
笔者所调查的福田村位于成都市大邑县王泗镇,距成都市区约65公里,全村土地总面积2035亩,共有3118户,合计9547人,村内依次以左、黄、王、雷为大姓,其现所辖地域为原福田、妙庄、联丰三个小村落在2005年所合并组成。合并前的福田村在经济上以纯农业生产为主,发展结构单一,90年代中期人均年收入仅1400余元;空间形态上以传统林盘院落为主,有着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特征。 但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大邑县西区工业园的建设,福田村与不少周边村落的土地被大量征用,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福田村也逐渐由一个传统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落变为了一个以食品酒类生产为主的工业化村落。“5.12”汶川大地震后福田村作为大邑县地震受灾居民安置点,修建了供受灾居民集中居住区福田小区。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成温邛高铁的兴建和桑园机场的土地征用,福田村的第一产业用地面积和散居村民数量进一步减少、空间形态上的聚落集中化趋势越发明显。目前福田村已建成4个居民集中居住小区(福田小区、联丰小区、五福小区、碧云天小区)并且依然保留有部分未搬迁的散居林盘院落。

表一 1995年福田、妙庄、联丰三个村庄人口与面积表

表二 2015年集中居住福田小区人口分布情况表
在福田村这样一个变迁着的村落社区中,公共空间形态的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以下是作者通过实地调研与访谈所了解到的具有代表性的空间形态:
(一)院坝空地
院坝是福田村最为基本,也是最具延续性的空间形态,无论是散居形态下的院落林盘、还是聚居形态下的林荫空地都承载着福田村居民最基本的信息交流、心里认同功能和休闲娱乐的功能。集中居住后的福田村在建筑格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已经接近于城市单元房院落社区,加之拆迁征地和地震安置打破了居民在原住村落中的村组秩序,邻里之间大部分彼此并不熟悉,因此小区内居民的交往方式已经由过去彼此相生相望的“熟人社会”转变为现在类似于城市小区居民之间各自独立的“陌生人社会”。这种情况下,楼间林荫空地、石凳石椅等等便成为了彼此不熟悉的居民之间增进感情、互相了解变为“熟人”的一个重要公共空间,居民们或是在其中“摆龙门阵”(聊天闲谈)、或是四人围坐摸几把麻将亦或是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打“斗地主”,在这个过程中原本不熟悉的迁入居民彼此得到了熟知,信息得到了传播,消遣也有了一种简单而又没有额外成本的便捷渠道。
在我们这次研究中,研究结果进一步的表明,小儿呼吸道传染病大多数情况下是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水痘,结果显示,冬季和春季是急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最常见的季节,其中高峰期是4-6月份,婴幼儿是患有麻疹情况最多的年龄段,4-6岁的幼儿患有水痘情况最多,通常都是学龄前儿童。7-12岁的儿童最主要患有流行性腮腺炎,大多数都发生在学龄期。在感染性疾病高发的季节,要着重针对这样的三种疾病展开有针对性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实施有效的预防措施,接种相应的疫苗,医务工作者也需接种部分疫苗,例如,进行麻疹等预防接种工作,这样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有效降低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生率。
(二)沿街商铺
在福田村整体建设规划中,王泗镇政府修建了一条穿越福田村中心的主干道,并在其周边兴建了58间面积大小各异的沿街商铺,租金从每月800元到1200元不等,商铺的租赁者全部为福田村的常驻居民,他们有的开起了理发店、有的开起了麻将馆、有的则开起了小超市,夏季夜晚时长还会摆起夜市场面十分热闹,而在集中居住前福田、妙庄、联丰三个小村庄每个村庄只有一到两个小杂货铺。福田村的商业街不但为居民提供了生活的便利、为经营者解决了生活来源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为居民提供了一种附属于商业空间的公共空间,居民在茶余饭后围坐在小商铺周围买一碗冰粉,在家泡上一杯淡茶“龙门阵”一摆一晚上,如此日复一日的过程中加深了彼此的感情,居民也逐渐熟悉了起来。同时这些小商铺也是笔者田野调查的重要观察点,笔者每日晚饭后都会固定去一家小超市购买饮用水和一家冰粉炸货铺子吃夜宵,一来二去和店主熟悉了起来,关系也从一开始的单纯“买家与卖家”转变为了一种接近于朋友的关系,收获了许多后续研究的重要资料。
(三)村委会
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机构,承担了村落自治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搭建了居民与基层乡镇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居民们在生产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均需要在村委会的公共服务中心解决办理。在福田村合并前,秒庄、联丰、福田三个小村落的村委会办公地点面积狭小,条件十分简陋,只承担着最基本的办公场所职能。合并后的福田村村委会坐落于福田小区中心位置,村委会办公室前还建有一块400平方米左右的小广场,广场一侧设有亭台回廊,虽然地块面积不大但由于小广场位于小区内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带,加之可以与村委会共用电源、公共卫生间等基础设施所以这片空地便成为了周边居民业余时间聚集娱乐的地点之一。笔者在福田村近两个月的调查中发现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每晚7点至8点都会有周边居民聚集于此跳广场舞。
(四)“四组织一平台”办公楼及周边空地
福田村作为大邑县四组织一平台(基层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经济组织,高效服务平台)的社会治理创新试点在福田小区东入口处修建了一幢2层建筑,目前细部精装已接近尾声,预计2017年初正式投入使用,届时福田村村委会、福田村公共服务平台以及若干社会组织将入驻办公。办公楼附近有一片面积1000平方米有余的空地,这片空地是福田村居民举办红白喜事的“默认”地点,笔者在福田村调研的2个月中该地总共举办大小规模不等的红白喜事6次。办公楼及周边空地既承载了传统的习俗性文化活动又融合了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这种整合型的空间形态也必然会使得福田村居民的公共文化生活越发多样化。
(五)物业公司前的空地
出租赁服务,据笔者了解每年大约有两到三次商业性推广演出活动租用此地,每场演出物业公司收取800元场租费并提供必要的水电服务,虽然演出性质本身是一种产品推广活动,但在客观上为丰富了福田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六)福田小区篮球场
福田小区内建有一座水泥地面篮球场,这座篮球场是福田村青少年们最为频繁光顾的地点之一,即便在炎炎夏日球场也难得空闲,年轻人课余、业余时间聚集于此打球聊天,增进了彼此的了解程度,完全不相识的几个人打两场球便成了球场上要好的朋友,在福田村篮球场也不仅仅是人们锻炼身体的运动场所,而成为了年轻人互相熟识,沟通信息的重要空间形态。
在此,我们可以按照类别、功能以及存续状况对福田村的公共空间形态进行归纳:

表三 福田村空间形态特征表
三,福田村村落空间与公共文化生活的变迁特征
如上所述,自90年代初至今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福田村的空间形态与居民的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
第一,居民在村落空间中的活动内容日益丰富。
在上世纪90年代前福田村居民在村落空间中的活动主要以最基本的商品交易、闲谈家常为主,一方面这是受搬迁前较为落后的基础设施所限,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福田村以农业耕作为主的生产方式有关。而在90年代后随着工业园区的引进空间形态也开始变得丰富起来,居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逐渐变得多样化,这时一部分村民从土地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开始了一种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2005年至今,随着集中居的推进福田村居民们的生活方式上更加接近城市居民,空间形态更加接近城市小区院落。
当前福田村居民可以参与一些传统的公共文化生活:如在树荫下、楼道口、健身器械下摆起“龙门阵”,闲谈家常;当然,居民也可以在村落空间中举办红白喜事,因为红白喜事自古以来都是村落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这些传统的文化生活之外,居民还可以在一些新型的村落空间中从事一些较为现代化的活动。比如,在新修建的办公楼空地前福田村居民们不仅可以散步闲谈也可以聚在一起跳起广场舞和放映公益电影。可见,在村落变迁的过程中,居民在村落空间中从事的活动也日渐多元化、复杂化。
第二,村落空间由封闭走向开放。
集中居住前的福田村,村民的生产、生活以村组为单位,与外界的接触比较少,村民之间的公共文化活动,人际交往互动也大都发生于村落内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需求福田村改散居为聚集、改村落为社区,这在客观上打破了村落空间的封闭性,加之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大邑县乡村公共交通的不断完善,福田村居民与其他村落及城市之间的互动频率、互动范围不断加大。可以说,市场化力量进入福田村,不仅使得福田村居民的生活半径不再只限于村庄内部,而是进一步扩展到更大的区域范围中。
居民们活动半径不断变大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村庄空间形态不断变迁、经济实体不断多元化的过程,村落空间的向外延伸则赋予了村落空间自身更多的灵活性、流动性,也正是这些流动的、向外延伸的村落空间形态成为了沟通福田村由传统走向现代化变迁的桥梁。
第三,村落空间更加“公私分明”。
集中居住前的福田村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千千万万个村落一样,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甚至可以说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然而,在集中居住后,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延伸,村民们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私人空间逐渐产生。由于福田村的集中居打乱了原有的村组序列,所以居住在单元楼房里的福田村居民们彼此并不熟识,居民们很难再向之前那样随意“串门”,此外,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电子科技产品的不断廉价,福田村居民家庭中的家用电器也日渐先进,“龙门阵”和搓麻将也不再是村民闲暇时的唯一选择。因此,村民们不再随意进入别人的私人空间,同时他们每个人也拥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且不希望他人随意进入。“公私分明”逐渐取代“公私不分”,村落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交互性也随着村民生活习惯、思想意识的改革而渐渐地消失。
四,小结
空间形态的多元化与村落空间的日渐开放使村落进一步适应了城镇化、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需要,并满足了村民自主意识的发展。早在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就指出,“城镇化要以人为本,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推进城镇化,既要优化宏观布局,也要搞好城市微观空间治理”。面对乡土文化的割舍不断、现代城市文化的强大吸引、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有力引导,福田社区居民和中国亿万城镇化过程中的居民一样,流露着复杂的情感。如何使公共文化空间既便捷居民物质生活、又丰富居民精神文化,既能最大限度保留他们头脑中的乡土文化记忆、又能让其深刻感受到现代城镇生活的多姿多彩,既能保存淳朴民风、又能有更开阔的眼界,便成为了摆在政府和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1](法)H.孟德拉斯(HenriMendras)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日)原广司著,于天祎等译.世界聚落的教示100[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3]G. R. Willey.Prehistory Settlement pattern in the Viru Valley, Peru. Bulletin,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Smith sonian Institution . 1953
[4]邓春凤,冯兵,龚克,刘声伟.桂北城镇聚落空间形态及景观格局浅析[J].城市问题,2007(9).
[5]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重建 ——以安徽省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7(2).
[6]赵艳梅,夏彩云.农村社会公共文化生活的衰落与重建研究[J].农村经济.2012(11).
[7]张金平.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变迁研究一一以L村篮球场为个案[D].华中师范大学2012
[8]郁大海.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变迁与重建[J].中国农村观察,2010.(14).
[9]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文件.2013.
高敬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生;何玉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生;程皓,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