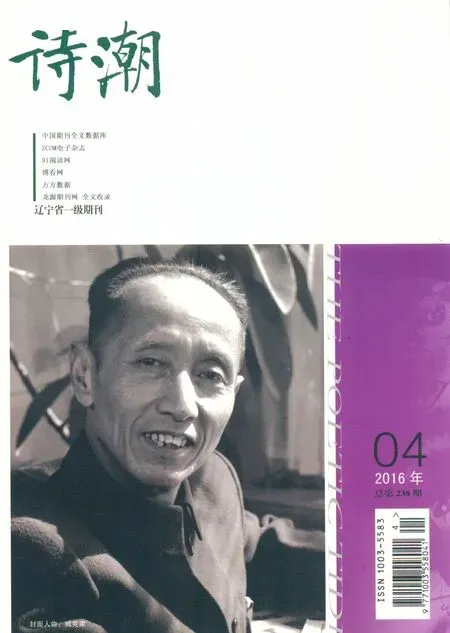欧阳昱近作
■ 欧阳昱
欧阳昱近作
■欧阳昱

欧阳昱,墨尔本La Trobe大学澳洲文学博士,澳大利亚作协会员。曾任武汉大学英文系讲座教授,现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思源”学者兼讲座教授。截至2016年1月,已出版中英文著译78种(含译著41部、英文诗集14本和中文诗集9本)。英文诗集《异物》获悉尼2003年快书诗歌奖。中文诗歌两度入选中国最佳诗歌选。英文诗歌连续9次入选澳大利亚最佳诗歌选。英文长篇处女作《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获2004年阿德雷得文学节文学创新奖,出版之后被列为悉尼大学英文系教材。第二部英文长篇小说《The English Class》2010年8月在墨尔本出版,于2011年获得新南威尔士总督奖。2014年,译著《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出版并获得2014年澳中理事会翻译奖。2011年,欧阳昱被评为2011年度百名顶级墨尔本人,并被纽约的中文杂志《明镜》月刊评选为十大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作家之一。
戚戚
那年,不是73,就是74年
我们养的那头猪
趁我们不在
冲进厨房
把中午做好
下午放工回来吃的饭
都吃了
我回来发现后气极
关起大门来
用扁担打猪
打得它嗷嗷乱叫
满屋乱跑
隔壁的大娘
隔着门缝
对我说:
欧阳,欧阳,别打了
猪又不懂事
后来,我把此事
写进诗里
那也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皆因自己
感到guilty
近读古文发现
有一位名叫
仇季知的人
自叙说:
吾尝饭牛,牛不食
鞭牛一下,至今
戚戚矣①
Oh, my God
这古今一仇一欧阳
一猪一牛
虽受鞭子扁担之苦
到底已经如诗
而不必
戚戚矣
注:参见明·冯梦龙《仇管省过》,原载《古今谭概》。
飘逸
一个作家,作家写道,必须时刻想到自己明天就要去世。那么,此时你要写什么,就不会只是为了下一碗饭,而是为了把临死前要讲的话说出来。不,明天去世还太晚,必须今晚就在睡眠中去世,那么,要写什么不是没有任何意义了吗?是的,没有。那么,你想说什么?你想说:我爱,我喜欢被爱的感觉。你想说:我一生没有跟任何人结成任何利益为中心的同盟。你还想说:我无法接受那些靠文学牟取暴利、牟取暴名的人。我在心中永远不承认他们。我连他们的姓名都不愿提到。除此而外,作家对自己说:让我今晚在睡梦中飘逸而去吧。
李子
两只黑色的李子
深黑色的李子
在我手上凹陷下去
一天天凹陷下去
黑色而无香的李子
是一月盛夏某个草影深浓的上午或下午
我到Link Street拿邮件回来时
在街角一家邻人果实累累
无人问津的李子树枝上
掐摘而来
每年这个时候
我们这条街的李子树
就会颜色转成古铜
成熟的果实
没有人吃
连看的眼睛都没有
就是写
也没有诗意
我让它们在电脑前一天天萎缩下去
灯光下的两颗黑枣
凑近鼻子闻起来
终于有一股淡淡的气味
不香
稍稍带有腐气
仿佛一个青春四溅的少女
牙缝中的气息
灯
远处有一盏灯灭了
我感觉,像是一个友人
近处,一盏灯也灭了
被一只吝啬的手
最近不断有灯
明明灭灭
也有自己掐灭的
也有别人吹熄的
还有一片灯火
在黎明的某个时辰集体熄灭
还有,当乌云聚拢之时
天灯,有时也会无光,甚至失踪数日
所有点亮的灯
届时都会熄灭的
是否能够续燃
那是更年轻灯们的事
但左近的灯,再度消隐
还会亮起的,因为那是街灯
Narcissus
Narcissus,这个希腊神话中的神
人见人爱,人爱都不爱
只爱自己
只爱自己本人
在水中的形象
直到把自己
爱死
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人
叫涓石梁
但他不爱自己
不爱自己本人的影子
“见己之影
以为鬼也
惊而死”①
这一怕一爱,恰似镜子
互相映照着古今
注:转引自明·冯梦龙《畏痴》,原载《古今谭概》。
活
一个人死了很久
我还能在吃晚饭的时候
蓦然、偶然想起他来
他没死
我是他活着记忆的
延续
我若死
那些碰巧记起我的人
也是我未死记忆的延续
励志
把自己放松、摆平
忘掉一切可以忘掉的人
忘不掉的人也不用去记
进入心灵深处
为自己洗脑
听没有听过的声音
走到河流尽头、道路尽头
从大脑的悬崖一跃
进入扑火的永恒
阳光
阳光太强烈
我把窗帘拉上
坐在电脑前修改译稿
阳光突然灭掉
室内黑暗一片
我突然什么都看不见
阳光转而回升
仿佛有人灭灯
又逐渐拧亮开关
阳光停在一半的地方
原稿字迹依稀可辨
我诗意陡生,停键另开文档打字
阳光再灭又再起
我懒开窗帘
任阳光在外嬉戏
看来
看来
希望又要落空
你和她缓缓地在8点后的暮色中散步,说
是的
你说,一本书出了如果不获奖
就等于白出
你们在一扇剥蚀的红门前停下
看两头瘦鸟在门头上走来走去
传来鸟爪在铁皮上走动的沙沙声
为什么从来没有成功的鸟
你说,一个人不成功
难道就等于白活?
那不就是我吗?
你说
你回望了她一眼,说:别瞎说了
这儿有很多人就像鸟
什么也不想,不想成功,只是生活
从生命的一端,飞向另一端
快活,但不快快地活
你说
只能这样了:这三本书就算是垫脚石了
后来,你们在家屋前停下
你把他们新漆的栅栏用手摸摸说:
真不错,一切又跟新的一样了
简单
又到了
虫叫声震耳
欲聋的时候
“为什么”
你说
“总在将入夜的时候”
简单的问题
总是最难回答
你回头,指了指黄蒙蒙的月亮
“是不是它们也在打?”
你又问,自己先笑了起来
你也笑了,因为
除了你和你
谁也不懂“打”
的意思
他
我在冲水倒茶的那一刻
终于看清了他
这张在夕阳下
忙碌的脸
看上去像铁托
现在转过去了
从稀疏的头发中看过去
能看到里面粉红色的肉
他周围的也不知是豆架子
还是瓜架子
长得比他高了
他的格子衬衣
他因栅栏
而永远也不会被我看到的
齐腰以下的任何部分
这是与我为邻14年
距离不到5米
从未讲过一句话
从未交流过目光
我估计来自欧洲
某个小国村庄
颇会侍弄菜园子
又在澳洲生活了几十年
完全不用与我交流
我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他姓名
估计直到他死
或我死之前
以及之后
双方都没有可能认识对方
也不想认识对方
的
一个人
蟋蟀
三月中旬近11点钟
墨尔本初秋的晚上
风很凉
蟋蟀不如黄昏时叫得响
但还在纱门外单独地叫
要是我生活在雪莱和济慈的时代
我也许会感到伤感
很可能坐下来把灯熄掉
静静地长久地听一会儿
体会在黑夜里陪伴一只蟋蟀的孤独的滋味
可我几乎连想都没想
就把纱门后面的玻璃门拉上
接着把玻璃门后面的门帘拉上
同时
脑子里冒出了
“要是我生活在雪莱和济慈的时代”
我又关上了一扇窗
熄掉了两盏灯
穿着短裤面对屏幕坐下
从那儿把这首诗
写完
居然依然不觉得伤感
看来,他们在浪漫的时代
早已把浪漫挥霍净尽
我这里
只能写一些
后孤独的余感
孩子
一个很生动的孩子
牵着我的手
走下云雾缭绕的大街
那时
世界仿佛回到了童年
孩子嫩嫩的指尖
绽放出新鲜的叶子
他把一切不该做的
都做了
我的劝阻
就像年久失修的
耳旁风
孩子的唇吻
是哈哈笑着
给予的
小手的温暖
可抵一颗太阳
在一个类似大写L的
尽头的地方
我们没有停下来
而是从梦中
惊醒
广告
做广告的女人
无论多么漂亮
也难逃被恶搞的噩运
比如我从车窗外
此时看到的对面橱窗
那个昂首大笑
满口白牙的女人
就被不知谁在她的唇上
画了一道浓黑的翘翘胡子
美人啊美人
当作广告展出
你可要多加小心!
法官
这话刚刚说完
就见法官
动容
乃至大痛
最后涕泪交流
证人身边的大律师
早已泣不成声
我看着法官涨红的脸
和沉重得似乎抬不起的头
好像也听见喉咙里发出
某种难受的声音
同时向右边看去
发现那个我以为绝对不会动情的人
也潸潸然颇有泪意
很快
全场唏嘘一片
但直至这场梦做完
这首诗写完
我也回忆不起
到底证人说了什么
导致男女集体
浇泪
野花就是这样长起来的
没有名
从来没人注意
不像花园里有园丁
辛勤侍弄
没有一大堆美丽的姐妹
围绕、衬托
无人保护、频递秋波、暗中提携
也不会有人摘取、包装、贴上标签
起一个漂亮的名字
以高价出售
即使偶有采摘
也会迅速丢弃
从来不会提及
不会用来送礼
不会用来装点节庆
不会用来装饰葬礼
哪怕已呈花花燎原之势
也不会抓住眼睛镜头
就像一位名人惊呼:哎呀!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怎么长成了这个样子!
野花,就是这样长起来的
那时
那时
是半下午
后院草色青青
阳光精力充沛
我
站着抽烟
等一个没有立刻回电的电话
湛蓝无云的空中
一群白鸟
上下翻飞
嘎嘎的叫声响成一片
偶尔
它们倒转身来
让我短暂地看见红色的胸脯
很快,它们消失了
如同我的爱
此时
是傍晚6点20分
迁移
在最开始的游移和混乱之后
我们进了车厢
还好
虽然很小
但自成一体
有洗脸的地方
床上还有帐子
老婆、孩子
还有另外一个孩子
因为什么和我怄气
不肯理我
后来我说了几句好话之后
孩子就活跃起来
我这才发现
她的上嘴唇好厚
呈三角形向上隆起
我们当时都知道
我们要去的地方
非常贫穷落后
是所有人都不要去的
我们非去不可
倒还不一定是别人所逼
我默默地想:
人生到了这个时候
还要如此
也无所谓了
就随它去吧
未尝不是好事
醒来之后
觉得还有点意思
就写下来了
家
回家的路上
影子在我右边
太阳在我左脸
离家的路上
我不记得影子
和太阳的方向
活了这么多年
脚还在地上走
人,还是跟人一样小
十月初,春天终于来到
到处都是浪费的光,和热
以及等待凋萎的鲜花
滴
滴、滴、滴
雨溜的水
滴得很急
不停地滴
从一早起
如果有人问
滴这么急干吗
雨溜不管不顾
雨水继续滴
有什么可比嘛
没什么可比
想起一个形容词
娇滴滴
想起一句诗
粒粒皆辛苦
天上的所有剧情
就通过滴声演出
滴滴滴的乐器
不过是一只生锈的
雨溜
在清晨的金斯勃雷
滴
只能无题
2011年8月22日
上午11点20分
飞机即将降落墨尔本时
我看见由赭红色方块
浓绿色方块
浅灰色方块
和深褐色方块
交织的土地
以及
远方大片的雪野
正在机翼下缓缓掠过
它们那么贴近地面
就像云
弄月
弄月仙郎意不自得
独行山梁
采花嚼之
作《蝶恋花》词云……(词略)
童子刈刍
翕然投镰而笑曰
吾家蔷薇开矣
盍往观乎?
随之至其家
老妇方据盆浴鸡卵
婴儿裸背伏地观之
庭无杂花
止蔷薇一架
风吹花片堕阶上
鸡雏数枚争啄之
啾啾然
麻木
冠被砍了
枝被斩了
叶被削了
这段树怎能不麻:
麻木
亮
把眼擦亮
不是看钱
不是看人
而是看天
把心擦亮
不是梦想
不是妄想
而是想象
把脑擦亮
不是思家
不是思迁
而是思想
把手擦亮
不是握笔
不是敲键
而是指路
把人擦亮
不是出头
不是照相
而是拓荒
窗口所见
一条无水的河流
像一道抛出去的长绳
蜿蜒地雕刻在
红褐色的大地
几百平方公里
几千平方公里
几万平方公里
这条河流
就那么曲曲弯弯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