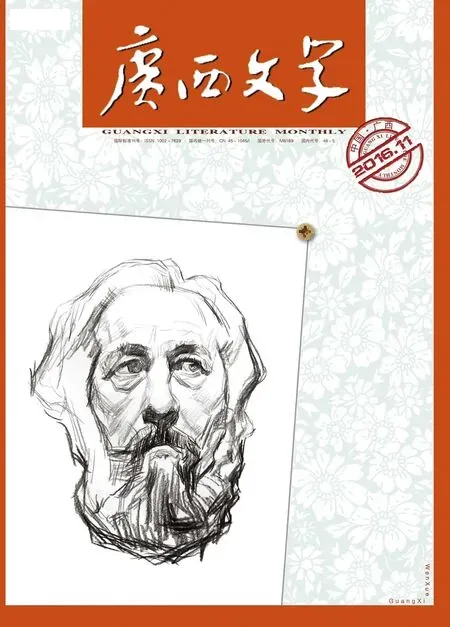高瞻的诗
横 山
横山像一位古居之智者,偏居桂东南一隅
攘持十万大山余脉之雄势
由陆川县城一路向东至大桥乡后突又斜横向南狂走
起伏近百里——横山由是得名
其始属大桥乡,终独自为乡为镇
而其子民日益壮大 又巍巍乎如绵密之丛林
初,横山不过一街一河一小学一初中一医院而已
以其偏于群峰洼地之西南角,而有“横山角”之名传
“有女不嫁横山角,吃无饱,衣地着”
而我母亲却从大邑贵县嫁来
生我之后,乡音俨然村人
步履快于时光
1980年分家后我八岁 开始独自煲饭煮菜
挑水挑谷插田骑单车上横山街游荡
1985年,我徒步蜿蜒乡间,挑书上学堂
“横过这座大山,就是博白县”
面对左边山之最高峰黄峰笼,心生敬畏
峰顶建有城堡像天安门模样
据说半山中有暗河。河怎么可能在山中流呢?
为什么不像眼前的龙河一样在地上走呢?
年少的我一直找不到这人生第一道难题
蓝天下有乌云自黄峰笼飘来,夏雨即将骤至
这样的常识,贯穿了在晒谷坪望山而收晒的
童年、少年,1988年及绝大多数村民的一生
泥泞且拥挤,一天两趟通往县城的班车周而复始
横山街就这样流走了我的小学时光
其间,十三岁的少年情窦初开,风怀其中
捕捉了一张天真无邪的笑脸
之后我缘北而上,一去百里千里
间别三年、五年、十年……又二十年
花开花落,五更梦醒,柳重烟稀
横山慢慢地变成了故乡
其间横山逐渐有了高楼瓷厂养猪场
水泥路也纵横四方
千家万户 变了模样
前年,还通了自来水
可惜半年后终是成了摆设
流水独自归于深井
版图中横山像一横排之筝柱
就之如日,望之如云
他是一位严父 看守着脚下万千子民
他带来风与水 雄壮血气摔打方刚
顺天之义 知民之急
当我出东山踏西山度南山及至登长城
未尝不慨然而叹也
这期间,横山仰之弥高
就像巨龙一样跃然而出
今夜,横山高大
今夜,大山至简
化成我面前的一张纸
纸上的一首诗
以至于我不知它是诗中的感伤
还是梦里的盛唐
龙 河
龙河,头枕着横山,有来龙有去脉
自旺坡佛子岭汇百泉而出
随物赋形而披六山通七泽决八溪
最终合于九洲江下广东进大海
其融冰化雪不知历经千年万年
其亲和百姓不知看尽多少人间
龙河,东至崩塘南过谢鲁河西浮子恩水
两岸良田千顷人民赖此为生
夏暑的龙河是孩童戏水纳凉的不二之选
寒冬牧童与鸭鹅不河之洲
冷风中吹来春草青涩的芬芳
当是时两岸晓烟连着阡陌映照竹翠柳绿
一犁春雨唤醒山村羞看桃青杏红
1980年 生产队的碾米水车犹在眼前
每逢天旱,村民都会引龙河水入田
其山洪为灾 时间指向1990年
依稀记得分田到户山上所有树木一夜砍光
山塘不蓄水打柴亦无望
之后山路愈发泥泞砂石路早不堪重车日夜来往
人们纷纷背井离乡到广东到香港
之后桥窄桥断之后又建起水泥路
之后水泥路又烂裂
而有人偷建砂场建起了洋房
有人圈种速生桉成了土豪日益张扬
有人贩卖地沟油发财而心慌
河山寂泣 而村民仍在挖井在起楼房
泥砖老宅弃而不顾 没地只能转移到山上
“以前六米就出水,现在要挖到三十米
还要用电来泵”隔壁三叔对此一脸迷惘
速生桉抽干了山的乳汁
水洼的水都成了黑色一汪
“好在不用养牛了,不然牛没水喝地仍是丢荒”
之前十年,龙河如妇女更年
水量日少曾经宽阔纵深的龙河
只剩沙洲日益扩张
鹅卵石暴晒在天空下 苍苔泛绿 满目沧桑
丙申年春,我埋葬了亲人后再到龙河边瞻望
河已为溪,它就像我山上地下的亲人
带走了一个时代的荣光
烈日中唐歌怆然响起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叙事性诗歌诗论】
用现代诗叙事,无疑是难以企及古诗筑就的高度,但我们仍然要锲而不舍地以诗人的热血之心,关注当下关照内心那些无法抚平的沧桑,哪怕只留下了凄惶的瞬间,也是一种悲壮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