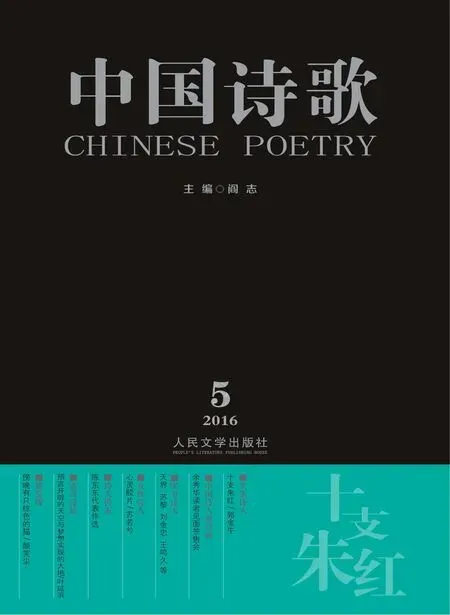诗学观点
阴孙凤玲/辑
诗学观点
阴孙凤玲/辑
●罗麟认为,诗歌经典是凝聚了人类的美好情感与智慧,能够引起不同时代读者的共鸣,艺术上具有独创性,内容上具有永恒性,能够穿越现实与历史的时空,经受得住历史涤荡的优秀诗歌文本。一方面,诗歌经典本身必须在内容、艺术上质量过硬,那些不严肃、不真实或是在艺术创造性上乏善可陈的诗歌作品,是不可能成为诗歌经典的。另一方面,诗歌经典必须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或者说具有某种历史性,比如新诗草创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品,放在今天或许在艺术性上并不出众,但由于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和条件下特有的开创性,而具有了无可取代的经典性。也就是说,没有相应的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的艺术沉淀,诗歌经典的生成是不可能的。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去考查,当下诗歌因为在时间沉淀的条件上无法满足要求,是不太可能产生诗歌经典的。在时间距离过近的环境下,所谓的“经典性”的生成往往是自封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21世纪:诗歌接受的“窘境”》,《文艺争鸣》2016年第1期)
荫王士强认为,个人化写作本身当然是值得肯定的,诗人作为独立的个人而不是作为群体、集体、理念的代言者,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才能够得到保障,这本应该是写作的基础与前提。……但是,个人化写作同时也是艰难的,绝不是没有边界和标准的随意乱写,它虽然高度尊重个体的独立性、个性,但这一切均需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之下进行,艺术本身便是在重重的不自由中寻求自由。就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写作而言,它一方面存在过度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不足的问题。个人化写作的“过度”主要体现在诗歌作品的过于自我、私密,从而割断了与广阔的生存世界的关联,仅仅成为了知识的中转、思想的演练、语言的炼金术、修辞的自我循环等等,从而导致个人化有余而公共性不足。
(《重审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个人化写作及其内在分歧——从罗振亚〈1990年代新潮诗研究〉谈起》,《当代文坛》2016年第1期)
荫蒋蓝认为一个人在文字上的亮相仪态,几乎就决定了其后来的言说方式,就像你无法改造自己的声带。采用转喻和口语的融合语态,为情绪加入冰块,对不断敞开的日常经验进行寓言化处理,一次写作就是一次回忆,往事在一种克制陈述的语态里复苏曾有的花香和枝蔓,那既是写作者的自画像,也是为生存完成的一次照亮。
(《圈内圈外的成都诗人》,《星火》2016年第1期)
荫周庆荣认为,对诗歌中的“分行”和不分行的散文诗,我从未把两者相隔离,我个人以为二者都是诗,是“大诗歌”。散文诗的叙述性和艺术的延展空间似乎更大,正因为更大,它需要写作者哪怕在手法的隐喻、模糊时,也要能把现象背后的本质性思考清楚,它不允许过分掩藏,而分行诗的魅力之一恰恰在于掩藏。我认为优秀的诗人,只要觉得叙述需要,在自由度、空间感或完整性需要进一步释放时,都会感受到思想性、叙述性和诗性真正结合后的美好,像昌耀后期的散文诗。现在有许多以分行诗写作为主,但散文诗也极其优秀的诗人,如:胡弦、徐俊国、雷霆、王西平、宋晓杰、金铃子等。
(《诗与远方——关于深度、理想、宏大叙述的诗歌对话》,《扬子江诗刊》2016年第1期)
荫刘向东认为,从根本性上来说诗歌无疑是想象和虚构的艺术,有一定鉴赏力的人,大体不难区分侧重于存在的具象的诗歌与侧重于虚构的想象的诗歌。我们的文学观里多年以来一直滋生着这样的一个念头,说是不能与现实靠得太近,太近了,其作品的文学性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受到质疑,因为我们很多文坛的老前辈是有教训的。我觉得根本问题不是离现实近不近的问题,也不完全是方法问题,说到底是襟怀和气度问题。
(《重温田间的〈抗战诗抄〉》,《诗选刊》2016年第1期)
荫田原认为“流畅性”是评价诗人的标准之一。这里所说的流畅性跟当下诗坛提倡的“阻拒性”并不矛盾,一首具有流畅感的诗中同样可以存在“阻拒性”。但如何在一首文字有限的诗歌作品中做到“流畅性”和“阻拒性”共存的平衡,我认为至关重要。对于内行读者,二者或许都很必要,但对于更多的一般读者,“流畅性”似乎更为重要。一首诗中,阻拒也许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很多的阻拒并非诗歌空间天然所致,而是作者的思维不通才华不够所致,甚至是做出来的,像脑血栓一样,这样的人为故障式的阻拒不是诗歌所需要的。即使是阻拒性的文本也应该是文字字面上的阻拒,而让读者感受到的那个生命也应是流畅的。
(《流畅与差异——吉狄马加其人其诗》,《时代文学》2016年第1期)
荫张曙光认为诗人必须研究技艺,使之娴熟精准。但诗人不应仅仅满足于技艺,更要发掘人类更为内在和隐秘的情感,以揭示时代本质的特征。现在写作的一个误区是,诗人认为写作的个人化就是单纯地表现个人的情感,而很少能够将个人情感上升到一个普遍的高度。同样,诗人们以语言为工具,但语言并不仅仅是工具,也代表着诗歌本身。因为诗歌中的技艺、情感或经验最终是以语言来呈现的。诗人不仅要善于使用语言,更要为语言的净化和丰富尽到力量。
(《著名诗人与优秀诗人》,《诗林》2016年第1期)
荫李以亮认为支撑和成就一个艺术家(包括作家、诗人)的,首要的是他身上整体的直觉,混沌却鲜明的倾向和意识,而非那些东拼西凑、乱七八糟的知识、概念、伪装、姿态、立场。而直觉背后,是独特的人格、热力、气质,是整个的人,是小宇宙,是他对世界与人的全部确信或无知。凡是能够解析的对象,都是贫瘠的和乏味的。艺术的想象,无疑具有轻灵、拔地而起的能力,这使它好像跟实在的现实没有关系。不对,想象虽然离开了那个具体、不能溶解于艺术的实体的现实,想象却必须关照、回顾、反哺那个现实。否则,想象不可能走多远,那样的想象也没有什么意义。
(《沉默与言说——2015年札记》,《诗歌月刊》2016年第1期)
荫牛学智认为,彻底的口语化用词、彻底的日常化句式,包括彻底的日常生活形式框架,都不是评价一首诗是不是坏诗的首要根据,标志一首诗是不是坏诗、非诗,甚至流水账、废话的,是诗人是否胸怀天下,是否真的用真切的生命体验观照外部世界。这时候,任何理由的时髦价值、任何圆熟的前卫技术,都必然首先为诗对世界、对社会现实、对无数个人的遭遇孤注一掷,去卖命、去咳血、去痛苦、去孤独、去寂寞。否则,读者便没有任何动力放下手机、放下鼠标,为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文字游戏去无聊地消耗时间。
(《宁夏“60后”作家的三副面孔》,《朔方》2016年第1期)
荫张晓琴认为,网络时期精英知识分子被进一步推挤,大众知识分子开始一统山河,“人的文学”已经演变为“身体写作”、“欲望写作”。就像福柯所说的那样,人被知识、欲望终结了,传统意义上的神性写作者彻底死了。也正是因为他的死亡,旧的写作伦理才被打破,新的写作伦理得以确立,而新的书写者也才产生。这便是大量网民的书写。从圣人移到精英知识分子,最后到大众,这显然是一种下降的趋势。作者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死亡方式,而其每一次的死亡,便是文学的新生。大众书写的网络时期,作者已死,无数的书写者诞生。书写者不再听命于神的召唤,也不再坚持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而是随心所欲地书写,是娱乐书写。
(《表象的恐慌与本质的自由:对新媒体时代文学境遇的另一种思考》,《创作与评论》2016年1月下半月刊)
●乔叶认为任何身份都会带来限制,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没有完美的身份。而写作的张力也恰恰来自于限制。至于历史观,我不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有一个历史观,那是政治学家或者历史学家的事。作家关心和体现的应该是人,历史中的人和历史中的人性。写作说到底是个人的事,也都是拿作品说话的事,读者不会因为你是70后就会格外厚待你,也不会因为你是90后就特别纵容你。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我觉得最根本的敌人永远是在自己内部,有个词叫祸起萧墙,我认为最根本的挑战就是“战起萧墙”,是自己对自己的挑战。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什么?清楚了这个,所有的冲击都不足为惧。
(《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文学的财富——对话乔叶》,《江南》2016年第1期)
荫欧阳昱认为,要“把你写进诗”就是把人写进诗,包括素不相识的路人,即凡是能让我产生诗意的人,尤其是平头百姓。诗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诗就是一个既要让诗人活、让大人物活,也要让名不见经传的人见经传,通过我诗而活下来。一个带着语言行走的人,所到之处、所到之国,都会自觉地把注意力转向该国的语言,并将其与自己的母语和父语(我个人的独创)进行对比,令其入诗。
(《把你写进诗:漫谈诗歌的全球写作》,《华文文学》2016年第1期)
荫艾伟认为,六十年代作家在中国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作家的童年记忆是十年“文革”,然后在他的少年、青年及中年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因此这一代作家身上有非常特殊的气质。年少时,因革命意识形态喂养,他们具有宏大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又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见证了“革命意识形态”破产后时代及人心的阵痛,见证了“信仰”崩溃后一个空前膨胀的物欲世界。这些经历让这一代作家建立了双向批判的目光。它既是“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者,也是“市场欲望”的批判者。
(《生于六十年代——中国六十年代作家的精神历程》,《花城》2016年第1期)
荫阿来认为,古代是一个诗歌时代,中国外国都是诗歌时代,外国包括描述他们宇宙观的《失乐园》那些都是,讲述历史的也是诗歌。文字越普及越发达,诗歌的受众肯定越强些。但是从消费主义开始,诗歌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满足,叙事文学有吸引更多读者的可能性。任何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大概到唐宋时期,叙事文学就开始发展,其实是因为城市的发展,消费的发展而导致的。中国叙事诗不强大大概是和汉语的功能有关系。西方诗歌,尤其是现代派意象派之后,西方诗歌也变得慢慢向中国诗歌学习,中国诗歌也向西方诗歌学习,所以变成全球的一体的诗歌状态,西方诗歌虽然有叙事传统它也停止叙事。
(《文学总是要面临一些问题——都江堰青年作家班上的演讲》,《美文》2016年第1期)
●关晶晶认为,艺术创作是体验、感受、自我探索的过程,艺术不是思想,它可以是思想性的,或是前思想的,但它必须以不同于思想的特征来呈现。任何关于精神的活动都可以是“思想性的”、“前思想的”,它只是描述了一种向度,但它不能区别不同的精神活动。艺术作品可以因创作者而带进一些思想性、宗教性或者科学性,但它们只在艺术创作中作为遥远而深蓄的背景存在。艺术就是艺术,艺术本体不应该也承载不了思想、宗教或者科学。我觉得生命的体验、感受,生命的状态要大于作品,大于思想性、宗教性、科学性。
(《关晶晶:从来就是这样》,《青年作家》2016年第1期)
荫曾蒙认为,把诗人经验改写为公共事件或者把对公共事件的观点切换成为个体的思考,这或者是一种写作才能,更是一个诗人成熟成为标新立异的创作冲动。种种道德约束、人为的成见都不会成为阻挡写作的动力。有时候我们看到小诗人的作品单独拿出来,比大诗人的要完美得多,但大诗人有一个明显的优点,那就是他总是持续地发展自己,一旦他学会了一种类型的诗歌写作,他立刻转向了其他方向,去寻找新的主题和新的形式,或两者同时进行。不断地转变、突围,不断地试验,以语言作为盾牌,又使得语言成为语言。写作的难度被不断超越,不断形成新的难度,不断地突破自己。这是个周而复始、没有终点的圆周运动,哪里都是起点,这也是诗人不断创造的源泉和秘密。
(《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青春》2016年第1期)
●陈仲义认为,现代诗经典化是时代语境、文本属性、审美习惯、接受口味、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博弈与合力的结果。现代诗经典化的“大指标”应充分考虑时空维度下的原创性、影响力与超越性三种。现代诗经典化需要漫长时空的筛选、甄别与耐心等等。它是集体记忆表层与深层铭刻的共同产物,其最显著标示是“流传”。现代诗经典化不同于诗歌标准的理性、抽象的“说教”,而是充满活的感性的形象化的“外延”。现代诗经典化意味着承认诗歌某些恒久性元素及其合法性,它们的留守与变异是继续重铸经典的支柱。
(《现代诗:不可或缺的经典化》,《南方文坛》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