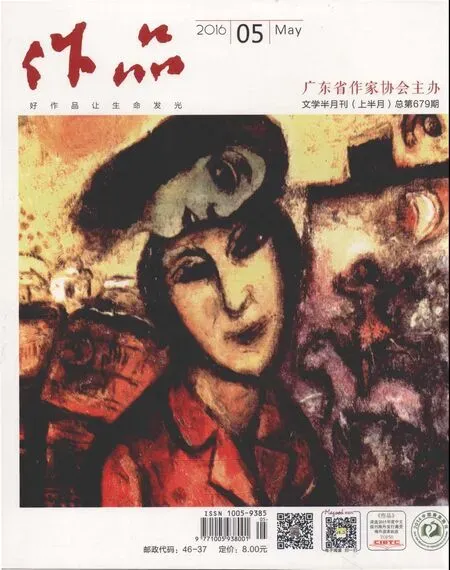寂静的浦西
文/顾青安
寂静的浦西
文/顾青安
顾青安女,原名侯丽芳,1994年生于甘肃。写小说和散文,文字见于《美文》、 《高中生之友》、 《中学生百科》、 《哲思》、 《课堂内外》等刊物。
小说的序言部分就定下了一种家族史诗的基调,也渲染了悲伤的情绪——主人公生在天寒大雪,被视为不祥的征兆。当读者读到这样的开头时,胃口就被吊了起来,因为家族冗长的命运连结起来,往往能造就一个引人入胜的小型的传奇。这样的传奇几乎存在于每一个普通的家庭里,如果不被作者一层层揭开,它们永远都会保持缄默。这也是我们乐此不疲地被这种故事吸引的原因,当故事展开,家族的历史被赤裸裸地展开,我们总会感同身受,潸然泪下。当然这篇小说也不例外,一开始就有让人读下去的欲望。
这篇小说以孙女的口吻,讲述着祖母的故事。这一层亲人的关系,看似亲密,却也注定了一种疏离感。孙女不仅是站在事件之外,更是站在时间之外,祖母的形象因此散发着独有的神秘感。虽然我们或多或少读过类似的故事,但顾青安的这篇小说简洁、有力,几乎不带任何多余的渲染和矫饰,在同类型的故事里显得非常纯粹,可读性也很强。在这种笔调下,祖母和曾祖母两位可敬的女性形象愈发动人。
读完这篇小说,还会想起作者开头描写的段落,“土墙的背后是湛蓝的天,有成群的不知名的鸟群盘旋飞过,发出鸣叫,有几只俯冲下来,落在不远处的灌木丛里,没了踪迹。”——“浦西”便是土墙背后的世界,仿佛是在灾难过后的一种小小奖赏,虽然它并不光辉伟大,却也散发着寂静和平凡的神性,值得大家品读、回味。
——栗鹿
序 言
我的祖母出生于1945年正月十六,时值天寒大雪,老一辈人多说不吉利,命运多舛,视为不祥。自此祖母漫长而寂寥的一生,从未过过生辰。
太爷爷,在冬天最后一场大雪销声匿迹的时候,给孩子起名赵吉吉。
愿其长女一生平安吉祥。
祖母所出生、长大的地方是西部清水镇塔北村,太爷爷去世得早,祖母是众姊妹之首,童年多寒食果腹,破衣加身。由于过早辛苦操劳,身子瘦弱矮小,像是随时可以被北下的寒风和隔日的饥饿送去与太爷爷团聚的可怜的孩子。
她一生默默无闻,一生穷困潦倒,一生颠沛流离,一生心无挂碍。
草草数语,便似能涵盖一生。
也许那些丢失的日子与生活的困苦如同顿河上化掉的坚冰,都和过往的岁月一般悄然流逝了。
但这并不是一个关于祖母的故事。
1955年,祖母穿过塔北村那个巨大的麦场,跨过清水镇界,越过顿河,到达了今天的浦西镇。
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故事。
顿河外的世界
祖母一直想去顿河外的世界看看,她想知道顿河那头是不是有巨大的麦场,麦子高高地摞起来,麦垛高得仿佛一眼望不到顶。是不是有巨大的棉花地,可以阻绝冬天寒冷的侵袭,是不是家家屋子里都有热乎乎的暖炕,人将脚一伸上去,就会感觉全身都暖和了起来。
那时候,她以为,顿河之外的世界,无疾苦,无寒冷,无灾病,无忧愁,自由平等,信仰随心。
便是世人所说的人间乐土。
所以她跨出塔北的脚步并未有丝毫犹豫,身上没有一斗米就毅然决然的向未知的路程出发。因为家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存粮了,为了留给冬日里还要给别人家洗衣服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吃,她选择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悄无声息的离开了。
走的时候最小的弟弟缩在那个黑暗的门口大声哭泣,她怕弟弟的哭声吵醒熟睡中的母亲,走过去轻轻地用手捂住他的嘴。
“嘘,别哭。阿姐给你去找吃的,天亮就回来了,你要听话。”
“知道了,阿姐,我等你回来。”
她猛烈地点了点头,蹲下身用力地抱了抱那个颤抖的小人儿,然后头也不回的没入了远方的黑暗里。
祖母饥寒交迫的走了三天,一路乞讨,最终叩响了舅舅家的木门,舅母看见立在大风中的祖母,坚持不让她进门。两只手牢牢地把住门框,三角眼里的眼珠咕噜噜地直转,连声骂道:“丧门星又上门了!”祖母无奈只好在舅舅家门外的草房里蜷缩了一宿,半夜乘着舅妈熟睡,舅舅才偷偷走出来抹着眼泪将两个黑面做的馒头塞给她。
“孩子……你走吧……是舅舅对不起你……”听舅舅这么说,祖母已经完全明白了。她默默地起身擦掉舅舅眼角的泪珠,小心翼翼地将那两个馒头裹在破烂的衣襟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草房。
她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听见舅舅闷声喊了一句。
他说:“吉吉,你要活下去啊……”声音夹杂着浓浓的哭腔和不可遏制的绝望。想来他也清楚,在这么个年代里,与她血脉相连的这个外甥女却不知何时会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死去。
她后来一直在想,那时候她濒临死亡却依然向往着顿河外的天堂,那里也许天气温和晴朗,远方遥远的平原上响起动听的风吟鸟唱,平房顶上的烟囱里炊烟缭绕,只是她后来才知道,原来浦西的冬天也是会下雪的!
祖母离开舅舅家门前的那片迷雾森林后,望着森林上方那片巨大的星河,不知道该往哪里跑,寒风吹得她的身子瑟瑟发抖,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和绝望。
她突然感觉到很疲惫,她的身体已经开始摇摆,冥冥中她觉得快要死了。寒风撕裂着她单薄的身体,她被漆黑的天穹压得有些头晕,脚下的路却一直都走不完。
心里不知哪里来的念头,她总觉得她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她深知明天深不可测,往前走才是最好的希望。
就这样,她一路艰难乞讨,做工,来到了浦西。
拖着身体前行的乞者
曾祖父在浦西镇口捡到祖母的时候,太阳正从玉龙湾升起来,清晨的第一丝阳光打在了镇口那座布满了弹痕的土墙上,他愉快地伸了伸懒腰,哼着秦腔想靠在土墙上抽支老旱烟,却看见土墙下已经失去知觉的祖母,他过去一看,人还没有死,一拍大腿,便把祖母背回了家。
祖母在前一天傍晚拖着已经孱弱之极的身体到了玉湾村,她觉得她似乎走了很久,终于她抬起头看到一面土墙。
她看到土墙散发着青烟和光晕。
土墙的背后是湛蓝的天,有成群的不知名的鸟群盘旋飞过,发出鸣叫,有几只俯冲下来,落在不远处的灌木丛里,没了踪迹。
她恍惚间看到那枚悬挂在玉龙湾的落日,然后因为长期的饥寒交迫,她就那么倒在了村口的那堵土墙下 。
她实在是太累了,她的身体再也无法前行,她的双脚再也无法去寻找顿河外那片乐土。她觉得她的灵魂一定是快要升天了,不然下一秒钟她怎么会看见一片金碧辉煌的屋宇,漫天的金光挥洒在她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她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她听到了附近婴儿的啼哭和狗吠,她听到了田野里麦子被风吹动,饱满的颗粒在风里相互撞击,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她的眸子已经被耀眼的阳光映成了金黄色,她的神态安详,再无忧惧,再无痛苦!
她扯开嘴角艰难地说道:“上天保佑!”
她想,她找到了,顿河外的天堂。
咧开干瘪的嘴角笑了一下,她终于微笑着晕了过去。
曾祖父名安德生,时年六十三,晚年膝下只得祖父安明泽一子,虽家中贫寒,对独子极其溺爱,那年祖父在浦西的镇里上初中,是浦西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之一,这件事也让曾祖父在人前风光了不少,平常在罗老汉那些人面前吹牛的时候也硬气了不少。
他逢人便问:“唉,你家的噢巴嘎呢?”
旁人听得莫名其妙,问他:“什么是傻巴噶?”
他像没听到一样兀自洋洋得意:“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奥巴嘎就是狗的意思!俄语!俄语知道吗?”
众人这才做恍然大悟,齐齐道:“噢……傻巴噶!”然后一哄而散。
曾祖父有些尴尬,他早晨听儿子背外文便顺口学了一句,本想显摆显摆,却不想闹了笑话。他也不在意,吧嗒吧嗒抽着旱烟上地里去了。
祖父早些年极其骄纵,看见家里多了一个吃白饭的人,气得摔了碗就走,曾祖父急得在地上直跳脚,下巴上的长胡子随着他的粗气一上一下的跳动,祖母吓得不敢吭声。
“这个不孝子……吉吉,你不要理她……你就在这里呆着,放宽心,凡事有我,看我回头怎么教训这个龟儿子。”
曾祖父看着瑟缩在墙边的祖母,微笑着喊道。
祖母一生尝尽人间冷暖,晚年提起这位我从未见过面的曾祖父,依旧是感激敬重居多,在当年那个人吃人的世界里,给了一个陌生人生还的希望!
祖父晚年也曾评价过他去世多年的父亲,只得短短八字却似涵盖了他的一生。
“明善处世,得人敬重。”
曾祖父尤其喜欢祖母的勤快善良,又心疼她的家世,于是便做主将祖母许配给了当年还在上学的祖父。
“1963年,儿媳赵吉吉嫁予明泽为妻,为人温良恭候,是为安家之福!”
多年之后,我翻看曾祖父的手稿,也只得这寥寥一句。
祖母的秘密
祖母嫁入安家的背后,当然并没有曾祖父在手稿上记录的那句话那么简单,除了曾祖父一力主张促成,祖父与各家亲戚邻居都表示了反对。
祖父更是半个月不曾回家,后被曾祖父强行从亲戚家里揪了回来,强迫成了婚。尽管成婚后的祖父依旧是半月不回家,但曾祖父总觉得自己给儿子挑了一个好儿媳,贤惠勤快。
其实曾祖父想得很简单,自己已经老了,儿子明泽说到底还是小孩儿的心性,家务农活竟是半分也不会,虽说是念了几天书,终究是无大用处的。自己给她物色的这个媳妇,好歹可以照顾他的衣食住行,也算是后半辈子有个依靠了!
这么想着,他忽然有些愧疚。自己见吉吉身世可怜,便存了让她进安家的念头,人家女娃啥都会,倒是自己儿子……唉,以后这光景过不好了,怕是要连累吉吉了。
可是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到时候明泽只怕无法自力更生。这么想着,他额间苍老的皱纹仿佛又深了一些。
因着那一丝愧疚,又或者是有别的原因,曾祖父生前对祖母极好,并不曾有半分苛待。
祖母入安家,祖父一直对她很冷淡,嫌弃她是一个乞丐,动不动就对她冷嘲热讽,连正眼都没有瞧过她一眼。无论曾祖父如何训斥劝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缓和。她做的饭菜只要稍微有一点不合口,他抄起碗便向她砸,她只得尖叫着险险地避开,然后眼神怯懦地站在原地不敢看他。祖父瞧她这副模样更是生气,冷哼一声便出了房门。
临走前他说:“赵吉吉,我要是你,肯定早就滚出这个家了!”
望着丈夫,她泪如雨下。她知道他嫌弃她,厌憎她,从来不把自己当做妻子看待。
但她还是默默地弓着身子收了地上的破碗,沉默地做着每天她都做的事情。
曾祖母在家里总是木讷而寡言,多数时候她都坐在门槛上晒太阳,两只娇小的脚丫并在一起,眯着眼睛就是一天。
她话极少,个子较寻常女人高大,眉眼开阔,从脸上依稀可以看出年轻时的样子。
祖母老是觉得曾祖母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因为从她狭长的眼睛和静默的神情里,她恍惚间觉得几乎看到了一个女人的一生。
她们婆媳之间的关系是缓和的,因为彼此都沉默寡言,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曾祖母便会在门槛里扯着嗓子喊:“吉吉……吉吉……”
有的时候,曾祖母也会拉着祖母在她常坐的门槛上聊天,这时候祖母总是很高兴,觉得她们之间的关系仿佛更亲近了。
曾祖母说:“吉吉……你真像年轻时候的我。”
她说:“吉吉,你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随即曾祖母的眼里竟然流出了两行浊泪,没有人知道曾祖母为何哭泣。祖母只当是婆婆心疼她的遭遇,心里感动莫名。便越发地孝顺这个古怪的长辈!
慢慢地,慢慢地,随着日子的推移,祖母很高兴的发现,祖父对她的伺候竟不再排斥,至少很少摔过碗筷了。她觉得很开心,她觉得以后祖父一定会慢慢转变对她的态度,为了这一丝丝希冀,她在家里干活更加卖力!
在这个家里呆得越久,她便知道的越多,渐渐地……渐渐地……她发现家里所有的人,每个人都藏着一个秘密。
于是,祖母向我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
那一场寂静的爱恋
曾祖母名叫沈九禾,沈家世代在离玉龙湾十里远的浦西镇,家里是一个小地主家庭,虽然算不上富裕,好歹曾祖母幼时倒也不曾有温饱的顾虑,家里有些田地,还雇了几个长工干活。
曾祖母十九岁的时候,在冬日清晨的一场大雾里恰逢出门,却看见晕倒在门口的一名八路军,便救了他。待得人清醒了问话,却道是附近打游击的散队遇到了袭击,仅他一人逃脱,又因弹尽粮绝,无法支撑,才冒险进村寻找食物,不想体力不支,晕倒在曾祖母家门口。
曾祖母对这个英勇的军人,几乎是一见钟情。喜欢他的英勇,喜欢他锋利的眼神,怎么看都比镇上那些只会摸麻将子和抽大烟的汉子都强。
她几乎衣不解带的照顾这个来路不明的军人,不顾父亲的反对,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两个人很快便陷入热恋。
只是军人伤好后却急着想回大部队,想报告这边的情况。祖母不依,总觉得他这一走,便永远不会再回来。
军人无赖的跟她解释道:“九儿,我这样子跟逃兵有什么区别,你不要逼我了好吗?”
曾祖母无力地瘫软在地上失声痛哭,即将失去爱人的痛苦几乎让她痛不欲生。
她哽咽着问道:“林越,你还会回来吗?回来娶我吗?”
身旁的林越蹲下身来轻轻地拥着她回道:“九儿,我一定会回来的,等战争结束,我便回来娶你。”
声音铿锵有力,充满了坚定的信念,依附在他怀里的她竟然再提不起反驳和质疑的力气。
林越必须要走,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外地已经抢占了祖国大片的领土,外面的很多人民都饱受战争的磨难,到处都分离崩析。
没有人可以逃脱这一切。
或许是受上天庇佑,浦西特殊的地形让它避免了战争的荼毒,但很快,他相信战争一定会蔓延到这里,没有人可以幸免于难。
所以,他走了,临走时他将他的手枪留给了她。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等我回来。”林越看着她的眼睛直直地说道。
她留着眼泪答应了他,目送他的身影在大雪里越走越远。
“等来年风起,我来看你。”
他的声音穿过窸窸窣窣地大雪,像是带着某种魔力般,准确地传入她的耳朵里,他相信她能明白。
那时候,对于命运多舛的人生,以及渺茫的时间,阻挡在他们中间这一事实,他们无可奈何。可是。笼罩在她心头的那一丝不安,渐渐消逝了。余下的,只有那个记忆中的背影,越走越远……
祖母讲到这里突然有些悲伤,我猜想也许这个故事并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那最后林越回来了吗?”我急急地问道。
“谁知道呢,或许回来过,或许始终没有回来。”祖母的声音好像是从那遥远的过往传来,带着宿命般的遗憾和叹息。
“况且人生啊,从来都是由不得我们自己去选择的!”祖母深深地叹气。
是啊,那么寂静的爱恋,要么他们曾经历生死,要么便是一别终身,淡漠如君子。
祖母告诉我,曾祖母这一生,怕是都忘不了那个雪夜,那时候曾祖母以为她十八岁时就看破了天下,熟知,原来我们耗尽周身气力看清的,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冰山一角罢了!
最后一颗子弹
没有持续的和平,没有持续的繁荣,所有的一切在人性的毁灭下,都开始走向灭亡的道路。
粮食越来越少,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冬天越来越寒冷,好多人都熬不过这个冬天去了。好多扛不住的人都上汤山当了土匪,一伙一伙地人扛着大刀,背起砍柴的家伙就干起了抢劫的行当,抢得光明正大,义正言辞。
这一年,世道都变了,人开始吃人了。
只是曾祖母心心念念想了三年的人,始终没有回来。
时间不久,沈家老太爷便被土匪掳去了山上,山上传下消息来,说如果沈家不交出多余的存粮,便将沈老太爷的头剁了,吊在浦西镇口的那棵大槐树上。听到消息的沈家老太太当场就晕了过去,曾祖母更是大惊失色,不知所措。
好在全家人冷静下来后,才勉强商量了一个对策,决定拿家里的两千斤粮食,从山上把沈老爷换下来。
沈家人拉着骡子队好不容易登上了汤山,这汤山顶上聚集了一窝土匪,在浦西地界内无法无天。
土匪首领揭开粮食袋子一看,不高兴地道:“你们沈家就只有两千斤,你们骗我吧,还是不把沈老爷的命当回事……”随即便冷哼一声看着沈家众人。沈家一应人都吓得腿脚酸软,好歹曾祖母也算冷静,提出说要先看看家人的安危。
沈老爷被带出来的时候,衣衫褴褛,肯定是受了刑,曾祖母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跑到她父亲身边扶住了那个几乎摇摇欲坠的身影。
土匪头子嗤笑了一下开口道:“我们也不为难你们,再拿两千斤,你们便可以回家了,这么点粮食,我们这么多弟兄怎么分!”
沈家人均是敢怒不敢言,凑齐这两千斤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曾祖母心想,这土匪如此贪得无厌,要完两千斤必定还会要得更多,今日这情景怕是不能善了了。
她猛地掏出林越走前留给她的手枪,指着众人,一字一句道:“我这里有十发子弹,九发送给众位,最后一发是为我自己准备的,倘若众位收了这两千斤粮食,放我们下山,就什么事都没有!”
众人均是一愣,不想一个弱女子手上有枪。一土匪嘴里喊着吓人的玩意就冲将过来,曾祖母眼睛一闭便开了一枪。
双腿不可遏制的颤抖,额头上冷汗直冒。
这是她第一次杀人,那人却没死,她打中了腿部,只是剩下的人却都不敢动,怕死是每个人的本能。
就这样,曾祖母孤身一人,带着沈家众人下了汤山。
直到成功下山后,曾祖母才瘫软在地上,大声哭泣。
祖母说到这里的时候,也是敬佩万分,佩服一个女子的胆识和勇气。但是我却怎么也无法将这个年轻时意气风发的女子与那个晚年自缢的曾祖母联系在一起,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人的命运转变得如此之快!
对于安家的这场变故,祖父的手稿里只有四字记录。
“世道无常。”只是简单四字,字迹却模糊不清,隐约判断是有水渍浸染,想来祖父写到这里回忆起曾祖母,也是情难自禁,潸然泪下。
浦西的落日
后三年,林越一直没有回来。曾祖母家道中落,在家里人的强逼下嫁给了安德生。她再也没有奢望,没有幻想,收起了意气风发,收起了年少风华,收起了无果的四年,老老实实地做了一个乡村妇人。
安德生惊喜交加的看着这个虽然已经快三十岁,却依旧风华逼人的女子,自是心里乐开了花。只是安家那位以前在沈家做过长工的安家老太爷却不这么想,心心念着以前的沈家大小姐最终也是要落到给自己每日端茶送饭,便好生愉快。
曾祖母在安家过得并不快活,不论曾祖父对她如何好,也改变不了她在安家要做苦力的事实。
安家两位老人丝毫不怜惜这个往日的主人,家里的重活几乎落到了她的肩上,她没有丝毫怨言,像是已经认了命。
曾祖母一直没有离开浦西,她心想如果有朝一日林越回来,怕是找不见她,所以她只能呆在原地等他,即使她自己清楚,那个人怕是再也回不来了。
或者他已经做了高官,或者他已经死在了战场上。
每天太阳落山的时候,曾祖母就坐在镇口的那棵大槐树下,望着汤山顶上的那枚落日,风来风又起。她脚下的那条小路也一直没有外人进村,于是她望啊望,却始终没有望见眼底的那抹地那抹青色。
曾祖父一生挚爱曾祖母,敬重那个挺身持枪的身影。他一生尊敬她,信任她,宛如对待最默契的伴侣。
曾祖父直到暮年才得一子,颇为爱重,孩子却不是曾祖母所出。
曾祖母入安家多年,无所出,安父或以为有什么怪病,执意让曾祖父再娶,要求多次无果。晚些年,隔壁桃花坞的林家女子才进了安家,曾祖母竟是没有半点不喜,不久林秀梅产得一子,安家举家齐欢。
本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祖母讲到这里也陷入了沉默,可是生活没有结束,那么故事也将继续。
曾祖母的自缢
曾祖母特地挑选了一个午后在屋后的偏房里自尽了,时值中秋,死的时候只有祖母在家里,死状安详。待得曾祖父跟祖父归家,才知噩耗。
曾祖父颤颤巍巍地泣不成声,只是一声接一声地说:“你终是解脱了……”
解脱了什么,为什么解脱,无人可知。命运就是一个巨大的齿轮,上面背负着的每个人都有一颗沉重的灵魂。
圣者克里斯朵夫渡过了命运那条河,他问肩上的孩子:“孩子,你究竟是谁?你为何这样沉重?”孩子答道:“我是未来的日子。”
真正让我们无法解脱的真的是未来日子吗?
曾祖母发丧后,祖父便携了一些值钱的行李离开了,他固执地相信别人所言,是因为祖母没有给曾祖母饭吃,才导致自己的母亲因为忍受不了饥饿,自尽而死。
他走的那天,玉龙湾起了一场大雾,祖母站在土墙外看着那个决然的身影,沉默的哭泣。
是的,她这一生,都在沉默,接受命运的安排,所以她不出声,不解释,但她并不懊丧,并不卑微。她昨天夜里在祖父的包裹里偷偷塞了家里值钱的物什。
她想,她要为曾祖母保守那个秘密。
桃花坞的林秀梅嫁入安家后,家里的一应杂务便都由曾祖母做,林秀梅从未将这个每天都将头包裹在头巾里的女人当做自己的姐姐,她娘家穷困,嫁来安家后又随即生了一个胖儿子,她的地位水涨船高,竟是享受了一把小姐的待遇,一应吃喝都由曾祖母伺候。安家老太爷和老太太冷眼看着家里的一切,并不出面回护这个向来勤快孝顺的大媳妇。他们更注重香火传承,生了孩子的自然就是家里的大功臣。
事情好像就应该这样继续发展,曾祖父给膝下唯一的儿子取名——明泽,尤其爱重。
林秀梅向来是个好吃懒做的女人,生了孩子只管让曾祖母带,曾祖母膝下无子,更加爱护这个孩子,颇为怜爱,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
祖父六岁时,曾祖母看见林秀梅在厨房责打年幼的明泽,赶紧放下手里的簸箕,冲到灶房护着他,期间与林秀梅起了争执,猝不及防间林秀梅摔倒在地,后脑勺被柴火上未除尽的钉子扎穿,当场死亡。
年幼的明泽扑在曾祖母怀里大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曾祖母蹲下身抱着祖父,身体不可遏制的颤抖,她的脑海中不自然的浮现出她第一次开枪杀人的时候的感觉,无边的恐惧翻江倒海的袭来,她只得将怀里的孩子拥得更紧。
地上的林秀梅的眼睛还保持着死亡前一秒的姿势,眼睛瞪得椭圆,像是经历了某种巨大的刺激。
她的血开始大面积的渗出,混着地上的泥土,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红色。
曾祖母抱着孩子突然开始呕吐,那种从胃里散发出的恶心几乎让她把苦胆都吐了出来。
人越来越多,所有的人都回来了。她的公婆,还有邻居……好多人都围着她,好多人都进来了,抬了尸体又出去了,身边有人在嘤嘤哭泣,指天骂地,很多的东西让她喘不过气。
有好事的闲话婆阴阳怪气的说道:“桃花坞那伙子人,家里姊妹众多,今儿的事怕是不能善了了……”
安家老太太狠狠地瞪了一眼地上的曾祖母,随即便扑倒在地上大声哭道:“我们安家是造了什么孽啊……竟然出了人命!”说完竟是跪在地上用手锤着地面大声地喊叫。
闻风赶来的邻居七嘴八舌的议论着,突然人群中有个声音就这么突兀的响了起来。
“我说,沈家妹子,莫不是你瞧不上林家这丫头,存心将她推倒了。”
声音一出,人群里顿时炸开了锅,所有人的眼神直刷刷地瞅着蹲在地上的曾祖母。她一言不发,也不出声解释。
直到此时,曾祖父才匆匆归了家。
他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拉起在地上的曾祖母,转身面向众人。
“我相信九禾,你们其他人莫要再乱说。我们安家的事自己会处理,今天劳烦大家操心了,入土的时候还要麻烦大家咧,诸位且先回吧!德生在这里谢过了!”
曾祖父深深鞠了一躬后,众人的议论才渐渐平息下来。被吓坏的祖父此时才“哇”地一声哭出声来。
在众人的注视下,那个一直躺在曾祖母怀里的孩子终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妈妈自己摔倒了……”
听完这句话的曾祖母伸手摸了摸这个在关键时刻保护了她的孩子,默默流泪。
从此以后,曾祖母一生抚养祖父长大,有如骨肉至亲。
只是,她怎么也放不下,这个口口声声喊自己娘亲的孩子,自己却亲手杀了她的母亲。
曾祖母走的时候一定很迅速,过往的一生如同电影般的在她脑海里划过,她一定是看见了什么,所以才想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说一句话。
嘴唇微张,声音却被吞进了胃里,再也没有出来!
“曾祖母是因为林秀梅的事情无法面对祖父才自杀的吗?”祖母漫长的叙述结束后,我疑惑的开口。
“要是无法面对的话,她估计早就走了!你曾祖母生前对你祖父那么疼爱,就算你祖父因为当年生母的死而对你曾祖母存有怨恨之心,这么多年那一丝怨恨怕是早就烟消云散了。”祖母伸手拉起掉落在地上的毛毯,盖在膝盖上。
“那是因为她一直都没有等到林越吗?”我想了想,觉得这个理由才是曾祖母自杀唯一合理的解释了。
“林越其实回来过。”祖母平静地说道。
“什么?”我吃了一惊。
“你祖父十岁那年,林越从很偏远的边疆回来了,听说从部队下来后便转到某个小城市做了官,稳定后他辗转到浦西,找到了你曾祖母。”
“啊,那曾祖母为什么没跟他走呢?”
“是啊,我也想知道她为什么没有走。”
也许她深信,命运的选择从来都是最好的安排。
隔年风又起
时值傍晚,曾祖母正在厨房准备给全家人蒸一锅玉米面的馒头,曾祖父在院里给骡子喂草。然后曾祖母就通过厨房那个狭窄的窗户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进了院子,好像是过路人,她准备出去留下那个赶路的人吃过晚饭再走。
可是她一出门就愣在了那里,林越端端地站在那里,眼神定定的看着她。
她下意识地把身子往后一缩,双手胡乱的在胸前脏脏的围裙上抓着。
她就那么直直地盯着他,想着匆匆二十年的时光啊,竟然就这么悄悄溜走了。
他老了很多,身子不似多年前那般挺拔,脸庞发福了不少,鬓间有些许白发,但唯一没变的是他看她的眼神,温柔的,寂静的。
她握紧了颤抖的双手,微微用力,指甲便嵌入了掌心里。
曾祖父像是一点都没有发现她的异常,朝还呆愣在原地的林越介绍到。
“这是家里掌柜的,你大老远过来不容易,留下来吃饭吧!”
说完便自顾自拉着林越进了堂屋,留下一脸复杂还没缓过神来的曾祖母留在原地。
晚上一桌人围在一起吃饭,曾祖母坐在林越对面,神色坦然的像主人一样招待远道而来的林越,她的神情那么自在,没有激动,没有喜悦,没有难过和怨怼,她的目光如幽深的井水一般寂静无波。
“那几年,我给九儿写了好多信,随信还邮寄了一些钱财,只是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杳无音信。我因为工作问题,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接她,却没想到,这一隔竟是将近二十年了。”
林越柔声讲着,曾祖母慢慢的将嘴里的咀嚼已久的食物吞进了胃里。
“你过得可好?至今一人吗?”曾祖母终于开口。
“得知你结婚后,我便成了家。我太太身体弱,边疆气候不好,前些年闹过一次大病,便去了。”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才是。”顿了顿,曾祖母开口说道。只是她的眼睛却始终落在桌上的一尺三寸里,从始至终,没有看那个昔日的故人一眼。
“成婚前,我曾随信附上了我的地址和车费,希望你能来找我!却不曾想意外收到一封回信,信上说你已嫁人。后来世事匆忙,没能回来。如今亲眼来瞧瞧,总是好的。”他说得缓慢,语气游离。
曾祖母听到这里终于皱了皱眉,她记得这些年并没有收到任何信件,自己没有他的通联地址,又何来给他写信告知自己嫁人一事呢?
曾祖母突然转头看了身旁沉默不语,不停低头吃饭的曾祖父一眼,然后她抬手给他碗里夹了一筷子咸菜。
曾祖父抬头望了她一眼,嘴唇哆嗦着似有千言万语。
饭毕,桌上的人各怀心思。
夜里曾祖母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曾祖父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睛瞅着漆黑的屋顶不发一语。
然后他就听到曾祖母开口道:“信是你写的?”
“不是我……是我让明泽写的。”曾祖父嗫嚅着说道。
曾祖母忽然叹了口气:“钱是人家的,拿了总归是不好,明天要还给人家才好。”
“前些年的钱我都不知道,有一回我撞见爹将信封里的钱拿了出来,然后将那些信扔到灶火里烧了!我怕你心里恼火,跟爹起冲突,就没敢跟你提。你不要生气,他们肯定不是故意的,你也知道他们不识字,肯定不晓得那些信是找你的。后来有天那人给你寄来了一大笔钱,信里要你按照地址坐车去找他。我心里一迷糊就让明泽给他回信了,可是你放心,那笔钱我原路退给他了。”
曾祖父说得很急,想来也是觉得理亏。
曾祖母没吭声,眼睛直晃晃的望着他,那双眼睛跟明镜似的,照得他不知所措。
曾祖母心里这些年的疑惑终于豁然开朗,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那些厚厚的信件和钱财,就算不识字,找人看看也是可以的。然后林秀梅的到来,这么多年所遭受的白眼和冷遇,这一桩桩一件件,却原来,从不是无缘无故的。
被曾祖母这么一望,曾祖父心里愈加内疚自责。
“算了,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还会来找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跟他走吧!总归是安家人对不住你,这么多年,你受的苦已经够多了。”
“夜深了,早点睡吧!”曾祖母说完竟是一翻身睡去了。
曾祖父万万没想到曾祖母会这么轻而易举的揭过这件事,就好像是她昨天错过了一道雨后的彩虹一般简单。
可是那雨后的彩虹尚有再现的时候,人的命运呢?错过了,便是错过了。
林越走的时候,曾祖母在村口那棵大槐树下送他,如同千万次她站在这里等他归来一样。
“你老了很多,看起来过得并不好,当年为什么不肯来找我呢?”
曾祖母突然眼泪就出来了,心里是说不清的酸涩之极的情绪,让她忍不住想哭出声来,但她没有。她就那么抬头,望了望槐树枝头的那一抹极淡的云彩,眼泪就瞬间没入了眼底,悄无声息。
“你可是对我有怨言,怪我当年没有等你?”曾祖母反问道。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想来你也是有苦衷的。”林越缓缓的摇了摇头。
“但是现在,你还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吗?”他想了想还是怀着一丝希望问道。
曾祖母心里大恸。
玉龙湾的落日终于跌入了山谷,留下一抹烫金的颜色,那个人像多年前的那个雪夜一样,消失在了视线里。
曾祖母裹着头巾进门的时候,曾祖父“唰”地一下从炕上窜了下来。
曾祖母神色如常,她平静的喝了一口水,然后准备解了头巾做饭,就像她很多次回家后的情形一样。
“你怎的……怎的又回来了?”他以为,下午的那场送别后,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去做饭,你把柴火劈了,明天明泽上学要带到学校里去。”说完曾祖母自顾自往厨房走去了。
曾祖父突然老泪纵横,那样子像是有人抢走了他心爱的那杆老烟枪,他分明是开心的,却觉得心脏好像被人用大锤重击了一般。
他隐约明白,那一刻,他永远的失去她了。
“如果有一天你要是死了,我一定去找你,这是我愿意做的。但是如果你活得好好的,我却不想和你过。”
那是曾祖母对林越说的最后一句话,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她在漫长的岁月里,恪守一个为人妻子,为人母亲的本分。尽心照顾家庭,看着儿子成家,然后在那个缺衣少食的日子里,在那个林越逝去后的某个下午,她去做她愿意去做的事情了。
她一生都在向那个远去的背影靠近,那是她心里想做的,她便做了。
我在等你
祖父在外漂泊几年,花光了祖母留给他的盘缠,在城里终是混了个灰头土脸,迫不得已卖了身后最后一件棉袄,落魄归家。
他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副场景。
他的父亲身子佝偻,瘦骨嶙峋,颧骨高高突出,眼神浑浊地坐在家里那把破旧的摇椅上。他的妻子正蹲在地上,捧着父亲的双脚清洗。盆子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身旁的泥土。
阳光在房顶铺射下来,他年轻的妻子,神情专注,恍若未闻。
心里的酸楚翻江倒海的向心口涌来,他低着头,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他看着对面这个灰头土脸的女人,不理解她怎么还在这里。
祖母看着他的眼睛,严肃而专注的陈述道。
我在等你。
是的,她就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她坚守在这个家里,照顾公公,等待那个不知道何时才能归来的丈夫。家里的锅里只剩下一把她从山上挖的野菜,米缸里空空如也。
她终于松了一口气,眼神欢喜。
下午公社分的粮食就下来了,我去领。你先吃这个。
祖父看着手里的野菜团,大口大口的吞咽着。
家里的劳动力都要去公社干活,他不在的日子,这个女人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养活着父亲。
那一刻,祖父抱着苍老的曾祖父泣不成声。
后来的日子很平静,祖母笑着向我讲述道。看着她苍老面容都遮不住的笑意,我猜想她必是过了人生中一段美好时光。这日子如此美好,以至于连回忆都散发着迷人的香气。
很快,祖母有了五个孩子,也有了我的父亲,为家里幼子。
祖父给父亲取名,希望。
父亲出生后,家里几乎陷入了绝境,一家人的温饱成为每天必须要解决的难题。他们必须为生存考虑。
后来,祖父毅然抛弃玉湾的祖屋,举家迁往浦西。搬家的理由只有一个,在浦西,一个人的工分要比在玉湾村多一分,而就这一分,却可以让他们多一份粮食,好养活庞大的家庭。
自此,安家整个庞大的家族便开始在浦西开支散叶,当然这是后话。
对于那段过往,祖父手稿里也只有一句感慨,就那一句却似乎已经说出了他全部想说的话。
“活下去。”
“这是多么奇妙的轮回啊,十年前,我的舅舅告诉我,一定要活下去,十年后,我的丈夫告诉我,一定要活下去。于是,就这一件事,却几乎耗尽了我半生的力气。”祖母的手搭在藤椅上,有风吹过,她的白发比珍珠还要美丽。
我的祖母一生都是寡言而无趣的人,认识的人都这么说。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经过岁月的打磨,却更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光彩。
于是,千山万水美好。
是的,这是两个女人的故事。
但这并不只是两个女人的故事。
我于这世间的缝隙窥探人生,人生不过千奇百怪、光怪陆离的一回合而已。
人生仓皇打马而过,不过寂寂一瞬,由此,对于生命之苦难,灾厄,尚可不畏惧,过好一生。仅此一点,我甘之若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