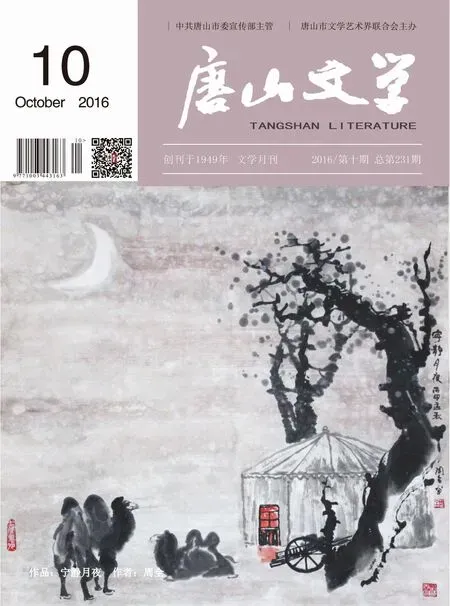雌雄同体:陷阱还是出路?兼论《黑暗的左手》与《方舟》
刘旭超
雌雄同体:陷阱还是出路?兼论《黑暗的左手》与《方舟》
刘旭超
“雌雄同体”这一原型有着古老的文学文化渊源,上世纪后半叶,美国女作家勒古恩和中国的张洁在《黑暗的左手》与《方舟》中分别从生物学、社会心理视角切入并建构着雌雄同体的“冬星”和“方舟”,这种建构是出路还是陷阱?本文就此予以评述。
“雌雄同体”这一原型,在中西文化史中有着古老渊源,最早见于神话宗教,如希伯来《圣经》中雌雄同体的亚当与夏娃、古希腊菲尼基阿斯塔提、印度神话主神湿婆、中国神话连体交尾的伏羲女娲等,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原始初民朴素的性别平等意识显现。然继之千年,这一思想基本消隐在男性中心文化价值体系中;也是在近代女权运动兴起,复活了的雌雄同体集体无意识被唤醒并反映在各领域中,如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双性化”、德里达“非两分性别”、伍尔夫在《奥兰多》里关于双性气质人物的塑造等。上世界后半叶,伴随着第三次女性主义思潮性别视角凸显,中外女性主义作家都颇为关注女性自我经验及理想性征的建构。倘说厄休拉˙勒古恩的《黑暗的左手》是从生物学角度切入的一场有意的雌雄同体的“思想实验”,那么张洁的《方舟》则是一场无意的深入到社会生活的雌雄同体“现实实践”。
一、“冬星”与“方舟”
厄休拉在《黑暗的左手》中对基于生物学实验的“雌雄同体”人和“冬星”寄予厚爱;张洁则于《方舟》中从基于社会学、心理学建构的“雌雄同体”人那儿展现一片绝望“方舟”。
《黑暗的左手》最出奇的莫过于雌雄同体人的生物学性征:“格森人的性周期通常是二十六到二十八天……第二十二或二十三天,他们会进入克慕期……当个体找到了同样处于克慕期的伴侣时……雄性或雌性荷尔蒙会在其中一位伴侣身上占据主导地位,此人的男性生殖器随之增大或萎缩……哺乳期过后,女性重新进入索慕期,接着变回一个彻底的双性人,生理上不会留下任何的后遗症。”那么,在取消“性别”这一天然尺度后,受道家合一思想影响的厄休拉追诉的是以伊斯特拉凡为代表的融强健体魄与柔韧性情于一身的新人和摆脱了性别对立——一切思维行动矛盾根源的“冬星”。
而在《方舟》中,基于社会学、心理学建构起来的“雌雄同体人”在现实实践中是否有如“冬星”般美好呢?曹荆华等“雌雄同体人”传统的女性特质,婚姻、家务、身段“样样不在行”,代之的是思想上刚毅果敢、行为上抽烟、喝酒等男性特质,如梁倩在面对“女主角的奶子怎么那么高”责难时针锋相对:“奶子高也成一条罪状了?……能削下去一块吗?装什么正经。”然而,女性的雄化并没有诺亚方舟,曹荆华坚持真理在“那篇冒尖的论文发表之后”,“刀条脸”的批判甚至“安眠药”设伏使其遍体鳞伤;柳泉在与魏经理“侮辱性的挑逗”周旋的疲惫不已;梁倩费尽心血视培育的如儿子一般的片子因莫须有“思想意识问题”被“枪毙了”。
因此,《黑暗的左手》生物学层面对女人的寻找亦或《方舟》以社会学、心理学等文化层面对女人的探寻,始终落脚于“雌雄同体”。这一思想实验和实践中,是陷阱还是出路?
二、陷阱还是出路?
《黑暗的左手》中以伊斯特拉凡为代表的冬星人与《方舟》中的三位主要女性从生物学、社会心理层面实现雌雄同体建构来作为对女人身份的寻找,是一种女性自我性别消解追求男性文化价值实现的过程,自然悲剧地陷入男性中心主义思维的怪圈;然而,这种自我寻找又蕴含着生物学、社会心理层面的出路。
在《黑暗的左手》中,厄休拉以女性生理特质为摹本建构包容于两性性征的“雌雄同体人”,且不论思想可行性,单就伊斯特拉凡与金利˙艾的生命诉求及冬星上卡亥德等国的政治气候、风土人情,一以贯之的仍是男性中心主义文化价值。被厄休拉寄于美好期许的伊艰难跋涉甚至付出生命来促成有性别偏见的金利˙艾完成使命,那些认为使命完成便是文明开化演进的学者疏忽了一个事实:伊所促成的愿望是两个星球“增加物质利益,开阔视野,使智慧的领域更加丰富”,而来到格森星的艾库曼人与冬星人的“性沟”依然是一种对立的存在;再就冬星自身政治动荡、风土人情的背后仍是强势的男性中心文化的内在逻辑,这是文本和创作本身的“俄狄浦斯式悲剧”。在《方舟》中,三位主要女性现实的突围更印证了这种寻找的悖论,且不说梁倩等人事业是否如愿,如此绝境的存在本身亦不是女人理想的存在。
然而,这种自我寻找又蕴含着生物学、社会心理层面的启示。在生物学层面,随着科技发展,试管婴儿、人造子宫等技术日益成熟,女性在摆脱生物学上的先天负担以及长期的传统社会家庭事务负担后,由基因变异表现在性器官效能转化,像冬星人般自由变体也并非不可能;而在社会心理层面,人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存在并在对象化过程辩证性确认自我的本质,那么祛除我们的社会心理文化集体无意识偏执,人的双性化更不可避免。
因此,关于“雌雄同体”的建构是有益的,倘能改善生物层面负担、消解文化障碍,两性实现作为“人”的存在且在与之体认与反叛中找到属于男人和女人的特质,这不失为可行之路。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571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