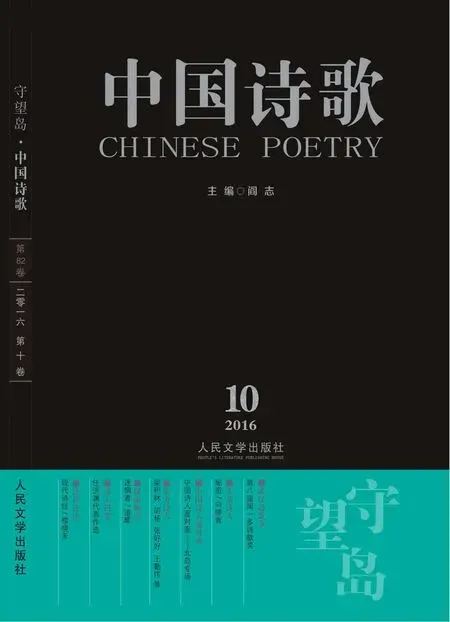齿轮〔组诗〕
星芽
齿轮〔组诗〕
星芽
齿轮
这些年 我听命于身体里小小的齿轮
它们往西转动 我的步子就不会迈向东边
它们睡着了 我在书页里低头
食用青草 学会了钻木取火 海底捞针
修理失眠的右眼
给身体里的犀牛 野豹子
补一补牙 为它们制作
防水的面具和胶鞋
醒来的齿轮 是一连串
铿锵的冒号 它们往西转动 发出的
可能是父亲的声音
弟兄姐妹的声音
教授的声音
上司的声音
睡在黄土里爷爷舅公的声音
活着的人牵着我走进羊群
喂给我黄金和螺母 死去的人
依旧在梦中 对我滔滔诉说
而我肚子里的青草仍在徒劳地窜长
多么亲密的齿轮 日以继夜消磨着
奔跑的野豹和犀牛
刺猬的生日
我出生的时间正好有刺猬经过
它们是潮湿的 但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接下来的几年 她将要借我年幼的躯体遮蔽锋端
动物学家 那些尝试用一本教科书
就将我们分离的
事实 外面的阳光爬上了屋脊
圆圆的刺猬不适合作为我声音的一部分
不止一次 我模仿它们滚过中央公园的草坪
在机车横穿的马路上发出致命的尖叫
我回忆起与它们出生的同一天里
那日阴雨绵绵
刺猬细软的爪子朝着泥块翻动
像几片湿云
冬天的馈赠
抹了蜜糖的收音机 以一只马蜂的方式告别双耳
更多的亲人跑到冰花上去喝冷冻啤酒
那是在一个别样的冬天 艺术家试图在甲鱼的身上大做文章
微苦植物的小刺果们 赶走屋舍周围的野兽
我们一会儿去河的上游垂钓
一会儿拧开笔头听宇宙的声音如何在诗歌中死去
雪簌簌地落在瓦檐
一个时辰的酒宴后 继续劳作的人
将要搬开木桶 把星辰一点点地装回盐袋
尽管父亲曾经教给我们唱诵圣歌
除了劳作 就要感恩天空土地
除了劳作 我们剩下的就只有眼前的这座小木屋了
每天 父亲把肥沃的雪块铲走 拿苞谷喂食麻雀
像这个冬天对待我们一样地
以在寒气中打旋的荒唐形式 几片雪花
给予我们幻想的牛奶与炉火
降落伞
降落伞坠下来
小a 小b都收到了我的信号
泥土因为扭结而蜷曲得更深
我们必将在共同体的记忆中
怀揣往事
像水池里被频频震碎的草木
降落伞一夜之间
成为我们飘忽不定的鱼钩
野地里
她养的金丝鸟跛了一条腿
她运送蔬菜的木车轮胎刚刚被换掉
她否认自己栽的田禾是绿色的 摇曳在草坡上
蟋蟀的眼皮垂下来
像个化开的大葫芦
孔雀之美
孔雀 请你们转过前世的身子
无需用开屏之美劫掠男人女人的关注
你们肩膀上的纤细面粉
终于被指甲抠出一株荷藕
在马车桥公园里 它们被一个精神病人焚烧
留下乌黑的根须 从此 不会有孔雀再去相信
事物一成不变的美之伦理
我所遇见的孔雀 有的已经参破红尘 被装进道长的皂靴
有的则成为审判官五颗脚趾中的其中一颗
孔雀在小学生的政治课本上正面临枯竭的危机
谁在日以继夜窥视着我们 要求恶人解放孔雀
为它们美丽的代价摘下哲学面纱
像这个新生时代解放女子的缚足礼
孔雀可以平等地坐在我们对面 端起一只茶杯
灾难关头
有时也会像一位绅士那样风度翩翩
话马
拴在马腿上的国家只是借马的嘶鸣声
来威慑四方 其实共和国的旗帜远没有马的脖子长
骑士的臂力也比不过马车夫
鞭子扬起的沙土却让我们望尘莫及
你们有砍掉的马头
用来替换悬在国王脖子上的铃铛
因此屠夫才是连通耶稣的大使
他们硕大的耳垂成了天堂与人间的活性塞子
我们匍匐在马的腰段下
给这些四条腿的动物穿上人类的皮鞋
为它们发表演说的喉舌准备一只高音话筒
等到夜深人静 月亮忘记了杀人
国王就会把多出来的一对马腿
埋进他后花园的水晶棺
来自海域的信
我的第一封信来自水底
目睹鲸鱼的鳃帮被海盗研成墨汁
印象中有关海洋的无非是沉船里的青铜宝藏
在岸边 我的鞋子与信件同时被扑上来的浪花打湿
一个人可以骑着螃蟹出海
也可以把鱼钩别在衣领前向来往的船只敬礼
昨夜死去的诗歌已经被我装进了信封
在今晚的月亮将小镇淹没之前
希望你们可以收到它
白萝卜
我的口琴 买于屯溪三马路的一家文具店
十一年了 店铺对面的小学建起了徽州牌坊
远远望过去 里面背双肩包踏着牧童牌旅游鞋的孩子们
我仿佛在哪儿见过
一定是小a 小b 小c的身体都缩小了
像一只只努力钻回土地的白萝卜
只留出头顶的一点点叶子
游子吟
脾气遇火会变薄 但从不发出开裂的爆鸣
表情上麻木的鱼类因此一捅即破
多年来 替自己打好一副棺材 只用檀木 鸡冠花
在泥土周围洒一圈白酒
就像我不谈及死亡 牙齿也会被沙棘鼠埋进冰雪
喉咙迟早给心怀不轨的哑巴偷走
仍在生长的头发也无法掘地三尺
好在 还有机会食用家乡漫过我下巴的凄凄荒草
以及一次次掀翻牛羊的浪子春风
返乡
我们缴获的镍币
被投入水潭清浑的两面
朋友喜欢蹲在岸边 指着那些裂腹鱼的鳞甲
“它们背负一身红藕 披麻戴孝 却不哀之过及”
多像我们零落成泥的故乡
又在鱼儿的身骨里陷落
凌晨 太阳翻出山坳
我们折断晨露深处的细柳
竹木屐绑翻诗中的黄鹂
许多年以后 水潭里的镍币全锈成了呼啸的鱼纹
我们搀扶着双双病倒在返乡的古道上
二十只喜鹊
春天 他们把喜鹊的声音拿来做酒
二十只活喜鹊的嗓子
医好了村子里的哑巴
一部分的胸脯发绿如丧钟
全是中年的喜鹊
在教堂里背《圣经》 啃木头
喜鹊通体明亮 却不食人间烟火
梦游的时候单脚着地
心怀不轨的人会在它们的脖子上
系起吊绳 另一些苦命赤贫者
将双手放在喜鹊的腮帮下
拼命乞求这些幸运的鸟儿 磕破了头颅
他们相信喜鹊的身体里
藏着一轮满月 像掏出高粱里的铁器
村庄里所有的聋子和哑巴
口皆不能发声 耳朵丢在了荒野
只有这二十只喜鹊的意义
被偶尔刮过的春风
鞭打得越来越新鲜明亮
我们在谈论动物的腿
四条腿的动物可以是丛林走兽
两条腿的一般是飞禽 游鱼是无腿的
我和表姐谈到动物的时候
会预先算计好腿的数量
至于毛色 性格 它们脖子里的粮食
全不是我们关心的话题
我们只偏爱议论它们的腿
比如我一提到八条腿
姐姐会立马说出蜜蜂 蟋蟀 金龟子
等一系列词 仿佛这些昆虫
是从她嘴边突然蹦出来的
我提到两条腿 姐姐却从来不会想到人
相比于家里夜夜酗酒的哥哥
从两条腿走成三条腿的祖父
隔壁用一条腿走路的跛子叔叔
她更爱说出停在围墙外面的鸟儿
比如山雀 乌鸦
红嘴巴的鹦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