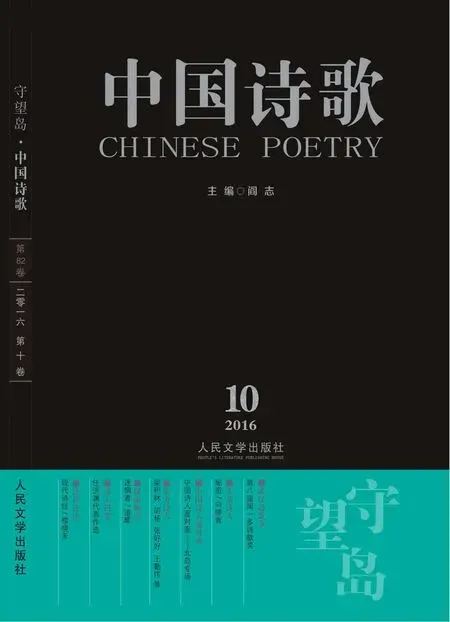茅草的诗
茅草的诗
MAO CAO
杏
杏跟着姥姥进城来了
躲在一个竹篮里偷偷地看我
她红红的脸酸溜溜的心事
还在回忆与我的过往
那时候她长在树枝上
饱满的身体把树枝压弯
我调皮又贫穷
一心想携着她去私奔
现在我掏出人民币
把一篮杏全买下来了
我大口大口地咀嚼她们
感觉不到当年的味道
迎春叶
迎春花不愿意再做迎春小姐
躲在迎春藤里不肯出来
我走过春天
走了整整一个季节
也没有看见迎春花的身影
迎春藤站在路两边
派出一些叶子来欢迎我
回来
楼道里挤满了人
楼上有一间更大的办公室
大家都想去
都拼命地往楼上挤
我从我的小办公室里走出来
犹豫不决
一步三回头走到楼道前
天就黑了
窗玻璃上的霞光转了一个弯
我面对窗户心随霞光飞去
楼上的那间大办公室与我的书房偏差太大
算了吧
我还是转身回家
听老歌的感受
一支死去的歌曲活过来了
它想找到它曾经呆过的地方
想找到唱过它的喉咙
想看到那张热情洋溢的脸
结果它没有如愿
世界已经面目全非
它活过来是孤独的
一个不合时宜的人走在大街上
东张西望怪模怪样
除了几只耳朵对它有点儿熟
它对什么都不熟悉了
阳台
阳台挂在半空中
依附在墙上
飞不起来也掉不下去
供室内的人出来
晒一晒阳光除一除霉味
吸一吸新鲜空气
赞一条裤
一条沉不住气的裤
遇到一点丰满就和盘托出
本是一个遮遮掩掩几千年的地方
现在原形毕露
不留一丝儿余地
挤出一个心脏的形状
我恍惚听到怦怦的心跳声
恍惚看到一只蝴蝶
飞出峡谷
飞过流水淙淙的小溪
衰老
岁月一直跟踪我
跟踪我五十多年
我一直想甩掉它
可是甩不掉
现在它猛扑上来
对我的肉体进行围剿
细菌和病毒组成联军
把一些器官追得东奔西逃
灵魂是肉体的叛徒
它得救了
它目睹肉体老态龙钟
在我的书房里朗诵小说和诗歌
父亲的拐杖
父亲手里的拐杖
跟在老黄牛的后面
听着老黄牛的脚步声辨识方向
父亲走在望不到尽头的犁沟里
探索着要走的路
父亲手里的拐杖
撑着我头顶上的夜空
月亮星星不会掉下来砸伤我
父亲手里的拐杖是我命运的杠杆
撬起我脚下的道路
我从低处走向高处
走进了大学住上了高楼
父亲看着我走稳了住安定了
倒在了我起步时的那个低处
羡慕
草莓苗生活在阳台上
我儿子养着它
我儿子把目光浇给草莓苗
草莓苗怀着一颗草心
回报给儿子洁白的花朵
夜晚的我
走进夜晚
我躺在自己的影子里
太阳来临
把影子从我身体里拉出来
这个季节的花朵
花嘟着嘴
不说话
扮一个撒娇的相
风摇动它的肩膀
它不回答
兀自在黄昏里静静开放
红红的嘴唇咧开
想笑
想一吐为快
其实都不是
等采花的人来
以色彩示人
失眠者
失去了职位和酒杯
也失去了睡眠
嫦娥静悄悄地站在窗外
不再进来陪他
那些好听的词从耳朵里撤退
回到了制作它们的嘴里
而那些嘴紧紧地闭着
再也不肯松开
妻的声音重复而又单调
他喝着一杯白开水
没有一点味道
一朵花的裸照
白玉兰在太阳下分娩
刚刚降生的白玉兰又白又嫩
一位老人坐在阳台上晒太阳
他眯缝着眼想
白玉兰是不是早产了
绿叶的襁褓还没来得及准备
这时候树下走过来一位新娘
摄影师的灯光一闪一闪
荧屏上留下了白玉兰的裸体
留下了老人的泪光
两棵含笑树
太阳没有推动办公楼
把办公楼的身影推倒在地
办公楼的阴影逮住了一棵含笑树
另一棵含笑树见势不妙
跑到了阳光中
被阴影逮住的那一棵含笑树
想笑笑不出来
跑到了阳光中的那一棵
炸蕾怒放
上班的人下班的人
都不愿意走近阴影中的那一棵
绕道也要走在阳光中去
灌木
1
乔木有向上爬的本钱
灌木长不高
灌木不认为自己长不高
老怪乔木遮住了自己
2
乔木一手遮天
灌木生活在它的阴影里
灌木想走到没有乔木的地方去
却迈不开步
宿福州三明大厦601房间
4月8号至11号
我下榻福州市三明大厦601房间
准备参加明天的会议
这恰好符合我的人生
坐了一天的车有点劳顿
走进房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把门打开把窗户打开
让风吹进来
坐在床上盘着腿
看电视入了迷忘记了在哪里
上卫生间冲个澡
跟在家里一样
晚饭后站在窗前
前面是满城的灯光
感觉妻子就在我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