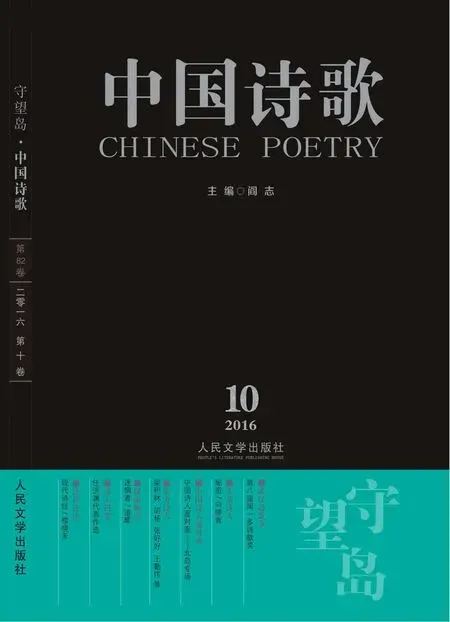孟松的诗
孟松的诗
MENG SONG
埋坟的人
暮色,像一个埋坟的人
它刚埋完远方的山岗,村子,河流
又转过身来
一锹一锹埋掉身旁那些
埋头走在回家路上的牛群,和羊群
对赶往村尾的那条小路
我亲眼所见,它是迎面埋过去的
那一位举着火把赶路的人
其实,也是它想埋葬的对象
只不过,暮色
对他手上的火把有所顾虑
仿佛他的手里
提着的,是一把明晃晃的刀
一只找回人形的麻雀
这是一群,操着各种方言的麻雀
一群在工地与工地之间
飞来飞去的麻雀
一群长时间戴着安全帽
却很长时间,没戴过安全套的麻雀
一群梦想离开土地
却又成天灰头土脸的麻雀
一群被工头吼来喝去
却把自己的吼声,藏在心里的麻雀
一群在钢筋水泥缝隙里觅食
太阳下忙碌,流汗,甚至流泪的麻雀
昨天,我看见有一只
从工地十楼飞下
先是安全网扯了他一把
尔后,是脚手架拦了他两次
最后是泥土地面
帮他找回了,一个深深的人形
撕日历
在办公室
我每天都在干着一件事情——
撕日历
撕过初一撕十五,撕完春天撕冬天
从日出江花红胜火开始
撕到杏花春雨江南
从落叶潇潇无穷尽往后
撕到我内心里的雪,比南山顶的还要厚
这些年来,我不停地撕
从汉王山撕到矿山
办公室也从底楼撕到二楼再到五楼
先后撕退休了黄大姐,曾大姐
马上又要撕退休庞大哥
中间,还撕走了我的同事老吴,和小杨
一次次想到命如纸薄
每一次下手,我就胆战心惊
老感觉那薄薄的一纸日历
就是一个人的命
这么想着,昨天我点燃撕下的一页
火光中我竟看见了我自己
百年之后
几十年来,人世间行走
我一直努力的方向
就是,将我的这一副肉身
活成命运一样曲曲折折的汉字
这样,百年之后
你看到的我那206块骨头
就是你眼睛里的横,竖,撇,捺,折——
长一点的是我的胫骨
短一些的,是我体内的趾骨
而那些顽固不化的
一定是我的脊梁,和碰过南墙的头骨
如果你突然看到多出一块
带有尖锐和棱角
请你,一定不要惊讶
我从未长过反骨
它要么,是我命运里的沉疴
要么是一条大河
流经我身体时,带给我的沙砾
墓志铭
绝不选用仿宋体
中规中矩,已害了我几十年
隶书虽好看
好像微微的起伏
并不能,说透我起落的一生
行书就不用选择了
太过圆滑和世故
不符合我的处世原则,和风格
就直接选用草书吧
刚好够,表达我潦草的一世
既暗合我的二两草命
也无需人人能看懂
其中,孟松的“松”字中的几把刀
一定要写得锋利一点
方便我与这个世界的恩怨
能痛快地一刀两断
但刀锋须朝内
宁可伤自己,也不要伤别人
母亲在我额上写下一个“王”字
我不止一次见过
老家的阴阳们做法事时
或断掉公鸡脖子
或直接掐出鸡冠上的血
关于血,可以驱邪避鬼
老人们也常说
一生身在农村的母亲
对此,更深信不疑
那年冬天的夜晚
雪花在窗外不紧不慢数着九
只有九岁的我
高烧,说起了胡话
急出眼泪的母亲
油灯下,用缝衣针刺破左手中指
用挤出的血珠
在我额上写下一个“王”字
上帝的迷宫
此刻,我正扮演上帝
给一只蚂蚁备下
一只无限光明的玻璃瓶——
许以蓝色的天空
天空中,棉花一样的云朵
许以云朵下
山川,河流,大地,草原
许以城市,乡村,和纵横交错的道路
许以小桥流水人家
许以空气,面包,和水
再许以一个情投意合的爱人
这些,都是我的障眼法
我真正的目的
是要给蚂蚁摆下一座迷宫
看上去,很美的那种
我故意不给它导航,和网络
让它空有一对天线
一想到,上帝每天就是这样
给我们摆弄迷宫的
轻轻一声“兄弟”,我还没喊出口
双眼已经噙满泪水
路边的树
昨天路过,我看见
一群麻雀在你耳旁鼓噪后
又在你的头上拉屎
尔后出现,令我不能再忍的一幕
一只叫黑豹儿的狗
跑过来落井下石,将一泡污秽
浇淋了你一身
为此,我向那群麻雀扔石头
将那只狗撵出老远
我不愿看到你被欺负的样子
这片城市的天空下
你作为树,而我作为人
谁活着都不容易
一想到你站在路边
和我一样,风里来雨里去
为了生活而隐忍
内心里,就生出同病相怜的悲悯
蜗牛
实在忍不住了
我只想弯下腰来,叫你一声兄弟
其实一大早我又看见了你
用整整一个晚上
从阳台那头,爬到这头
你翻过的中间那只大花盆
在我看来,和我工作过的汉王山差不多
你爬过的那截枯枝
就像那些年我随时都经过的南广桥
这不,枯枝下的一线积水
不就是那桥下的河水?
最不敢看的,还是你背上的壳
总感觉那是你替我背的
真的像我这么些年来
被生活压得越来越弯的腰
看两眼,我就情不自禁会流泪
可可只有五岁,还小
爸爸常年外出打工
妈妈正在不远的坡地上挖红薯
整整一个下午,可可
自顾自在红薯地边玩着堆坟墓的游戏——
一个堆给前年死去的爷爷
坟头插着一朵野花的,那一个
堆给去年又走了的奶奶
堆好爸爸,和妈妈的那两座
他又堆了一座更小的
边堆边说,这个给再不调皮的可可
地上的一堆散泥
他心里想着,还是应该
堆一个给在他身边转来转去的狗狗花花
爷爷,奶奶走后
每天就只有它一直陪他玩了
风吹过,初冬的阳光有些冷
可可只有五岁,还小
他还不懂得孤独
但他已提前懂得死亡,和一生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