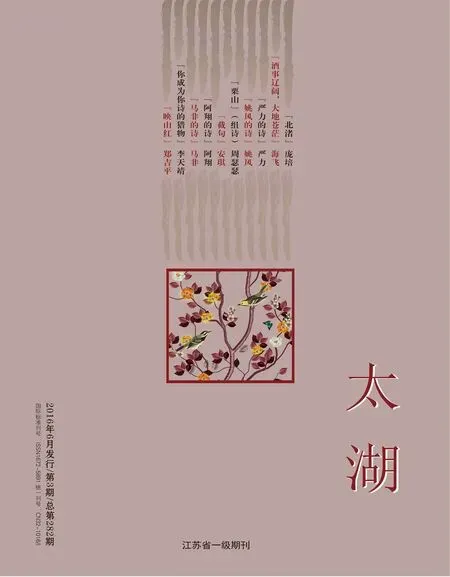安宁
罗箫
安宁
罗箫
1
山道崎岖,弯曲,盘旋,郝莉肩扛行李卷,手拎大包小包,趔趔趄趄下山。山半腰,道旁有棵核桃树,树上有对小鸟在啁啾鸣叫。郝莉停下,将东西放在核桃树下那块青石板上,掏手绢擦汗。
后面,章桐同样扛着行李卷,拎着大包小包走来。章桐上到山梁最高处,俯瞰山脚下梦绕魂牵的村庄,放声喊叫,喂!旮旯村,我回来啦!我回来啦!
郝莉惊喜地望向山梁,目光却被巨石阻隔。她双手捧成喇叭状,朝上面大喊,桐哥,是你吗?
我是章桐,你谁啊?
我是郝莉!郝——莉!
郝莉!我来啦!
章桐连颠带跑,经过一段陡坡,脚步收拢不住,差点栽倒。
郝莉远远望见章桐狼狈的样子,担心得直跺脚,小心点!跑啥嘛!
看见郝莉后,章桐不跑了,改做大步走,喘息声清晰可闻。郝莉一溜小碎步迎上去,接过章桐手里拎着的东西,二人说笑着来到核桃树下青石板前。
章桐撂下行李,直往郝莉跟前凑。郝莉往后撤,被岩石挡住退路。她伸出双手做推阻状,干嘛,干嘛你?你肩膀头上有鸟屎。章桐说。郝莉扭头,果然看到鸟屎。章桐替郝莉弹掉鸟屎。郝莉掐腰伸食指戳点上面,嗨!你俩咋不讲卫生啊!那对小鸟愣愣神,扑棱棱扇翅飞走。
章桐背负两卷行李,臂弯里挎着两人的大包小包,吃力地前行。郝莉轻松地甩着两手,戏谑章桐,你这是给自己找罪受,怨不得我哟?
我是男人,应该的。
郝莉撇撇嘴,充其量,你只是个小男人。
为啥?
没成家呗。
这不咱俩大学毕业了,该成家了。
你成你的家,干嘛拉扯我?
不拉扯你,我跟谁成家?
没听说过用这种方式求婚的,忒直接了吧,恋爱过程全省略了,让人猝不及防。
小时候你不是答应过,长大后嫁给我吗?
不算数!玩过家家那会儿,你九岁,我八岁,谁懂啥叫恋爱、结婚、成家过日子哟?
上大学这三年,你在东北,我在西南,假期都不回家,光顾打零工挣学杂费了,没法花前月下互诉衷肠,可在QQ里咱俩聊天不是挺投缘的嘛?
那不叫投缘,叫互诉烦恼,跟恋爱相差十万八千里。
每次聊天后,我都兴奋得睡不着觉,这叫啥?
这叫想入非非,神经病人都这样。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爱你,由来已久。
自说自话,活脱神经病人。
难道,你不爱我?
你应该先问我,喜不喜欢你。
对,喜欢是爱的基础,郝莉,你喜欢我吗?
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
不知道。
好嘛,一问三不知。不过,回家你就知道了,你娘已经答应咱俩的亲事了。
郝莉的眉头皱成了疙瘩。
章桐加快脚步,郝莉小跑着追上去。
桐哥,这事不能听家长的,得听我的。
当然,你不点头,我再怎么想也是空想。
那就好。眼下,我不想结婚,我得出去打工,挣钱给娘治病。
你娘什么病?
胃溃疡加腰椎间盘突出,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你家和我家一样没钱,不治好娘的病,我是不会结婚的。
是该出去打工。可是,我怕你变心。
变心?笑话,我同意过吗?
你没点头,所以可以爱上其他任何人,但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预约,如果我在你心里,与别人分量相等,希望你选择我。
中。
郝莉突然停下,蹲在那里呲牙咧嘴。
怎么啦?
崴脚了。
来,我背你下山。
不如你先把东西送回去,再来接我。
可太阳落山了呀!
郝莉指指绛红的西方,那不太阳还挂着哩?
好吧,我很快就回来接你。
太阳落山,鸟雀归林,章桐背着郝莉进村。郝莉突然泪流满面,大滴大滴落在章桐肩上。
郝莉,你哭了?为啥哭啊?
郝莉哽咽不止,我经常这样,突然就泪流满面,没有原因,又好像原因很多。
2
院子不大,院墙是用石块垒起来的,一个破旧的栅栏就是街门。两间低矮的石屋里,有个土炕,炉膛里火着得正旺,屋内却没有柴烟,柴烟通过山墙,飘飞到外面去了。
莉莉,脚还疼吗?
不疼了,娘你真行。
久病成医,娘崴脚次数多了,先是求人拿捏,后来自个儿就学会了。
抽空教教我呗。
那得等你再崴了脚。
为这,我也得去乱石堆里跑跑,再崴一次脚。
娘戳点郝莉眉心,大姑娘了,还跟小时候一样顽皮。哎,有件正事,桐桐爹娘托人撮合你和桐桐,我说等你回来再说。桐桐是我看着长大的,咱村就你俩是大学毕业生,依我说,就把婚事给定了吧。
不中,婚事定下章家又该催结婚了,我还小,过两年再说。
你都二十二岁了,娘在这年龄,你都绕院跑了。
我想出去打工,挣钱给您治病。
我的病不当紧,不耽误干活。
瞧您瘦的……爹走得早,您太辛苦了。
娘不辛苦,你才辛苦呢,一个女孩子,靠自己打零工挣书费学费生活费,硬是读完了大学,村里好多人竖大拇指呢。
打零工并不辛苦,跟玩似的。我就是想您,可东北离咱家太远,花不起路费。
没钱寸步难行啊!家里有两麻袋核桃,哪天你去县城卖了,好做你出门打工的盘缠。
明儿个我就去。
早七点,街上杳无人影。男人起早下地了,女人在家里忙着做饭,而那些孩子,大都贪睡,不到饭点是叫不醒的。这几年村里人口锐减,外出打工的人把老婆儿女乃至老爹老娘一股脑儿全带走了,这从鲜见的炊烟就能看出来,这儿一缕,哪儿一缕,零落,散淡,村庄因为空荡,显得异常安宁。
骡子车上装着两麻袋核桃,坐着章桐和郝莉两个人。章桐坐在左前边,手持一根拇指粗的树枝,不时扬起来,嗖嗖嗖抽打几下空气。郝莉坐在右边,脸朝外。骡子没有被柳枝的嗖嗖声所惊扰,走得不快不慢,蹄鼓哒哒哒哒清脆响亮。
郝莉,出村这么远了,没听见你说一句话,怎么啦?
我想出去打工。
去哪儿?
北京。
我也想去北京打工,咱俩结伴走呗。
我知道怎么走。
好歹是个照应嘛。
郝莉扭脸注视章桐,章桐正好也扭脸注视郝莉,触电似的,两人转头看向东方。太阳在山顶刚露出月牙似的一块,鲜红如熟透的西瓜瓤。
3
列车怪叫一声,喘着粗气停下,吐出一拨人,又吞进一大拨人,再怪叫一声,喘着粗气开走。
时值傍晚,车厢内尚未开灯,光线昏暗,章桐把自己的行李搁行李架上,转身接过郝莉的行李,举上去。一个愣头青撞了郝莉一下,章桐倏地捉住愣头青一只手,钱包掉地上,章桐捡起钱包,塞进腰内。
愣头青压低嗓音,算你狠!
章桐也压低嗓音,怎么,不服气?找地儿练练?
凭你?胎毛未掉,还想教训老子?
老子是校园拳击冠军。章桐勾拳亮势。
愣头青蔫了,灰溜溜去了另一节车厢。
邻座大嫂端详着章桐,不露声色。
列车员推着餐车走过来,卖盒饭啦!大米盒饭,五块一份!
许多旅客递钱买饭。郝莉舔舔嘴唇,脸扭向车窗。车窗外影影绰绰有村庄闪过,线杆一根接一根向后倒去。
郝莉,要不要买份盒饭?
太贵了。
飞机上的盒饭更贵。
据说,飞机上不卖盒饭。
为啥?
坐得起飞机的,都是些财大气粗的人,吃盒饭多丢份啊。
咱俩啥时能坐坐飞机就好啦。
钱多得花不完时,就坐一回飞机,证明脱贫了。可你没必要跟我一起坐,你是你,我是我,井水河水,互不相扰。
这会儿警惕性蛮高。
我一向警惕性特高。
方才你的警惕性哪儿去了?
方才咋啦?
章桐狡黠地微笑,没什么。
郝莉摸裤兜,面容失色,钱包!我的钱包不见了!呜呜……
泪腺咋这么旺盛,别哭了,没丢!
丢了!真的丢了耶!
在我这儿呢!章桐指指自己腹部。
郝莉声色俱厉,给我!没想到你这么坏!居然掏我钱包!
我没掏你钱包,真的!在你专心往行李架上塞提包那会儿,有个愣头青撞你一下,有印象吗?
好像,有人撞我。
你的钱包就是那会儿离开口袋的,幸亏我出手快,钱包才失而复得。
郝莉半信半疑。
邻座大嫂说,姑娘,我亲眼所见,钱包没丢。
给我!
不!
你想控制我?
是啊,你兜里空空如也,不得死缠死黏着我啊?
郝莉扑过来,伸手掏钱包。
别别别!钱包在裤衩口袋里面,你想非礼我啊!
郝莉满脸绯红,悻悻然坐回自己座位。
邻座大嫂窃笑。
郝莉,饿吗?
早饿了。
这就给你开饭。
章桐拿个搪瓷缸去接开水。回来后,从提包里摸出羹匙,又摸出一个塑料袋,解开塑料袋,往搪瓷缸里倒些黑糊糊的东西,用羹匙搅匀,递给郝莉。
什么呀这是?
我娘忙乎半天,面粉、花生米、精盐一一炒熟,把花生米捣碎,搅在一起,说这是油茶。你尝尝,看好喝不。
郝莉喝一小口,嘬嘬嘴,味道不错耶!
章桐又从提包里摸出四个煮鸡蛋,递给郝莉两个。
你娘对你真好。
对你更好,不是和你结伴,我娘至多给我摊几张小鏊子煎饼,绝对不会费劲巴力炒油茶,还煮鸡蛋。
4
清晨,雾霾黏稠,太阳出来了,浑浑噩噩,像个发霉的烧饼。那些楼房和车辆,包括匆忙蠕动的人群,都是那么陈旧,仿佛被镀上了一层古褐色。
这是西郊某某村,章桐兴致勃勃地介绍着。
郝莉面露疑惑,干嘛来这儿?太偏僻了。
我在QQ上问过网友,市内的房租忒高。
多高?
章桐伸出五指,在郝莉脸前晃晃,起码这个数,还是地下室。
郝莉吐吐舌头,老天儿,我只带二百。
郝莉见墙外有出租字样,走进去询问,大叔,你们这儿有房出租吗?
对不起,住满了。
为啥这么多人来这儿租房?
便宜呗,交通也方便,步行十几分钟就是地铁站。
二人往外走。
男房东追出来,哎!右拐第四家有空房!
谢谢大叔!
女房东问,一间房每月三百,你俩是合住还是分住?
郝莉甩个白眼,当然分住了。
章桐问,有没有一间房里有木板隔墙的?
还真有一间,走,我带你们看看。
女房东打开一扇门,屋里用粘合板隔成两个小得可怜的住室,安着两扇小门。
女房东说,前年秋末有对青年男女,非要隔开住。后来,俩人住一块了。再后来,结婚换大房子了。
章桐掩饰不住喜悦,手舞足蹈,抖肩晃脑,抿嘴直乐。
郝莉又甩个白眼,美得你!
章桐问,这两间鸽子窝每月租金多少?
四百。
我俩初次出门,手头紧,能不能便宜点?
那就三百八十吧,再不能低了。
章桐点钱,您数数,三百八十。
还得再拿七百六,我们这儿一向预收一个季度的租金。
我们没带那么多钱。
打电话让家里汇钱呗。
我们是从山里来的,家里没钱,带来的这点钱大半是借来的。
预交一个月的租金肯定不行,要不,你们再拿三百八十块,预交两个月的吧。
章桐又点出三百八十块,交给女房东。
二人在各自房间拾掇床铺。
郝莉说,谢谢你桐哥,不是跟你结伴,我就抓瞎了。
你呀,初生牛犊不怕虎,装二百块钱,就想来首都闯世界。
你咋带那么多钱?
我也没带多少,这不,还剩一百多块。
一百多块?俩人吃饭坐车的,忒紧了。
本来我只带四百,我爹怕你受委屈,夜里出去转几家,又凑三百。
又来了,钱我会还你的,人情债我可还不了。
爱还不还!
深夜,章桐辗转反侧,床板随着他身体的翻动咯吱咯吱响。
桐哥,你咋回事啊?
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挺累的,就是睡不着。
可能到了新地方,脑细胞活跃,导致失眠吧。更可能,跟这屋子里的气味有关。
气味怎么啦?
有点特别,你闻不出来吗?
我感冒,嗅觉失灵。
男女混杂的气味。
没正经!不理你了!
章桐起床去敲郝莉的门。
有话说呗,敲啥敲?
你有闲书吗?
有本 《故事会》。
中,开门给我,也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你把书当催眠剂了?
没办法啊。
章桐等啊等,门没有开。
郝莉,开门啊!
开啥开,书就在你脚边。
章桐低头一看,脚边门缝里果然有本 《故事会》。他重新躺下,看书。后来,灯开着,人已经睡熟,那本 《故事会》掉落在床前地上。
5
写字楼走道里鸦鹊无声,因为无人走动。房间里有人,透过玻璃窗,能清晰地看到人影晃动。
郝莉推开玻璃门,问一位埋头敲键盘的女士,你们这儿招工吗?
不招,正准备裁员呐。
我有大专文凭。
女士仍未抬头,如今有大专文凭的比麻雀还多。
数百米外有个场院,章桐被青年门卫拦住,你找谁?
找你们老总。
有预约吗?
没有,我想问问,你们这儿招不招工?
正好一辆奥迪车进门,一位胖子从车里钻出来。青年门卫喊住胖子,刘主任,咱们这儿招工吗?
刘主任看向这边,招啊,必须是学理科的,持研究生文凭。
章桐挠挠头,懊丧地离去。
郝莉对面坐着一位中年男士。
我们是个小公司,只招熟手,就是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的,不好意思。
我会尽快适应的。
我说过了,我们这儿不招学徒工。好了,我还有事。
日薄西山,章桐口干舌燥,站在一个冷饮摊前,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钱,转个念,把钱又塞进口袋。他走进公共厕所,拧开水龙头,弯腰侧脸喝水,之后进去方便。
郝莉从女厕所出来,拧开水龙头喝一通冷水,洗脸,擦脸,匆忙去地铁站。
章桐走进地铁站。
桐哥!我在这儿!
郝莉!你早来啦?
刚到,不是说好六点整在这儿碰头吗?
咋样儿?
没人要。
没关系,我要。
瞧那狼狈相,居然还笑得出来?
中午吃东西没?
让气给灌饱了,山珍海味也吃不下。
我买了几包方便面,回去泡给你吃。
老吃方便面,再就是油茶泡馒头,都吃烦了。
章桐苦笑,我也是。
6
又逢雾霾,天与地一派混沌。
郝莉问,今儿去哪儿?
朝阳区。
昨天不是去过了吗?
正因为去过,所以要再去一趟。
为啥?
那儿有家酒楼,勤杂工请假,周老板说可以替工半月,一天三十块,我说考虑考虑。
替工半月,那不耽误正事吗?
听人说,有一年多找不到工作的。兜里的钱有减无增,顾嘴要紧啊!
从地铁站出来再步行半个多小时,他俩来到某酒楼。
章桐说,周老板,替工的活儿,我做。
好,洗涮间忙去吧。
好咧!周老板,这位是我同村老乡,能给她安个活儿么?
周老板仔细打量郝莉一番,问道,你会唱歌跳舞吗?
会唱歌,没学过跳舞。
跳舞好学,客人带你几次就会了。
章桐面露疑惑,周老板,你想让她当坐台小姐?
别紧张,只是陪喝酒吃饭,我们这儿的陪酒小姐来去自由,二楼雅间里有音响设备,客人酒足饭饱,难免要唱歌跳舞啥的,陪一个小时二十块,饭店不抽钱。姑娘,做不做,给个痛快话儿?
郝莉眼睛发绿,我做!
中午,二楼走廊长条椅上坐着五位小姐,有四位陆续被熟客人叫走。郝莉局促不安之际,周老板走了过来。
你该简单化化妆,衣服穿得也太严实了。
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我……做不到。
多想想利害关系,就做到了。
一位大胡子摄影师和一位披肩发画家结伴走过来。
大胡子摄影师问,老板,有陪酒小姐吗?
有,您看她行吗?周老板指指郝莉。
大胡子摄影师说,是个长头发的就中!
披肩发画家逗趣道,我头发不够长吗?
噢,忘记加定语了,女的,秀色可餐嘛。
周老板走近郝莉,小郝,饿了吧?陪他们吃饭去。
老板,他俩那模样,怪吓人的。
人不能貌相,再说了,雅间门口有服务生,出不了事的。
三人走进雅间落座。大胡子摄影师问,姑娘,看你像个大学生,怎么干这个?
我大学毕业出来打工,没人要,钱快花光了,只好打零工。
噢,灰姑娘一个。能喝酒吗?
郝莉摇头。
会跳舞吗?
郝莉摇头,我给你们唱首歌吧。
好啊,等你一首歌唱罢,菜也该上来了。
郝莉打开音响,放 《青藏高原》音乐,然后放声歌唱: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呀啦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呀啦索,那就是青藏高原。
二人拍手叫好。披肩发画家说,嗓门挺高的,音质也好,就像丫蛋在唱。
郝莉自鸣得意地说,我的高嗓门是在老家山里练出来的。
披肩发画家说,我老家也在山区。
大胡子摄影师说,姑娘,他是画家,山区景色是他不变的主题。
画家?那他一定是个大画家。
为什么?
奇发怪装,青年时期也许是出洋相,成年时期却是气质的一部分。
披肩发画家说,谢谢你的理解。我怎么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知音的味道呢?
大胡子摄影师说,姑娘,下午我俩要去郊外逛逛,你能陪我们去吗?
郝莉有点为难。
按钟点开你钱,这家伙有的是钱,预定他一幅画,得交这个数。大胡子摄影师伸出三个手指。
三百?
加个零。
夜晚的景色很美,远处近处的霓虹灯不仅闪闪烁烁,还滴溜溜旋转,让人眼花缭乱。音像店里飘出的歌声,有柔婉,有雷暴,动人心弦,震撼耳鼓。
章桐在大门外徘徊许久,不见郝莉回来。他去小卖部买了盒老仁义香烟,撕开口,弹一支,点着,只抽一口,就大声咳嗽起来。再抽,再咳嗽,咳嗽得直打哆嗦。郝莉突然出现在章桐背后。
桐哥,你咋抽上烟了?
姑奶奶,可回来啦!你去哪儿啦?
八达岭。
跟谁去的?
一位画家,一位摄影师。
你跟他们熟?
当然熟了,中午我陪他俩吃饭来着。
吃顿饭就熟人了?憨不憨呀!你就不怕被人贩子拐走?
我看他俩不像人贩子。
知道不,周老板急坏了。
我告诉过周老板的。
我跟他要人,差点打架。
你咋这样?我好我赖,跟你有关系吗?
你是我……带出来的。
你就二百五吧你。给你钱,我去睡了!
章桐捏着两张领袖大钞,愁眉不展。
7
临近中午,酒楼顾客渐多,越来越多。服务生来去生风。周老板乐得眉眼儿里都是笑。章桐恨不得再生一双手,把堆积如山的碗盘碟子麻利洗净。
一位丰腴、端庄但不失美丽的女士走进洗涮间,问,有干净毛巾吗?
有,怎么啦?
袖口这儿有菜汁。
这块湿毛巾是刚洗干净的,我帮你擦。章桐细心地擦拭。
谢谢你小伙子。哎,你人高马大的,咋在这儿洗盘子?
章桐不好意思地笑笑,找不到工作,当几天替工。
学过武术吗?
章桐摇头,没学过,不过,我练过拳击,获得过校园拳击冠军。
女士点头表示相信,我那儿有份工作,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做。
章桐精神一振,什么工作?
保镖。
你看我适合吗?
没啥不适合的,我去哪儿你跟哪儿就得。
我做!
第一个月是试用期,月薪一千五。
中!
那好,这就跟我走。
这就走?
你不就是个替工吗?咋,舍不得眼下的工作?
不是,我得告诉周老板一声。
你快点,我赶时间,得去银行提笔款子。
章桐来到二楼,周老板,有个老总雇我做保镖,您看……
好啊!做去呗。
那,洗刷这活儿……
小郝,你去洗刷间,有客人我再喊你过来。
郝莉捣章桐一拳,桐哥,运气不赖呀!守株待兔,还真他妈有兔子往树上撞!
将近子夜,音像店早打烊关门了。大街两旁的霓虹灯也不再旋转,和许多房间一样,熄灯闭眼沉睡,微风轻轻吹,仿佛有人在打呼噜。
章桐推门进屋。郝莉从自己小屋出来,二人在狭小的空间面对面站立。
郝莉,还没睡?
你不回来,我睡不着。
挺在乎我的嘛。
我怕你被老虎吃掉。
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没有老虎。
章桐走进自己小屋,郝莉跟进来。
也不让坐?
请坐。
我怎么觉着,你那位女老总挺厉害的,厉害得想吃人。
哪儿啊,佟总挺慈善的,这不,还给我配部手机。
山寨版的。
管他呢,能通话就中。
刚上班就给你配手机,她啥用意?
我不是保镖吗?召之即来呗。
我给老家打个电话中吗?
打呗。
打不成,我不知道小卖部电话号码。
我知道。章桐翻电话号码本。
算了,太晚了,明儿个打吧。你咋回来这么晚?
佟总跟人吃饭喝酒聊大天,我得陪着。
佟总洗澡,你也陪着?
不用,佟总进家门,我就下班了。
8
端盘子的女服务生往来穿梭,走道显得窄小许多,大胡子摄影师和披肩发画家只得靠边走,畏畏缩缩的。周老板迎过来,二位,要陪酒小姐吗?
大胡子摄影师说,要!
一位?两位?
披肩发画家说,一位,就那姓郝的。
周老板出门。
大胡子摄影师说,老弟,该不会恋上了吧?
怎么会,董倩虽然留学国外,我也是有妇之夫呀,得守住自己。
六零后观念,传统,不失可爱。
我七零后,观念不超前,也不落后,严正好。
当下这类事,不叫偷,叫周瑜打黄盖,你情我愿。
新鲜。
有钱能使鬼推磨呗。
周老板来到洗刷间。郝莉正在忙碌。
小郝,有客人点名要你去。
我没有熟客。
大胡子和披肩发。
噢。郝莉擦手。
小郝,你不能跟人出去。你要跟人出去,就别在这儿干了。
为啥?
我怕章桐找我闹事。
他凭啥管我?
他说,你是他的人。
郝莉把毛巾嗖一下甩到木架上,甭听他瞎掰扯!
大街上堵车了。一位司机酒驾,连挂三辆车,最后撞在护栏上,车才停下。车头凹陷,车身横趴,仅几分钟,就堵停百余辆车。
章桐正在看热闹,突然瞥见郝莉咯噔咯噔踩着棕紫色高跟鞋扭扭搭搭走过来。
回来了?
不是人,别跟我说话!
不理我行,可你娘等着跟你说话呐。
啥?你给我娘打电话了?
昨晚你不是说要给你娘打电话吗?我让老歪叔把你娘叫到小卖部了。打不?
当然打了。
章桐按号码,摁通话键,把手机递给郝莉。
郝莉开口前先揉了揉眼睛,娘,您身体好吗?过段时间我就给您汇钱,一定要买药吃,不能断药!谁说我乱跑了?我没乱跑,真的,您放心,我是那么好糊弄的?有主儿?哎呀娘您说啥呢,不沾边的事,村里人爱嚼舌头,随他们嚼去!
郝莉气愤地把手机扔过去,章桐猝不及防,没接住,手机啪一下掉在地上。他拾起手机,心疼地打开查看,外壳没摔坏,但他不放心,摁了重拨键。
喂,老歪叔吗?我是桐桐,麻烦您告诉我爹,让他明儿个晚饭后到你那儿等电话。
章桐关掉手机,去那屋找郝莉,却推不开门。
郝莉,开门,我有话跟你说。
再烦人,我就搬别处住了!
9
窗外,暮色渐深。窗内,灯光明亮,杯盘狼藉。偌大的餐桌两旁,只有披肩发画家和郝莉两个人。
郝莉,我想请你去我画室坐坐。
我没时间。
怎么会没时间,吃罢饭你不就没事了吗?
十点前我必须回到旅馆,有个同村老乡跟我住同一家旅馆,昨晚回去晚了,他竟然给我娘打电话告状。
那咱抓紧时间吃饭,然后去我画室,我有车,十点前铁定送你回到旅馆。
披肩发画家开车,郝莉坐在后座,远远望见章桐正在路边徘徊。
郝莉说,停车!车停下来,郝莉犹豫着没有下车。她说,不能在这儿下车,会被他逮个正着。
披肩发画家说,开过去拐个弯,他就发现不了。
大画家真聪明。
郝莉闪进院内,很快又走出来。章桐仍在百米外路边徘徊。郝莉蹑手蹑脚走近章桐。章桐听得身后有动静,猛回头,吓一跳。
你个鬼,打哪儿钻出来的?
出租屋呀。
你啥时回来的?
个把小时前我就回来了。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月亮从东边出来了!
我咋没看见你?
我也没看见你。
月亮好圆好亮,像个银盘子,在东面旋转。
傍晚,披肩发画家正在自家厨房做菜,边翻炒边问,郝莉,你会做菜吗?
郝莉由于看画太专注,没听到问话。
郝莉,你在做什么?
哦,我在欣赏你的大作,你这幅 《秋山》,是昨天我见到的那幅吗?
是啊,我修改了一下,你不是说你家山坡上那棵核桃树下有块青石板吗?
太像了,就像回到了家乡。
客厅餐桌上摆着几样菜。披肩发画家端来一盆甜玉米羹。
郝莉,尝尝,看合口不?
郝莉一样尝一口,哇!你厨艺超棒,为啥老去酒楼吃饭?
你猜。
猜不到。
爱屋及乌,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吗?
当然知道了。
鬼迷心窍,这个词也不难理解。
有一点,我不理解。
哪一点?
好多有钱人,怎么一个个跟病秧子似的,见色眼开?
包括我吗?
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
你有老婆吗?
有哇,她出国留学,再有两年就回来了。
你这人还算诚实。这么多菜,咱俩吃得了吗?
待会儿有个朋友要来。
男的女的?
男的,是位老总,请他来,是为给你找工作。
真的?
你不能老当陪酒小姐,我请你作陪都有些不忍心。
敲门声响起,披肩发画家前去开门。英俊潇洒的吕总进门,在餐桌旁大咧咧落座。
大画家,这你表妹?
噢,郝莉,大学刚毕业。郝莉,这是吕总。
看着还养眼,明儿个去我那儿报到吧。
你看她适合做啥工作?
当秘书。
让她做其他活儿呗。
我那儿正好缺个秘书。
郝莉给吕总斟酒,我刚出校门,啥也不懂,希望吕总多多点拨。
点拨是肯定的,哪位当头头儿的也不容属下碌碌无为。
章桐在院门外徘徊,见郝莉回来了,却扭扭脸,装作没看见。
桐哥,这么晚了,还没睡?
我搁这儿看大门呢。
房东不在?
在,早睡了。
郝莉往里走,章桐插街门,回自己小屋,插门。
郝莉敲门,桐哥,我给你带了吃的。
没胃口。
新疆风干牛肉,还有瓶酒,北京牛栏山二锅头。
章桐麻利开门,接过袋装风干牛肉和酒瓶,又要插门。郝莉倏地从章桐胳肢窝里钻进去。
我回来晚是有原因的。
哪回也有原因,哪回都是很晚才回来。
今儿情况特殊,我找到工作了!
真的假的?
郝莉得意地微笑,假的。
章桐凝视郝莉几秒钟,我怎么觉得,是真的。
这说明,你察言观色的功夫大有长进。
谁帮你找到工作的?
大画家。
你该不会,去他那儿当模特吧?
不去他那儿,是去他朋友那儿,一位姓吕的老总要我明天去他公司报到。
太好了!往后你能照时照点回来啦。
这就是你的贺词?
再补充半句,我能睡安生了。
这么说,你之前没睡过安生觉?
你不回来,我心里猫抓油煎似的,睡不着。
咸吃萝卜淡操心,我不好好的吗?
我怕你变心,不是,怕你的心变色。
又来了又来了,树老根多,合着你也老了?废话咋那么多?
唉!我觉得,自己快七老八十了。
10
章桐在这边徘徊,郝莉在那边下车。吕总将车掉头,一溜烟离去。
章桐走过来,黑着脸问,谁送你回来的?
我这不是自己走回来的吗?
你只走了百来米,那辆车是谁的?
吕总送我回来的。
老总送你回家,派头挺大嘛。
我是吕总的秘书,陪客户吃饭是份内工作。本来我要坐地铁回来,吕总说他家也在西郊,顺路。
二人走进租屋。
郝莉,给你个手机。
买的?你开支了?
不是,一个同事换新手机了,要扔掉这个,我说我帮你扔吧,就揣回来了。手机卡是我新买的。
郝莉一脸不悦,女式的?
你跟女人有仇啊?
你跟她……
爱用不用!
章桐夺回手机,塞兜里。
郝莉强行从章桐衣兜里掏出那个女式手机,摁键,章桐搁在枕头旁的手机响了。
郝莉抓过章桐的手机,看来电显示,面露喜色,后面三位数字真好,我要发啦!
郝莉在唱 《童年》: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唧唧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吕总和张总绕着郝莉翩翩起舞。
吕总和张总碰杯喝酒。郝莉去了洗手间。
吕总,你这马子,比先前那个靓丽好多耶。
不要乱说好不好,小郝是我新招的秘书。
先当秘书,然后小蜜,水到渠成嘛。
小郝太单纯……
不忍下手是不是?那我可要加塞了。
你浑啊?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狐狸露尾巴了吧?罚酒三杯!
洗手间里,郝莉在打手机。
大画家,谢谢你。
郝莉,你有手机了?吕总给买的?
不是,拣别人的旧手机。
十多天不联系,以为你失踪了。
这儿吧,饭局忒多,有客户得作陪,没客户得陪吕总吃饭,几个女同事对我横眉冷对,就差吐唾沫了。
这说明,你还是你。
我当然是我了,你在说什么呀?
我的意思是,你依然故你,朴素,纯真。
入夜,披肩发画家在QQ上跟人聊天。
你好?
你好?
我很好,你有危机。
危机?能说具体点吗?
有个事,我想告诉你……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为你是我好友,也为我自身的良知。
11
佟总办公室外有几位年轻男女正在电脑前忙碌。章桐坐在电脑前,浏览网页。一位女秘书从佟总办公室走出来。
章桐,佟总叫你。
章桐走进佟总办公室,佟总,有事?
你开过车吗?
开过,不是很熟练,但我有驾照。
太好了!这不,每天得跑邮局送邮包,所以,我买了一辆商务车,既然你有驾照,那就由你当司机了。另外,我外出时,你就为我开车,两不耽搁。
佟总递给章桐车钥匙,郑重其事地说,眼下有件事,需要你去办,也好趁机练车。她又递给章桐一张照片和一页纸,这个人,你给盯梢一下,这是照片,车牌号,还有工作地点。每天下午下班前你去他公司楼下蹲守,查清他的去向。
他谁啊?
不瞒你,我老公最近旧病复发,晚上总是很晚才回家,问他,总说在开会加班,哪儿有啊,公司里黑着灯,咋开会加班?一到傍晚就关机,不信我就没法治他了。噢,带上这个相机,拍几张证据给我。
郝莉在大门外徘徊。章桐开着商务车过来,在郝莉身旁停下。章桐下车。郝莉惊喜地大叫。
哇噻!桐哥,你开上车了?
对不起,之前没告诉你,驾照在我大学毕业前就办了。
郝莉这儿摸摸,那儿摸摸,探头往里张望,这车是佟总配给你的?
不是配给我的,是每天跑邮局的专用车,这几天我有特殊任务,离开车不行,佟总特批我车随人走。
特殊任务?能透漏一二吗?
佟总交代过,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章桐将面包车开进院内。
女房东说,这车停院里要收费的。
章桐大咧咧地说,收呗,公司给报销。
天刚亮,章桐就咋呼起来。
郝莉,该起床了。
你走你的,喊我做啥?
捎走你呗。
真难听,都是捎东西,哪有捎人的。
行车路上,郝莉说,啥时能有自己的车就好啦。
核桃树有了,核桃也会有的。
我到了,靠边停车。
章桐把车停在写字大楼前,说,我想上去看看。
你不上班啊?
浏览一下就走。
你这人真黏糊,不利索。
二人进电梯,出电梯。
那边就是我们河源文化传播公司。
我瞭一眼就走。
章桐隔着玻璃窗往里看,见吕总正在翻看文件。郝莉在总经理室门外一个小隔间坐着,一脸不忿,似乎在跟那几个不爱搭理她的女同事怄气。大厅里有十多张电脑桌,每台电脑前都有人在忙碌。
郝莉拿块抹布,进到总经理室,擦抹真皮沙发。她直起腰面向窗外,只看到正往电梯方向走去的章桐的后背。
将近十点,章桐走进天网购销有限公司。
佟总,我迟到了。
为啥迟到这么长时间?
我去踩点了。
噢,你应该打电话告诉我。
那会儿不方便打。
十一点多,章桐在邮局门外打手机。
喂,佟总,那些邮包发走了,我想顺路去看望一位老乡。
章桐在车内打手机。
郝莉,我在你楼下。
有事吗?
我开支了,中午搓一顿呗。
好哇!你等着,我快下班了。
郝莉正在装订刚刚打印出来的文件,吕总走过来,郝莉,中午跟我出去吃个饭。
对不起吕总,一个老乡约我了。
不能推掉吗?
啊?能,能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吕总给郝莉开车门,扶郝莉在副驾驶座上坐好,然后转到这边开车门,坐驾驶座上,发车,驱动,驶出大门。
章桐开着商务车,随后出门。
凤凰酒家一楼靠窗餐桌,吕总和郝莉面对面吃喝说笑。
外面不远处,章桐发车,驱动,一溜烟离去。
吕总捉住郝莉的手,郝莉挣两下,没挣脱。
这儿太乱,恁多眼睛看着呐。
吕总松手,下次换个僻静地方。
下午两点多,章桐说,佟总,我有个亲戚,想来北京打工,您熟人多,能给找个事做吗?
我妹妹那儿正在招人,我跟她说一声,应该能成。
拜托您了。
小章,那件事有进展吗?
正要跟您汇报呢,确实有情况,可惜,没留下照片,胶卷跑光了。
再买个胶卷呗,一定要留下证据。
有照片又能怎样?我觉得,不如……
你有好主意?说出来听听。
12
章桐对郝莉说,我爹来电话了,说你娘吃饭正常,椎间盘突出也大有好转。
不治而愈?怎么会?
医生说幸亏及时住院,真要再拖延下去的话,有可能发展成胃癌。
我还没给娘汇钱呢,她哪儿来的钱住院?
前段时间吧,你娘水米不进,起不了床了,我爹一咬牙,把骡子买掉,送你娘去了县医院。
骡子没了,你爹咋给人拉脚啊?
骡子没了可以买,人没了,多少钱也买不回来。我爹说,你家的几亩地他给代种,你娘最好来北京常住,这样,你就少了牵挂。
谢谢,你们全家都是好人,呜呜……
哭什么嘛。
我愿意哭,呜呜呜呜呜……
次日上午,吕总说,郝莉,你陪我去趟合肥,十点钟出发。
啥时回来?
没一定。
哦,好吧。
郝莉去外边打手机,桐哥,五分钟后你给我打手机,说几句闲话就中。
你啥意思啊?
别问了,没意思。
郝莉刚走进吕总办公室,她的手机就唱起了常回家看看那首歌。
喂!桐哥,有事吗?啥?哦,我知道了。
郝莉关掉手机,满怀歉意地说,吕总,我娘坐火车来京,下午四点一刻到站,您看……
吕总脸拉老长,摆摆手,一言不发,出门了。
13
总是这样,天刚亮,章桐就悄没声儿起来,轻手轻脚出门,去买早餐。回来才叫郝莉起床。
郝莉,快八点了,还睡,猪啊。
你才猪呢!哎呀!难得周六睡个囫囵觉,被你搅了。
咱去颐和园转转呗。
好呀!那些生地方,我得挨个儿转熟了。
二人正在颐和园转悠,郝莉的手机响了。她走开几步,接手机。
喂,吕总你好?我想转几个景点。啥?有重要事情?电话里不能说吗?那……好吧。
从公交车下来,走十几分钟,就到了凤凰酒家门外。手机响了,郝莉想接手机,见章桐探头探脑,索性把来电掐断了。她跺跺高跟鞋,我有正事,你别特务好不好?
不好。
知道不干胶是什么样子吗?
我这样子呗。
手机又响了,郝莉摁接听键,我姓郝,你谁啊?
章桐叼着烟卷在附近徘徊,眼望这边。
凤凰酒家一楼大厅里座无虚席,猜拳声磨牙斗嘴声熙攘杂乱。二楼没那么吵,那些食客的动静全被雅间的软包门封闭住了。三楼更为幽静,走道里连服务生也不见一个,似乎所有房间里都没有人,只有吕总独自一人坐在中厅沙发上,眼睛盯着楼道口。郝莉神色凝重地走过来,在吕总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
郝莉,咋才来?
对不起,遇到个特殊情况。
我已经开好房了,咱进去吧。
有事就在这儿说呗,干嘛开房?
你不是嫌下边乱吗?
下边是挺乱的,可一男一女呆在一间屋子里,更乱,指不定出啥乱子呢。
不就那么点事么?
就那么点事?你说得忒轻飘了吧?跟约我吃饭一样轻飘。
不是,我是爱你的。
有个词叫大爱无疆,很适合你。
啥意思?
你有老婆,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也没问啊。
方才你老婆打电话恐吓我,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想过。
放心,早晚我会跟她分手。
早晚?晚三十年,我年过半百了。
你不放心的话,我可以先给你买房,买车。
我想要安宁,你买得来吗?其实,我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有人在彩印厂给我联系到一份工作,月薪没这里高,可我愿意去!拜拜!
吕总起身挡住郝莉去路……突然,他从对面那块大水银镜里看见老婆怒气冲冲而来,于是赶紧换作送客的姿势,郝莉你……你请便。
吕总的老婆就是佟总,是章桐把郝莉的手机号码告诉她的。郝莉不认识佟总,却把约会地点透漏给了她。
郝莉从旋转门这边出来,那边进去一位大腹便便戴墨镜的中年男士,臂弯里揽着的一位浓抹艳妆的姑娘,也戴着墨镜。
章桐正坐在台阶上仰头看天。天空海水一样湛蓝,一架飞机无声划过,留下长长一股白烟。正午璀璨的阳光,直晃人眼睛。
罗俊士 笔名罗箫,河北省作协会员。曾出版诗集两本,有中篇小说、小小说、诗歌与散文多次获奖,诗歌曾连续数年入选 《中国诗歌精选》和 《文学中国》,在 《特区文学》、《章回小说》、《滇池》、《雨花》、《湖南文学》、《延河》等百余家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百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