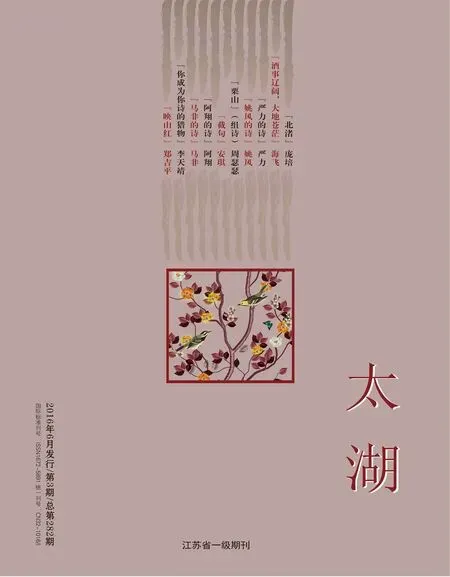如果你还在,该有多好
黄园佳
如果你还在,该有多好
黄园佳
每当日落,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位背着大号提篮的老妪,直起腰立住脚稍喘口气的画面,也因有感于一句歌词 “残破的书记不下一个个红颜”,我提起笔,决定写写我的奶奶。
在我们的方言中,我称她 “亲娘”(谐音)。普通话里的 “奶奶”很难用方言发音,如若直接说普通话,又显得矫情。不过有时,我会调皮地用普通话叫她 “阿奶”,不会说普通话的她听了之后很高兴。
她瘦高,直不起背。尽管生活中多有挫折困难,但她始终都保持了单纯的个性。说话爽直、没有心机、不谙人情世故贯穿她人生的始终,能豁然于现实又难免体会辛酸。然而,在我记忆中,她总是笑眯眯的。
奶奶出生于一九三八年,本姓费。姑姑说,奶奶的外公家姓郁,算是中农。奶奶的母亲是家中独女,可惜等奶奶长到七岁左右,她就病逝了。关于母亲,奶奶讲过一个片段:幼弟荷青 (谐音)才一岁多,她的母亲就得了重病。幼子在一旁哭闹要喝奶,瘦削不堪的女人常无力地将幼子推开。没过多久,奶奶失去了母亲。丧礼上,人们按习俗安排这一双儿女走在仪仗前头送亡灵,炮仗轰隆,唢呐锣鼓声响连天,放置在箩筐中担着的幼子被活活吓死了。之后,奶奶的父亲续娶,给她添了几个弟妹。
讲起童年,她用 “开心”二字形容。开春后,每到例定的商贩集聚日,她就踮起脚尖,将手伸进生母遗下的皮箱里,抓出一把铜板,然后兴高采烈地跑去逛游。因为有吃的,一帮小姑娘簇拥着她。
奶奶的外婆失去了丈夫,继而又失去了独生女儿和外孙,守着空旷的家,终究在寂寞孤苦中熬了过来。在她最后的生命里,一定给了奶奶难能可贵的关怀和照顾。奶奶说,每次住在外婆家,清早起来,习惯动作就是把手伸进枕头底下,因为那里一定有一包盐煮花生。那是她外婆清早上街买菜带回来给她的,其他人都没得尝!陪伴她一生的龋齿怕就是这么来的。
家里人丁众多,又遇上荒年,家境每况愈下,奶奶的父亲想到了亡妻的妆奁。在前岳母的再三阻挠下,首饰才不至于被全部当掉。提起父亲,奶奶怀着感恩的心,说他是家里的顶梁柱。至于继母,对她持有敬重。荒年,大米稀贵,继母只能将糠麸之类与少许大米混着一起煮。糠麸比大米轻,煮熟后自然全浮在上层。继母就将上层的全分与子女和自己,而将底下的大米饭全留给出体力养家的丈夫。
继母,也被称作 “晚娘”,是一个令人戒备的称呼。在我两三岁的时候,那位太婆婆还来过我家几次。印象中,她着一身陈旧的黑色,梳两条长辫 (想来是保持了一生的发型),给人一种硬朗和利索的感觉。后来我问奶奶:“晚娘对你好吗?”她说:“当然好的。”我不信:“是对舅公姨婆他们一样的好吗?”她笑着说:“有一点区别吧。”她十几岁就跟着父亲农忙担稻麦。稻麦多,忙不过来,她心劲强,为省来回趟数,她担的和男人一样的分量。她的父亲给她一捆一捆往肩上摞,她非要等到直不起腰了才喊停。年老后,她再也不能如年轻时候一样直挺着背走路了。
说起奶奶的自豪,第一件事要数小学四年级期末考试考了全镇第一,只可惜之后她没有再上学。第二件事便是爷爷选择了她做妻子。
爷爷比她年长一岁,是个有口碑的手艺匠,而外形上,完全是江南男子的清俊之貌。爷爷本有指腹为婚的对象,对方家境颇丰,只是天生黄发黄牙,两人凑机会联络感情,又话不投机半句多。最终,爷爷宁舍聘金,选择了清贫普通的奶奶。
那是一段被劳作掩埋的岁月吧。为生计,即便被倒扣工分,爷爷还是决定外出做手艺活,等我父亲长到十三岁时,便也跟着爷爷出去谋生了。而田地里的活儿,整个儿落到了身为女性的奶奶身上。奶奶手笨,不会做鞋,灵巧的大姑姑在十多岁时就坐在煤油灯下,挑起了给全家人做鞋的担子,为奶奶分忧。
爷爷说,他还不会骑自行车的时候,常常要走五六个小时外出打工,一星期回来一次,到家的时候,已是午夜十二点。他经过窗户推门进来,就看见奶奶就着月光纺纱的身影。
奶奶说,有一次,爷爷从六十里开外的地方回家来,走到半路觉得热,就把新买的外套脱下披在肩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狭窄的土路两边树木参差,路上仅他一人,不禁有些胆寒,听觉也跟着灵敏起来。猛不丁,耳边传来呲呲的声响,走得越急,声音还越大,仿佛有脚跟着。爷爷大惊,奔跑良久,终于将那声音甩丢去。等回到家里,奶奶奇怪不见外套,爷爷这才回过神,发现他庆幸甩掉的声音竟就是搭在肩上的外套摩擦身上衬衫时发出的声响。天微亮,他照原路返回细细寻找,没能找到。
父亲永远忘不掉奶奶打了二斤六两油,在回家路上被蔓草绊了一跤的事情。一大半油撒进了稻田旁的水沟里。那是一家人准备食用一整年的油。于是奶奶蹲在水沟下游,将漂浮水上的油一点一点捞回瓶中,硬是灌了一瓶,硬是一家人食用了一年。
我无法思量那双淳朴的眼睛里是否盈满泪水,无法想象那双粗糙的手会是怎样的颤抖。但可以确信,在艰苦的岁月里,一家人不离不弃相互安慰的温暖足以抵挡无尽的失落与挫折,纵然朴素在现实面前显得单薄,但良善守得住眷顾。时过境迁后,恰恰是这些平凡,化作记忆中珍贵的宝石。
我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奶奶溘然离世,令亲人猝不及防。
父亲在电话中极尽可能地表现平静,要我别多难过。我木然点头,仅能用只字应答,忽而不知 “难过”为何物。晚间休息,竟木然睡去,天蒙蒙亮时,又木然爬起。
当时的我,晕车症状严重。怕吃多了引起呕吐,仅买了两个茶叶蛋作为早餐。我徒步十多分钟到校门口搭公车,花费大概一个半小时到达火车站,之后又花费一个半小时,火车到站。走出火车车厢的时候,我依然捧着塑料袋,边走边吐。等走出火车站,寻到一处座椅坐下,我已委靡无力。
兜兜转转,虚耗半日,最终由父亲接引回到家中,我疲乏得近于昏迷,眼皮简直像要胶着到一处。按照仪式,姑姑们用沙哑疲惫的嗓子向作为吊唁者的我哀哭片刻。我茫然站在灵前,望着一地秸秆,满室凄然,从未有此刻这般深刻的明了跟随尖冷的风,嘲弄似的在我周身游转。我闭上眼,直想遁逃。
母亲吃了一惊,赶紧过来提醒我:该给奶奶磕头。
于是我顺从而麻木地下跪、磕头,直到目光触及端放着的相片上那张温慈而清苦一生的脸,胸中陡然一恸,震彻心肺的悲戚嚎啕而出,难收难止。我无意识念叨着的 “你为什么不等我”、隔壁男性亲属的吸鼻叹息声、还有整栋楼房的沉闷枯寂,尽数融合成为我年轻生命中难以磨灭的印记。
你为什么不等我?
等我什么呢?
我说不出口。
我的奶奶,虽然不善言辞,但的的确确是个可以把爱全部奉献给亲人且毫不顾惜自己的女性。
当我用二八自行车练习骑行,不慎被车把杵到肋骨,摔倒在地疼得出不来气时,正在河中央采菱角的奶奶,竟能在极短极短的时间内靠岸,弯着腰跑到我身边帮我顺气。她根本不曾想过自己不会游泳,更不会考虑到靠岸过程中如若不慎落水的后果。
当我和弟弟被臭名昭著的恶狗追咬,她可以不顾一切地冲出来,把我们挡在身后,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用护卫子孙的大无畏气势硬生生将恶狗逼退。
曾有几个寒冬夜,雾霾厚重异常,即便路灯当头照,行人亦因难辨方向而胆颤心惊。当老式座钟的钟摆敲过了十一下,而外出接我母亲下班的父亲依旧未归时,听过枪声、喧嚷的奶奶再也睡不着,顾不得仔细穿衣,仅披了件棉袄就出了家门,一直一直地在离家几百米的三岔路口徘徊,听到车铃声就试着呼唤我父亲的小名。即便身体被冻得近于麻木,等待的焦灼迫使她不见到我父亲决不回家!
就是这样一位长辈,一位深爱着我们的女性,我希望她等我,等我长大,等我有能力回报她。十几岁时,我就知道,她害怕彗星,害怕阎王,更害怕瘫倒在床拖累他人。我曾稚嫩地安慰她:“等我长大,我会照顾你,而且还会花钱请人照顾你。”她宽慰地笑了,同时也失落着:“就怕等不到啊。”
孰料竟然就这样一语成谶!
她的生命戛然而止。
于是乎,每当我看到价格实惠又适合她的衣服、访到优秀的牙医师、习得一些按压穴位以缓解疼痛症状的方法、邂逅在孙女陪伴下逛游超市的华发老人,无计回报的遗憾尽数化做成了焦灼的痛苦:如果你还在,该有多好!
有人说,如果逝者能够出现在梦中,说明并未真正远离。奶奶过世后的三四年间,我曾于节假日前夕梦见她数次。她在她的小厨房里忙着做菜,肴馔之丰富,一如当年,甚至有一次,我还帮她到屋后竹林中采摘南瓜大小的茄子。
而如今,我已长久长久不曾梦见她,不由得在心底默默祈祷:
如果真有来生,但愿她能拥有福慧双全的全新人生;
如果真有轮回,但愿终有一日,我依然能投入她的臂弯,做一名不会要她 “等”的子孙。
个人简介:
黄园佳 1989年生人,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2011年6月毕业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对外汉语 (汉英双语方向)专业,现为公司职员。相信文如其人,把写作视为心灵之田,静心自省、思考、探索,细细耕耘,期待在不断的创作中收获成熟优雅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