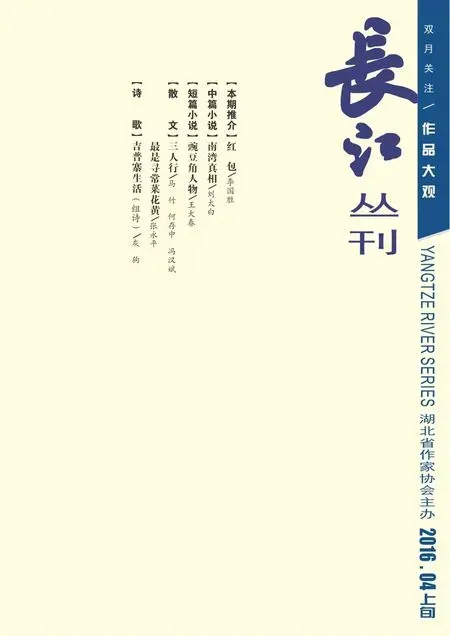最难得活成一个孩子
谢络绎
最难得活成一个孩子
谢络绎
第一次见王新民是在2011年,夏天,我刚刚加入武汉作协,与那一届的签约作家一起赴市郊的张公山骞参加签约仪式。那也是我辞职在家整整三年后第一次重新进入集体,我有点惶恐,不知道即将面对的是怎样的一群人。按规定我们需要在张公山骞住一个晚上。那天一早起来,我需要先把自己年仅3岁的女儿送到朋友家,然后才能往集合地点赶。为了尽量从容,我选择了一条狭窄但很快捷的城中村小道,没想到被堵在路上。王新民很快打来电话,说一车人都在等我。我很抱歉,请他们先走,我开车追赶他们。这一追就追到了张公骞。真是难堪。我记得,当我追到徐东平价时,我把车停在大巴后面,心想终于追上了,得先找个停车位,把车停好,然后再上大巴。却眼见一位宽脸粗眉,头发茂密的男士从前面的大巴上下来,缓步走到我跟前,严厉地问,你怎么回事?这种情况下还想再花时间找停车位?我马上说,对不起,你们赶紧走吧,我开车跟在后面,保证不耽误事。这就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威严,没有多余的话。这种印象并没有在后来的接触中发生转变,虽然后来大家熟悉起来,但我从来都当他是一个严肃而重要的存在,即使我说,他其实是一个孩子,一个严肃而重要的孩子。
严肃而重要,孩子,这样的词语搭配一点也不矛盾。人一上了岁数,对人情世故有了相当的体量后,容易变得圆滑,变得辛辣,变得吝啬,变得只爱自己。那样的人看起来,尤其在年轻人,或者他们认为的不重要的人面前,仿佛是严肃的,其实是滑稽的,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拥有强烈的自主意识的人心目中的重要之人。反倒是率真,透明如孩子的人,才会具有真实的严肃,才会让人觉得真正重要。王新民就是这样一个人。
2013年,我跟王新民已经相识两年了,但一直未有更多接触。两年间我又有两部新作问世。《卡奴》出版伊始,有一天他突然发来一个长篇评论。那时候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初入文坛,两眼一摸黑,谁也不认识,也不知道路该怎么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外省女子》出版后,编辑说为了宣传,需要书评四到五篇。我硬着头皮找到当时与我一样名不见经传的几个作者,他们有的也只刚刚出版了处女作,有的已经出版了两三本书。我请他们帮我写评论,虽然一一得到应允,但仍觉得忐忑和难为情。对我来说,开口求人是一件特别撕裂自我的事。所以当第二本书《卡奴》出来,看到王新民主动发来的长篇评论,我有一种目瞪口呆的感觉。
在评论最后,他提到了我的一首诗。这首诗写于当时刚刚结束的长篇小说笔会:“在这个世上没有属于我们的棺木,没有能从我们身上逃亡的春天。”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我很迷茫,不知道持续的创作对我来说是否可行,我因此写下这样的诗句,有自我鼓励的意思。我在集体从笔会驻地前往某个景区参观的大巴上,当众颂读了一大早一挥而就的诗句,没想到令王新民印象这么深刻。就是因为这首诗,王新民开始阅读我的作品,而后写出长篇评论。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既使在今天以这样的方式写出的我感受,仍不能写出我当时的心情,一个仅仅只是一只脚跨进文坛的还在分辨方向的作者,王新民作为一名资深的业界长者,一位领导,洋洋洒洒上万字,为这株刚刚萌芽的幼苗提供支持,未有任何索求。不仅如此,他还请来其他评论家,如樊星、吕幼安、曾详顺等,在我的另一本书出版后,一如继往地支持我。
正因为有王新民,我才对作协有了一定了解,也非常感激这个组织在提供交流平台和对作家的培养上开展的工作。一个组织是积极开阔的还是自私无能的,在如何对待新人上最能体现出来。我当时初来乍到,又是一个异乡人,懒得在除小说之外的其他事上,比如私下里多聊天、走动上花时间,以便博人照顾。我大多数时候是一个奇怪的期望脱离日常生活和庸俗人际的人。王新民在当时主要负责签约作家工作,对我这样的怪人与其他作家无异,接纳、鼓励,让人觉得温暖。作为一个游弋惯了的自由分子,能被“组织”这个词打动挺不容易的,何况细想起来,我还时常能从中体味出“娘家”的意味来。也正是王新民,最先发现和认可我在文学创作上的天分和素质,鼓励我坚持下去。有那么几次,我们偶然坐到一起,我对着面相肃穆的他,却觉得无比放松,我跟他一起喝酒、抽烟,聊创作。我一个接一个讲我的小说创意,他安静地听着,只偶尔发表一下意见:
“好,真好,特别好,就这样写,就这样。”他说。
他带给我前所未有的信心。
而我的信心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长辈,还因为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和评论家,具有相当水准的文学创作能力和鉴赏力,能得到这样一位长辈的赏识,我感到非常珍贵,对他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迄今为止,王新民已经出版作品20部,其中,诗集《走向黎明》《美丽的阵痛》,散文诗集《颤抖的灵肉》,评论集《与缪斯女神握手》《精神脐带》等作品文采迸发,广受好评。我第一次阅读王新民的著作还是在刚加入武汉作协之时,那时他知道我也写诗,就非常平淡地找出一本他自己的诗集出来,签名后赠予我。我被诗集中天才般富于激情的长句惊呆了,很难将它们与眼前这位衬衣西裤,严肃持重的老者联系在一起。我说写得太好了。他摇摇头说,年轻时候写的。我当时突然觉得有点悲伤,为一种叫作命运的东西。我常说人有人命,书有书命,不必期翼,听天由命。那是因为我还年轻,明白名利心如果太强,会很累,不如撒手,只管写,其它的交给命运。而面对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老者,当我发现他的作品光彩照人,却遗珠于大海,便产生了不平。但王新民显然并不因此而烦恼。如果烦恼,他必然会与命运兜圈子,裹足不前。他后来一部接着一部的作品证明了他的实力。我最近一次收到王新民的著作是在今年3月,评论集《精神脐带》作为“武汉作家书库”系列作品之一出版发行。这本书囊括了王新民近年来为许多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所写的评论和序跋,武汉本土的大部分作家,其作品名都出现在这部评论集当中,王新民研究并宣传着这些有待被发现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以己之力用心支持着他们。而我也有幸成为这其中的一名。这部评论集收入了王新民为我写的四篇评论,洋洋40页,殷殷期望,可见一斑。
如果说到今天,我在文学创作上多少有了那么一点点进步,必定与王新民当初的鼓励分不开。当我慢慢借助作品打开圈子,我在好些场合都听到有人提到王新民对我的提携,他们说,你就是谢络绎啊,听王主席说武汉作协有个特别棒的青年作家,很有希望,就是你啊。每一次我的内心都会荡漾起别样的情绪,被认可的满足和被关照的感激,交织出对王新民深深的信任。这种信任还在于,他不求任何回报。我多次在节日里提出要去看他,都被他无情地拒绝了。有一次,在一件我当时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上,我受到一位朋友的错怪,心有委屈,转而向王新民寻求帮助,希望能讨个说法。他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跳出事件本身,劝我把目光放得长远些。他始终认为我可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中去。突然之间我就觉得没问题了,安全了,整个世界都是善意的。我有了一种坚定的想法:无论将来我遇到什么,受到怎样的误读,一定会有朋友如王新民这般,不加思索地选择站在我这边,信任我,支持我,正如我信任和支持他们一样。
在人群中,王新民是健谈而克制的,这是他家长性的一面,同时他又是善良和贪玩的,这是他孩子气的一面。这两点同时出现在一位看多了人生景物的老者身上,是完美的。他给我们讲文坛中的故事,但从不因那些故事的情感倾向而掺杂他个人的情绪,他从不评判个人,尤其是不会讲人的坏话。他的眼里只有人和人交织出的故事,在故事中,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立场和角度,他因为理解他们而从不对他们的为人下结论。这一点是多么难得。这不就是一个孩子的眼光吗。在孩子眼里,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即使有童话中的大灰狼和现实中爷爷奶奶嘴巴里经常出现的会把不听话的小孩捉走的警察叔叔,然而无论何时,孩子们都快乐地玩耍,大灰狼和警察叔叔在哪里?根本不存在嘛。如果孩子们这么认知是因为涉世不深,那么对于一个摸爬滚打了很久的长者而言,对世间人和事仍怀着孩子般的感念,对他人体恤,全然接纳人生悲欢,又是因为什么呢?是太傻太耿直太会做人,还是别的什么?我的看法是:无他,涉世太深矣。他已经洞穿了人生的根本,变得超脱和简单了。人生多么奇妙,涉世不深和涉世太深,到最后,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当然并不是所有人的人生都是这样,更多人在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后,会成为一个太像老人的老人,世俗所定义的那种所谓的智者,狡猾,唯我独尊,众人皆醉我独醒,看世事一片苍凉。最难得的其实是最终活成了一个孩子,因心存体谅也从内心深处原谅并开拓了自己,终得洒脱。
我所敬爱的王新民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在我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一个特别容易心急、特别容易受到轻视、特别容易放弃的阶段,他以他孩子般的心理样貌和为人之道影响着我,使我能在关键时刻慢下来,稳下来,坚持下来,与人为善,开放、大度地看待这个世界。这样的影响特别重要。我发自内心地尊敬他。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我一直直呼其名,是出于成就这篇文章的需要,不愿让读者先入为主。毕竟,写领导与写师友大不一样。
散文责任编辑:田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