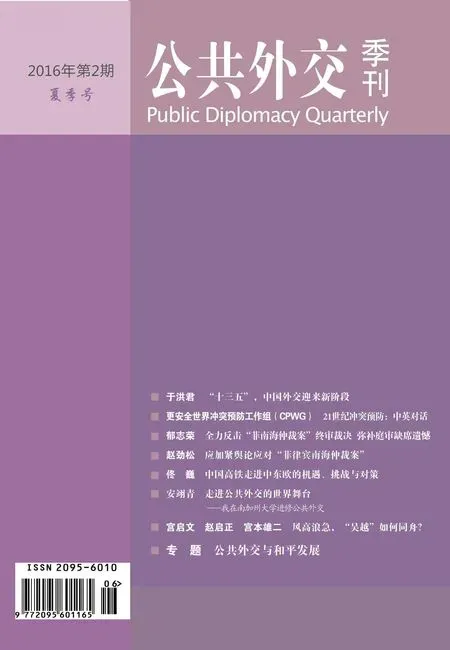中国外交转型
——从“以国家为中心”到“以公民为中心”
于 凡
何为“以公民为中心”的外交?
中国外交转型
——从“以国家为中心”到“以公民为中心”
于 凡
“察哈尔圆桌:中国外交如何从国家中心转向公民中心——王逸舟作品《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座谈会”于2016年3月22日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察哈尔学会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记者和出版业的朋友齐聚一堂,共同讨论王逸舟教授的著作《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本文摘录了部分与会者的观点,以飨读者。作者王逸舟关于中国外交由以国家为中心向以公民为中心转型的提法属于新见,欢迎读者就此展开讨论或投稿本刊。
何为“以公民为中心”的外交?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未来的外交,应当不只是领导人的大手笔或是中国经贸在世界舞台上的叱咤风云。最重要的还是要夯实社会基础,将个体的人搭起来,“以人为本,外交为民”。
“以人为本”不是说仅仅给公民提供一些保护、慈善和关怀,而是保证我们国内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社会个体是大写的,是受到尊重的,使我们的公民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我们的公仆、我们的外交部门理论上是服务者,是被纳税人,被我们企业养活的。这个以人为本,不是说只保护我们的公民和海外的公职人员,强调具体人事的安全,政府应该能够服务普通大众、服务社会,这就是外交“以人为本”。
陈志瑞(外交学院教授,《外交评论》执行主编):中国外交是否能从以国家为中心转移到以公民为中心,是和我们的世界观、战略目标有密切关系的。先说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希望以后的世界是一个完全以实力说了算的世界?还是一个更加多元的,既需要硬实力也需要软实力,国际协调和平共处的合作的世界?再说我们的战略,是不是一定要好好把握住韬光养晦?是不是等到以后我们实力足够了,一定要跟美国一决高下?这样就牵扯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是需要一种和平的外交,一种“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外交?还是完全从国家或者政府的利益出发,完全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外交?
尹继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我觉得“以人为本,外交为民”可以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国家外交战略上的层次。第二个是技术服务层次的,我们在技术层面上为人民服务。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外交有一些变化,理念上提到了要外交为民,但是具体做得更多体现在技术上。我觉得“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放到战略层次去处理才是真正的外交转型。这涉及对中国外交的本质或者它的目的的理解。
我们常常将外交理解为高级政治,是服务于国家的需要、服务于政治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大家比较公认中国外交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基于现实主义来看都是基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就是高级政治的话题,它比较抽象地界定国家关系,处理全球问题,跟普通民众并不一定是直接相关。但是如果要理解“外交为民”的话,必须要加上社会利益。如果我们要做到外交为民、以公民为中心的话,我们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之中,必须要把社会利益纳入进去,社会利益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
金相淳(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韩国东亚和平研究会会长):我们谈论外交的“以民为本”,我相信这个“民”的意思是国际社会的民众,并不只是中国人民。因为中国外交不可能只影响中国人民。
中国外交为何要转变?
王逸舟:随着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领事馆、军方和政府的压力也随之增大。如何保护中国的全球利益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传统意义上,保护中国的全球利益主要是靠军舰、靠外交的使领馆、靠政府的各种驻外机构。而今,随着全球市场的逐步建立,企业的跨国合作和公众的跨国交流机会增多,外交的行为体已经不再仅限于政府机构和精英阶层,普通公民也逐渐成为外交活动的主体。未来中国的外交,包括未来对海外利益的保护,靠的不只是军舰、官方外交或是政府看得见的手,更重要的是靠社会公民起作用。
现在总体来说,中国外交还处在比较粗放的阶段,即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主要通过传统外交方式来进行。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中国外交在转型过程中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但是未来中国的外交一定是更加多元互动高度参与的进程,这是外交长期系统的工程。所以不要把外交看成是少数精英少数大人物的事情。金字塔没有底座肯定不行。底座越宽,社会的参与热情越高,越能展示中国的亲和力,“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当然,没有塔尖的外交部和中南海的核心战略指导也不行。
目前,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公众、社会和企业等积极、广泛参与,提高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
陈志瑞:想做好“一带一路”,缺少社会的维度恐怕是很困难的。假如没有社会的参与,我想可能很难收到真正的实效。中国是个大国,我们利益是多元、多层次的。目前很多项目是国家在里面唱主角,但是假如社会不参与进来,恐怕就很难持续。政府在其中应该怎么样营造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制定规则,需要通过外交沟通双边或者多边,去为中国社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环境,同样也要考虑怎么去监督企业、教育民众。
加藤嘉一(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我认为日本的外交应该是从国家外交走向公民外交转变的范本。日本是二战期间对外发动战争的国家之一,也是最后的战败国。二战后日本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日本的国家形象可以说是个“零”,那么日本如何走出战败国的困境呢?
2005年,在北京包括中国各界发生了很多反日的游行。当时有两万多家日本企业在华注册,大概雇佣着一千万以上的中国员工。当时我和很多日本的企业家,包括佳能、索尼的高管讨论,他们说特别希望政治家闭嘴。只要我们的政治家不说话,不干扰日中关系,我们可以靠产品、靠我们企业的行为大大地改善日中关系。
当年如果没有日本的产品、日剧、日本漫画,我不敢想象今天的日中关系会恶化到什么程度?尤其是2005年的时候,小泉纯一郎首相武断地参拜靖国神社,两国的政治氛围、两国相互的理解面临非常恶劣的局面。但是哪怕是那么一个情况下,由于日本的汽车、家电等产品,包括日本的一些软实力产品的存在,很多中国的公民喜爱用那些产品,才能够始终支撑两国关系至少往前走。
所以我觉得从战后到今天,日本的政治家也做了一些事情。1980年代福田康夫首相对东南亚的外交就是强调以人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政治家首先要做到的事情是为公民、企业家提供良好环境,保护好国家形象,稳定整体的对外的政治关系。
日本一提到国家战略很容易引起误会,因为我们当时提倡大东亚共荣圈,所以日本人的对外公关、对外传播是不适合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去做的,我们从产品、民间的角度出发,日本才能走出战败国的阴影。
中国外交如何转变?
王逸舟:时代的进步,中国外交的进步,一定要以人,以每一个个体公民,以每一个社会的分子的进步为前提。过去我们外交认识只是国家的一种博弈的大战略。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如果公民对本国的政治发展、社会进步没有关注,对自身的权利保障没有关注,外交官的努力最终将会枯竭,他们获得社会的支持也会减少。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加强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参与和智库的评估,包括一定程度的公开,让政策更加透明,让社会有更多知情权,让整个过程有一个纠错的可能性。这个过程十分复杂,涉及各种权力的制约,涉及我们的政务在阳光下,包括外交的预算。这个不是短时间的事情,是一个很长期的改革进程。随着这个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外交会慢慢健康化,会渐渐符合国际上的标准。
当然,社会也好,人民也好,也有其层次和副作用。比如说民粹主义者,他们也是社会的一分子。有的时候从外交实践来看,这种激进的民粹主义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这对外交核心来说也是很大的压力。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本身不是一个单向的正面的正能量,它包括很复杂的塑造、互动、成长的过程。
强调外交要转向以人为本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是跟整个社会的进步,整个改革的方向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要想象以人为本就是一次性的,就是好的设计,一个路线图就完事了,它将是伴随中国成长的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张 涛(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如果外交真的要转向以公民为中心的话,更多的是要普通民众来了解外交,特别是让大学生这个层次的人了解外交思想。一方面,我们现在的外交官队伍的知识构成比较单一,多向大学生宣传外交知识能激发更多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才投入其中。另一方面,我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所以,以公民为中心的外交就要回归到我们内政以民为主、以民生为主的这一根本点。
于 凡:察哈尔学会秘书处研究项目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