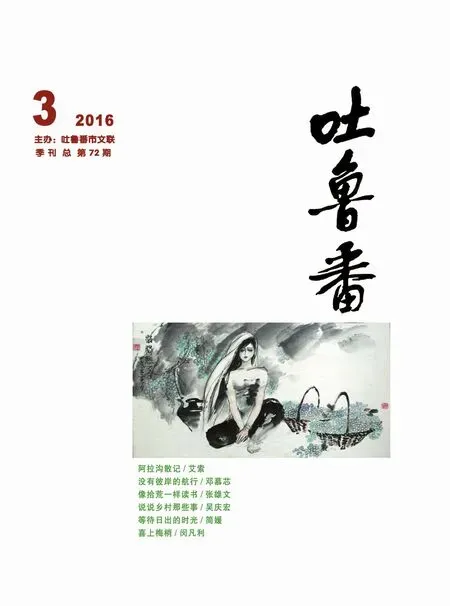像拾荒一样读书
张雄文
像拾荒一样读书
张雄文
人生最惬意的境界,大概要算曾国藩的“百战归来再读书”。
夜色深沉,明河在天,四周静谧如洪荒远古,一束橙色笔头般的火焰从油污的灯盏里伸出来,偶尔跳跃在沧桑的眼眸,漂白了木质的四壁,勾勒着灯影里握卷沉吟的解甲人。阴谋、算计、杀戮、血腥、瞬间转换的生死成败与随之而来的或喜或悲,都随远去的鼙鼓声悄然消隐。清风徐来,窗外的海棠花香乘势探入敞开的家居衣衫,与书中的古贤今哲一道沁润着解甲人风雨摧磨硬如磐石的心灵。天地空阔,物欲隐灭。人生有此,夫复何求?
我不曾有曾国藩踏破关山的金戈铁马,慕书恋书之心却也如出一辙,童年至今始终如一。稍有不同的是,曾国藩出身荷叶乡间的殷实之家,少年时代得到一本心仪如窈窕淑女般的书,像阵前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张飞,易如反掌;我则家道寒微,土砖瓦房里搜寻片纸不易,何况那些明眸皓齿、顾盼生辉的“淑女”们,只能像一个落寞的拾荒者,时常在荒芜废弃间祈祷从天而降的一份惊喜。
我对书籍的迷恋始于九岁。那年暑假,或许因期末考试得了第一名,外地工作的父亲咧着嘴,一个午后破天荒地带我到老家的“大城市”新化街上玩了一趟。烈日高悬,蝉声聒噪,汗水润透衣背,都早已不在我眼花缭乱的意识里。只觉得满街人流熙熙,店铺如林,古朴的深灰色青石板路踏上去夯实、清爽,似乎有一股山泉般的凉意从脚板直透顶门,像电流从山脚瞬间滑过山顶,与乡间软乎乎的黄泥土路不可同日而语。我随着父亲进了贾府大观园般地走走停停,最终像牛犊盯住了一丛鲜嫩的绿草,停在了街边一个小人书摊前。
书摊不大,摆在浓密如盖的樟树荫里,地面铺开一张饭桌大小的塑料布,整齐放着一本本连环画;靠里坐着一个衣衫朴拙、面容清癯的老者。他的身后向着大街似乎竖着一块倒放的门板,也一排排挂满了红红绿绿,都是些封面颜色各异的连环画,诸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瓦岗寨》《小八路》《平原游击队》一类。四周散了些低矮的小木凳或者靠背竹椅,坐满了全神贯注捧着书本,年龄大小不一的孩童与少年。
家里没有这些小人书,我却在夏夜屋前合抱粗的苦楝树下,听老辈们讲过这些故事,或者在村里晒谷坪上看过些电影,也偶尔从同学手中借过三两本,对一些恒星一般活在书里的英雄人物如数家珍,心神往之。我再没了别的逛街兴致,涎着脸向父亲央求留在这里看书。父亲犹豫一瞬,小声地问了价,两分钱看一本,于是爽快答应了。
我不知道到蓝色天幕上那轮炽热的火球是如何疲乏地散尽了暑气,悄然靠近了西边的山峦;到别的地方办事的父亲又是何时回来,静静地站在了我身后。慈眉善目的老者一声“要收摊了”的吆喝,将我从刀光剑影或者枪林弹雨的英雄往事里唤了回来。只得怏怏还了书,像被迫告别正玩得意兴盎然的好伙伴,依依不舍随父亲重新踩着光滑的青石板,与云间三三两两落下来的倦鸟一道踏上归程。
新化街上终究离家太远,大人去一趟都殊为不易,何况我这偶尔还像制作红薯粉丝一般挂着鼻涕的小屁孩;口袋里除了常不空山上摘取的小野果,也少有从摆摊老人手中换过小人书的两分硬币。当我渐渐从小人书摊的沉醉里拔出来,重新与天空的浮云、树上的鸟窝、塘边的蜻蜓,甚或坪前的蚂蚁木然相对时,一个意外的发现令我欣喜不已。
与我家共着一个堂屋的邻居,男主人是村里多年的支书,个儿不高,能说会道,依辈分我们几个兄妹叫哥哥。他小父亲几岁,却膝下寂寞,无儿无女。我们泥鳅一般串门时,他与堂嫂颇为欢喜。一次我偶然上门,没见一个人影。他家除桌椅、碗柜等几样简单的杉木家具外,几乎空空如也,平素出去便不大锁门。我正准备打转,忽然瞥见打开的破旧柜子一角赫然放着本书。好奇地拿过来一瞧,是部砖头厚的《水浒传》,封面一角已深深蜷曲起来,像门前阳光暴晒下的一片芭蕉叶。随手翻了翻,多半是些陌生的繁体字,许多字眼只能猜测。饶是如此,我的心依然怦怦直跳,有着在山路上闲走,蓦然发现一枚闪着金色光芒的钻石般惊喜。
这部书在我眼里是稀罕的珍宝,在邻家堂兄那儿大概也是。他家也不宽裕,堂嫂有积年的慢性疾病,一年到头捧着空了满,满了又空的陶瓷药罐,不会有闲钱买书。我已无暇探究书从何处来,也不敢向堂兄开口借,生怕他不肯,神差鬼使地拿上书,疾走的野兔一般穿过堂屋,溜回了自己家。
几个昼夜后,我跳过所有的景物描写和诗词,囫囵看完了全书。这是我最快乐也最担惊受怕的日子。那时课堂上还没学过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不知道原来“窃书不算偷”,第一次担了“贼”名,半夜里的床上还偶尔惊醒,生恐堂兄火冒三丈找上门来。路上遇见他迎面过来,便急忙远远躲过,闪在了高高的稻草垛背后或者椿树影里。最后一页翻完,被高俅等人害死的宋江“累累显灵,百姓四时享祭不绝”,我在一腔幽幽怨愤里长吁一口气,贼着眼,找了个机会鬼鬼祟祟溜进堂兄家,将书完璧归赵,放回了原处。
多年后我才发觉,偷来的书读起来是如此记忆惊人,勒进石头一般印象深刻。而今自己有着一间宽敞的书房,两边书架里满是簇新的书籍,可以风晨雨夕从容不迫读书。书一合上,多半内容却已忘却了,像彬彬有礼的上古贤士,将别人送上的礼物又立马原封不动还了回去。我读完堂兄的书,便能说出一百零八将的主要故事和多半好汉的绰号,还能学着父辈们屋前讲古的语气绘声绘色说给弟妹们听,关键时刻还能老练地卖点关子,引得他们欲罢不能,屁颠颠地做着原该我做的家务,以当作交换条件。
一个凉风如水的夏夜,四周寂寥,虫声唧唧,屋后的大株山偶尔传来一两声“哭鸟”(猫头鹰)的悲鸣,我与同睡在厢房的两个弟弟又开始钻在被窝里讲《水浒》。夜已深时,弟弟们还毫无倦意,牛皮糖一般粘着我往下讲。说到没羽箭张清如何一颗石子一个,打得前来围攻的梁山好汉溃不成军时,弟弟们似乎不甘心目中的梁山英雄们打不过张清,大声争辩起来,说是我瞎编。这时,门忽然推开了,从工作的矿山回家休探亲假的父亲笑着进来,夸奖了我的记忆,弟弟们才终于服气。多年后,父亲闲聊间还常常眉飞色舞地说起这一幕,脸上满是以我为荣的自豪,将我的记忆拉回到青涩而快乐的童年读书时代。
大概喜欢读书的缘故,我少年时代比较文静,甚或有点过于老成,喜欢模仿大人的举止,不像两个弟弟那么猴儿般野。每每随父母走或远或近的亲戚,我很少与同龄伙伴外出疯玩,而是常常留意有无书报。书籍自然如同我家一般难觅踪迹,但那时包裹食物或者别的用品偶尔用的是废旧报纸,若能找到污迹斑斑的一张,我半天的时光便能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飞快流逝了。无论这家亲戚是悲悲戚戚的丧事还是吹吹打打的喜事,于我已如九霄云外,一点也不相干。
父亲见我喜欢读书,开始设法收集单位里一些被人遗弃的杂志,将它们从几十里外带回来,时断时续,没有定准,却令我如获至宝,大开眼界,诸如《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上海文学》,最多的是与工人有关的《主人翁》和《支部生活》。第一次读到贾平凹的《鸟窠》,便在当时的《人民文学》上。我住在乡间,生活的圈子小,周围没有姓贾的人;文中多次舒缓而怪异地写到“它(毛驴)的眼睛被布蒙住了,套着磨杆,走着一圈,又一圈;我跟着毛驴的屁股,也走着一圈,又一圈”,因而对“贾平凹”三个字印象极深。不想多年后,贾平凹名声如日中天,直逼文坛顶峰位置;我已步入鬓毛挂雪的中年,他仍然笔如泉涌,锐气不减当年。
年岁渐长时,父亲偶尔才能弄到的三两本杂志已满足不了我的需求。焦渴间,一个堂叔如及时雨般出现了。他在隔村子十多里外的搬运公司上班,与父亲一样也吃着村里人羡慕的国家粮,敦厚老实,不善言辞,几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干的又是食堂炊事员,回家也是田间地头忙个不止,我从来没想过他能带给我某种惊喜。
一次他偶然到我家办事,听母亲说我到处找书看,忽然说,我那里有啊。原来他单位有个小图书室,各种大部头的书籍不少,母亲深知我心,连连替我道谢。我从外边回家听说,第二天便起个大早,心急火燎地赶往堂叔的单位。这是一个炎炎夏日,云彩似乎被人恶作剧般藏进了某处山沟,天空一片炫目的白热。我一个人沿山路踽踽独行许久,觉得随父母走过几回的路长得没有尽头,汗水从睫毛滑进眼眶,涩得难受,眼前时常一片迷离。往常出没戏闹的鸟雀影儿也不见了,只有树荫深处的蝉儿在撕心裂肺地鸣唱。终于挨到堂叔那儿时,我的辛苦才获得了丰厚的补偿。他给我打了一份饭菜,满满一碗平素难见的青椒炒肉,肉片肥腻可口,至今嘴角似乎尚有余香;还借到了三部长篇小说。
这时,我已学会了做读书笔记。堂叔那儿借到的一本反映自卫还击战的小说不算太厚,里面特异的南疆风光与战地描写令我爱不释手,还书的日子虽然从容,却终究得还回去,摘录也似乎不大过瘾。我索性将全书抄录下来,工工整整写满了几个新买的作业本。我作文时能比较自如地写景状物,课堂上时常被老师当作范文,这回的抄录之功大概不小。
借也罢,抄也罢,说到底是无奈之举。我时时渴望有一部属于自己的书,能放在母亲用秕谷做的枕头边,或早或晚随心所欲翻看。这一愿望几年后才总算得以实现,有了一部课本以外的新书。这部书来之不易,淌过了三十多个春秋的似水流年,至今被我小心翼翼收藏着,不肯轻易示人,像金屋里藏着的一个绝色女子。
这是一部薄薄的《呼家将》。我在镇上供销社弥散着糖果清香的玻璃柜里盯上它有好几个月了,定价是三角八分,那时的一元似乎能买斤把令人口水直淌的猪肉。我像一个准备起新屋的农民一般,暗淡的灯光里无数次计算汗渍津津积攒了许久的碎散钱币,还差了点。便又趁休假回家的父亲酣然午睡,从他床头挂着的衣衫口袋里偷拿了五分,总算够数了。
一个阳光晴好的日子,门前两棵缀满露珠的芭蕉树绿得格外晃眼,我揣上钱打算出门。母亲听说我去买书,生怕一把零钱容易弄丢,第一次慷慨换给我了一张五角的整钱,紫色纺织女工图案的那种版本。她管着一家六口的柴米油盐与吃喝拉撒,往常比父亲吝啬多了,因而我颇感意外,乐成了一根晨风里摇曳的狗尾巴草,一路小跑到供销社的柜台前买了书,那本也带着淡淡糖果芬芳的《呼家将》。
返回时,我漫不经心数了数找回的零钱,竟赫然多出了一张纺织女工。才想起可能是那位肥肥胖胖的售货婶子找零时,忙着和旁边的同事闲聊,将我递过的钱连同书和零钱一道给了我。也就是说,这书不但算是供销社白送,还得了一角二分的跑路费。我情知应当转身回去,脚下却生根一般纹丝未动。家中过于拮据,别的新书似乎在向我眨巴晶亮的眼眸,我像一个侥幸的拾荒者,心里忽然涌出一丝窃喜,最终竟未能回去还钱。几天后,它们给我换来了枕边的另一部书。
多年来,这事一直隐秘于心。随着岁月之流的飘然远逝,愧疚如同柴火上锅底的沸水一般翻滚。那家叫沙塘湾供销社的国营店铺早已倒闭,人去楼空,四周满是林立的高楼与挨挤的各类私家超市。售货的胖婶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妪了吧?若有重逢的可能,我愿意如廉颇一般背负荆条匍匐在地,虔诚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