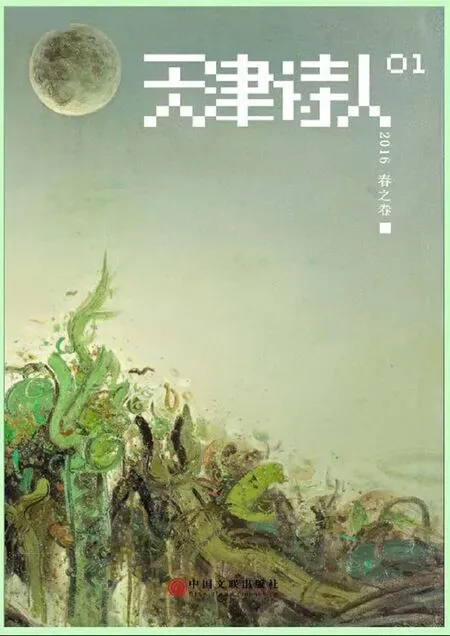病人
潘云贵
1
挖土机在春天取代燕子呢喃,发出轰鸣声响,推倒乡村的五官。
活在昨日的田野、山林和果实皆已去世,它们葬于文明的废墟底下,像亲人呼喊着他的名字。
他坐在昏暗的瓦房里,陪一盏濒临失明的钨丝灯猜度彼此死亡的期限。墙上的裂缝绘制出丛生的纹络,模拟他脸上的河谷。他身形渐瘦,如竹签,剔着暗夜的余烬。
他叹息,抽烟,咳嗽。在风湿的双腿中,骨髓被时间的蛀虫分食。他用粗劣的尼古丁填埋,痛,仍旧痛着。
在这春天,在这永不再来的夜晚,隐去的星群是大地所有过去集合起来的告别,月球是短路的吊灯、一个关闭的路口。
他的年龄、姓氏、祖籍跟烟灰一起撒在发黄的纸面上,一个火星燃起,烧了。
一粒豆子在水泥中关上最后的门,凝固,成为一桩缄默的故事。迟归的群鸟把家园背在身上,口音被强行安在远方的树梢。孱弱的小屋,摇摇晃晃,像一枚果实,要落了。
世界像个死去的情人,曾经被他一人所有。他爱万物,如自己的子嗣。如今,村庄在咳血,灵魂被驱赶,安宁被打碎,孤独和流亡淹没大地,夺走他发声的喉咙和要崩塌的家。
他老了,同所有拥有“农民”身份的老人一道,被遗忘,被抛弃。
他捡拾儿女离开村庄那天决绝的目光,怀念妻子按在自己风湿双腿上的那双手。春寒料峭,他不停抽搐,像一头即刻被时间屠杀的牲畜。
放眼四下,空荡荡的家,寂寞回声响亮。他贴满膏药,握紧睡眠,一个艰难的翻身,白色的动静,只有风知道。
夜是倒空真相的麻袋。
他睁开眼又闭上眼,似已服从来自暗处的口令。
转瞬即逝的灯火,无法回来的昨天,风带走一切。万物归于一截截空白。
他像一件停摆的挂钟,骨头被岁月梳坏。
夜是一个巨大的胃,正消化着他。
2
太阳作为暴君,吸取他体内的海。
他置身高处,却仍旧没有改变自己奴隶的身份。
脚手架紧紧与他相连,仿佛一对孪生兄弟。
天空万里无云,也不蔚蓝,灰扑扑,像落满尘埃的白色桌面,并作为他生存的背景,时刻提醒他的渺小:出卖体力,城市的佣人,不被记住的名字,一张薄薄的暂居证。
护城河保持病态的抒情,钢筋水泥和绳索发挥物件的属性,不带同情成分。他不断上升下降,不断靠近光辉又被光辉疏远,在失语的地盘努力寻找流浪的喉咙和人形,未果,无法确认自己的存在。
大厦和高架桥使地面扭曲升高,城中村像患病的儿童想要水喝,房地产商把眼睛安在天上,还贷者被银行的验钞机吸入肺中,人们睡在一座座巨大崭新的石碑里,失眠,被烘烤,像熔化的泡沫板上失血的虱子。
他想起故乡,一个此刻只能作为风背在身上的地方。盛夏如火的凤凰花,跟天边的火烧云一样瑰丽,印在节气谱上:芒种、小暑、大暑……
日月星辰像虚假的布景罩在他头顶,出租车撅着屁股放出一路尾气,卫星城区如地雷埋在四方,地平线被倾倒在更远的地方。
城市被改造成一座座迷宫,扬起火葬场上空的灰烬。
故乡,千里万里外出生的地方,泥土与稻香遍布的故乡,无数等候和牵挂的故乡,他的或别人的故乡,此刻,正像一匹匹马倒下。
他的眼睛被突然袭来的风沙吹疼,急忙降落地面。
在学校受气的儿子跑到工地,嘟囔一句:
“吃了十几年这个城市的老冰棍,为什么却不是这城市的主人……”
他隐忍许久的眼眶,瞬间红了。手一抹,望望远方,没有回去的路。
故乡是一方废弃的旧址,乡愁是他一生的病。
3
时间垂钓完睡眠的鱼群,他醒来,自动进入城市的节奏:
牙刷与牙齿的问候,剃须刀和胡子的战斗,早间新闻对这世界美好的陈词,都是昨天相同的副本。他如机器,吞完桌上的牛奶、面包,匆匆出门,更大的空倒在社会的餐盘中。
中年女人涌入超市,喧嚣的空间像剧烈抖动的蚊蝇腹部。公交车仿佛时间推来的棺木,被无数双脚塌出未来的裂缝。
在城市深藏的脉络里,地铁是一串流脓的伤口,在指定的时间吐出浓稠的黏液,流淌到地面,绽放出黑色花朵。
人们穿长袖,围围脖,携带手机、菜篮、书包、公文包,覆盖车站、地铁站、码头和机场。
他混迹其中,戳光烟蒂上的灰,出卖指纹和笑容,挤进电梯来到高大积木顶部,站在一个角落里端正衣领,摆弄发型。镜子是一个哑巴,看着一个傻瓜。
他迈进一扇灰色的门,开始提线木偶的演出:
思维被文件绑架,四肢被领导租用,脊背被椅子奴役。
电脑显示屏像巨大机关枪口,对他扫射。他呆滞如一头骆驼。
落地窗外,飞机笨拙掠过,两边机翼像刀子割过他腋下,他不觉疼痛。
积木底下,割草机轰隆隆踏过的草地,如易感冒儿童裸露的黑色头皮。
夕阳憋红脸,坠落一刻,车胎泄气,天黑下来。
公交车站在那,红绿灯在那,地铁站在那,安检输送带在那,日渐深邃的秋天在那。
经历过太多大楼、街衢、盖章、刷卡、无线电信号殖民,他渐渐丢失自己的面孔,丧失自己的身体。
红尘拥挤,他被黑色挤着,成为黑色。
他是穿着皮囊的机器、数据、纸片,被时间挖出一个又一个的洞,埋进一个又一个的炸弹:
嘀嗒——
嘀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