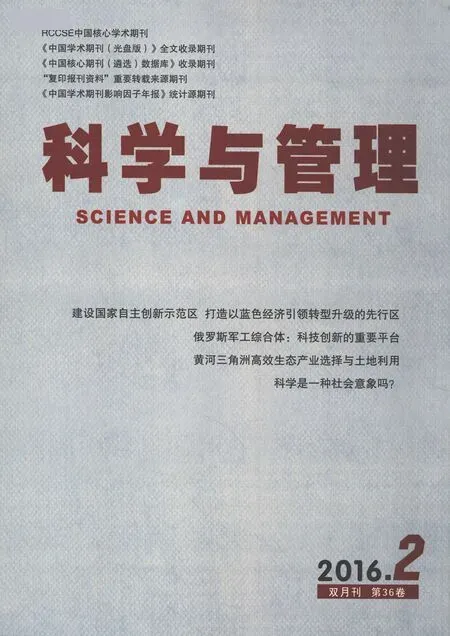科学是一种社会意象吗?
——布鲁尔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观批判
尹维坤(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州 510006)
科学是一种社会意象吗?
——布鲁尔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观批判
尹维坤
(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州 510006)
摘要:布鲁尔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观的核心观点是科学是一种社会意象。他一方面通过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社会制度的权威性类比,试图说明科学不过是社会常规;另一方面对寻找科学规范性的科学哲学进行意识形态的比附,论证科学哲学本身就是社会常规的产物,从而进一步解构科学的客观性。这种类比论证缺乏说服力。科学的客观性与社会常规的权威性有本质差异。因此,“科学是一种社会意象”的论题远远没有得到合理地论证。
关键词:社会意象;大卫·布鲁尔;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观;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是科学哲学中影响深远的思潮。这股思潮的内部虽有各种不同的理论流派,[1]但它们大致分享了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即认为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利益的社会建构,跟其他知识形态一样,科学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并不具有特殊意义的客观性。在这些流派中,爱丁堡学派是发展最为成熟的突出代表,引起最多争论,而布鲁尔又是该学派的杰出代表。他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中对社会建构主义的论述,观点突出、论证清晰,是反思与批判的合适对象。让我们从他提出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开始考察。
1 强纲领与知识规范
关于强纲领与知识的规范性、客观性的关系,布鲁尔的论述显得有些矛盾。[2]一方面,他对强纲领的明确表述中,并不主张知识的内容完全由社会决定。如布鲁尔谈到:“我之所以称之为‘强纲领’,是因为使它与(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仅仅对错误作出说明、或者仅仅对那些有利于知识的一般条件作出说明的目标形成对照。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强纲领’之所以被称之为‘强’,是因为它体现了下列主张,即知识‘纯粹’是社会性的、或者说知识完完全全是社会性的(比如说,就像知识根本没有任何来自实在的感性方面的输入物那样)。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隐含在‘强’这个语词之中的‘力量’所指涉的是下列观念,即所有知识都包含着某种社会维度,而且这种社会维度是永远无法消除或者超越的。”[3]中文版作者前言强纲领并不主张“知识完全依赖于诸如各种利益集团这样的社会变量”,也不是“只承认社会过程在发挥作用,不承认其他任何事物也可以发挥作用”。“强纲领的意思是说,社会成分始终存在,并且始终是知识的构成成分。它并没有说社会成分是知识唯一的成分,或者说必须把社会成分确定为任何变化的导火索:它可以作为一种背景条件而存在。”[3]262这些话确实没有否认自然对知识的作用,因此也没有否认组织自然经验的客观规范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他在著作中却常常表露出如下观点:科学知识完全是社会建构的,自然以及客观规范因素在其中不起作用。这单从他对《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的核心论题的界定就可以看出。他认为《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的核心论题有,知识的各种观念都建立在社会意象之上,逻辑必然性是道德义务的一个类,以及客观性是一种社会现象等。[3]251他甚至宣称,“我们应当使知识与‘文化’等同起来,而不是使之与‘经验’等同起来。”[3]21如此,有论者将强纲领看成极端的社会建构论是有根据的。如有学者说道:“概括地说,‘强纲领’所主张的是,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各种人类知识,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所有这些信念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决定的,都是处于一定社会情境之中的人们进行协商的结果。因此,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民族之中的人们,会基于不同的‘社会意象’而形成不同的信念,因而拥有不同的知识。”[3]译者前言这种立场毫无疑问的是规范知识论的对立面,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构成严重挑战。这种立场为布鲁尔的绝大部分论述所支持。基于反对相对主义化,维护科学知识客观性的目的,笔者将重点考察布鲁尔论述中将科学社会意象化、解构科学客观性的立场。
2 科学规范与社会“常规”
首先考察布鲁尔对科学知识的客观规范进行“常规化”解构。布鲁尔认为,人们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寻找某种知识的客观规范,将知识神圣化,是因为人们认为知识社会受到了威胁,知识的权威必须得到维护。[3]117-120正是这种权威使得知识有别于信念。对于这种权威的来源,布鲁尔承认“知识和科学都取决于某种存在于纯粹的信念之外的东西。”不过,这种使知识和科学得以存在的东西并不具有任何超验性。“存在知识‘之外’的东西,比知识更加伟大的东西,使知识得以存在的东西,就是社会本身。”[3]127科学知识生产中所有运用概念的过程都是可以争论和协商的,所有得到人们承认的运用概念的过程都具有社会制度的特征。[3]263围绕那些“具有普遍涵盖范围的法则”的、“与‘绝对’有关的光环,必定是由那些构成它们的特殊地位的社会构成物(social contrivances)产生出来的。当我们感受到它们那令人信服和具有强制性的特征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对象就是文化传统和文化常规。因此,事实证明,‘必然性的王国’就是社会的王国。”[3]290给予科学知识权威的客观的、必然的规范不过是社会常规!
由于社会常规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和任意性,为了尽量拉近社会常规与科学知识的规范性,布鲁尔试图撇清人们在选择社会常规时的任意性。他说:“各种常规都不具有任意性。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常规。……社会的可信性和实践方面的效用,可以对有可能成为某种常规、规范、或者制度的东西加以限制。”各种科学理论事实上都必须在人们从常规的角度出发所期望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并且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精确程度。这些常规都既不自明,也不普遍和一成不变。而且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程序都必须与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流行的其他常规和意图相一致。和其他任何一种政策性建议一样,它们也都面临着与接受有关的“政治”问题。[3]65
虽然如此,他还是感觉到科学知识与其他社会常规不一样。因此他认为,科学的各种方法和结论虽是常规,但并不是“纯粹的常规”,否则就会铸成大错,将各种常规降格为一些可以随随便便满足的、从本质上说要求不高的东西。事实上,科学“常规”通常要我们的体力和脑力发挥到最大限度才能达到。此外,各种理论和科学观念可以做出成功的预见。这是强加给我们的精神建构过程的一种苛刻的行为准则。
布鲁尔在此已经感觉到将科学预测的经验规范性准则说成是常规,牵强而不能服众。而且这样推广下去他就会犯无原则的错误,一切都会化约为纯粹的社会常规。但他仍然坚持:科学知识虽不是一般的常规,“但是,它也同样是一种常规。”[3]67对于自己论述的这种令人不放心的感觉,布鲁尔出于维护理论的彻底性,还是勉强接受下来。他说,这种感受即使在被正视并且拒斥之后依然存在,只能认为它是凭自己的权利存在的现象。他认为,“它的存在恰恰可以揭示某种与科学有关的、有趣的东西——因为存在于科学本性之中的某种东西,必定会激发出这种具有保护性和防卫性的反应。”[3]67布鲁尔没有说明那种“与科学有关的、有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也没有解释“激发出这种具有保护性和防卫性的反应”的“科学本性”是什么,这是极其狡猾的开小差行为!他将已经到舌尖上的、对科学蕴含的客观规范的表述又吞回肚子里。但是这种欲盖弥彰的诡计不能得逞。让我们将布鲁尔遮遮掩掩、不敢明言的话说出来吧——那种“与科学有关的、有趣的东西”和“激发出这种具有保护性和防卫性的反应”的“科学本性”是科学具有的规范性和客观性!所有规范的科学哲学和科学认识论早已经公之于众的道理不会因为布鲁尔的健忘和怯弱消失。科学苛刻地要求我们遵守的准则绝不是常规,而是人类认识铁一般的规则!布鲁尔试图通过社会常规解构科学知识的客观规范是不成功的。
3 规范知识论与意识形态
布鲁尔关于意识形态与规范认识论各种理论的联系的论证,是布鲁尔研究知识与社会意象之间的关系的典型案例,也是他消解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清晰表达。他通过将科学哲学中规范知识论理论说成是意识形态的隐喻,将科学哲学的规范理论说成是社会决定的。
布鲁尔选取了科学哲学中两种有代表性的理论:波普尔和库恩的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在布鲁尔看来,波普尔和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的基调都有一部分是由它们所使用的那些关键性的隐喻决定的。[3]85-88它们分别是对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和浪漫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的隐喻——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具有明显的启蒙运动意识形态的特征;库恩的范式理论则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运动意识形态的特色。而意识形态无疑是一种社会存在,如此那些试图寻找科学知识中的规范的认识论模式本身就受社会意识形态决定。这些规范认识论不可能指明科学知识的规范性。科学的社会意象特征再明显不过了。为进一步看清布鲁尔的结论是否合理,我们将他的论证过程简述如下。
布鲁尔首先对波普尔和库恩的科学认识论思想进行了对比。他认为,虽然库恩和波普尔一致同意真理和事实是他们理论的解释要点,但对它们的具体的解释和说明分歧却十分明显。布鲁尔对这些分歧做了归类:[3]93
“首先,他们赋予他们那些规定的(prescriptive)方面和非规定的(descriptive)方面的重要性不同。”波普尔设定了一些方法论的规定;库恩的论述更接近一种不涉及任何公开的合法化的说明,其中非规定性(描述性,对科学史的描述)十分明显。
“其次,波普尔强调的是辩论、不一致和批评,而库恩强调的则是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论断领域。”布鲁尔认为这是波普尔和库恩的理论社会特征的表露:前者认为最重要的社会过程是公众辩论(与证伪相应),后者认为得到共享的生活方式(与范式相应)最重要。
“第三,波普尔集中注意的是科学……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方面,”诸如方法论规则;库恩集中注意的则是科学的局部性和具体性的方面,诸如科学共同体的范例。
第四,波普尔把科学看作是一个直线性的、同质的过程;库恩则坚持一种循环观念。
波普尔和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的这些分歧,与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和浪漫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具有结构上的对称性,把波普尔归类到启蒙运动思想家一边,把库恩归类到浪漫主义运动思想家一边是很容易的事。[3]98因为,波普尔作为一个个体主义和原子论思想家,其思想中强调逻辑和方法论规范的特征,强调科学思维的普遍性和超越时间性的特征,与启蒙思想在思维领域强调普遍理性,在社会领域主张社会契约论神话如出一辙;而库恩作为范式论的提出者,其思想强调整体、范式的权威、逻辑和方法论的非规定性等方面也与浪漫主义思想风格相一致。因此,“显而易见的是,两种刻板的社会模式和政治模式,与两种存在于科学哲学之中的对立立场之间,有某种结构性的统一性。”[3]100
布鲁尔除了要从结构上一致来说明波普尔和库恩的认识论思想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联系以外,还从内容上证明这一点。他对内容上的相似性论证如下:
“(一)在这两种知识理论中,由个体主义的民主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家长主义的独裁主义构成的对立面是显而易见的。波普尔的理论是反独裁主义的和原子论的;而库恩的理论则具有整体主义和独裁主义的色彩。(二)由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构成的对立面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波普尔关于人类的理性统一和观念的‘自由贸易’的理论,与范式所特有的理智封闭状态、与范式那独特的语言所特有的丰富性形成了对照……(三)存在于边沁主义者的追求‘编纂法典’、追求明晰性的愿望,和伯克有关偏见之作用的主张之间的对立,是波普尔为方法论立法、划出界线的做法、和库恩对教条、传统以及判断的强调相对应。”[3]114
如此这般,布鲁尔就论证了科学哲学对规范的追求,其实不过是一个谎言,所谓的规范不过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隐秘体现。但是,这些论证饱含的穿凿附会,在笔者看来这几乎到了“听风就是雨”程度。为使这种“太突出、太富有联想性”的联系变得合情合理一些,让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他关于“知识理论实际上都是对那些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论断,布鲁尔对两种意识形态与两种认识论理论如何相联系的机制做了解释。他认为,“通过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对立的传播是十分广泛的。它是一种引人注目而又反复出现的模式,因此,任何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人都会遇到它……。”“通过社会经验的有规律的节奏,通过心灵寻找结构和模式的过程,这两种原型就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之中安顿下来,并且形成我们的思维过程所依赖的基础和资源。”我们“心照不宣地把这些意识形态当作隐喻来运用,”“从它们那里获得各种观念模式”。如此,意识形态就不知不觉地体现在我们所不得不思考的那些观念之中了。总之,从我们的社会生活经验和语言出发,我们心灵之中拥有的正是那些对我们的各种知识理论产生影响的社会原型——意识形态。因此,“存在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知识理论之间的联系根本不具有任何神秘之处,而完全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所产生的一种自然而然和平平常常的结果。”[3]115-117
4 对布鲁尔的批判
但是,笔者对这种有着诗意跳跃的论证实在不能心悦诚服,它仍然太唐突、太富有联想性,因为布鲁尔的论证问题重重。首先,既然两种意识形态都是在社会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对人们起作用,那么,波普尔和库恩就同时受两种意识形态的作用,由此布鲁尔就应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波普尔与库恩的知识理论不是同时表现两种意识形态或它们的某种综合,而是分别表现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的一种。笔者为布鲁尔设想了几种可能的解决方法。(1)布鲁尔可以论证说,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不可能综合或一起出现在一种知识理论中,任何知识理论都不能违反矛盾律。这样布鲁尔就论证了一种知识论规范,这种规范不以社会因素的转移为转移。布鲁尔试图从知识理论与意识形态的联系论证知识的社会建构性的努力就适得其反了。(2)布鲁尔可以从知识理论家的独特的个人因素方面解释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不同选择。这些个人因素要么受其它社会因素的影响,要么不受其它社会因素的影响。在前一种情况下,布鲁尔必须论证是什么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使得波普尔和库恩具有不同的个人特征,如若不然,布鲁尔就违反了他推崇的因果性原则:相同的原因导致相同的结果。而这种研究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极其繁琐的(SSK中的实验室研究就是如此)。如果布鲁尔没有进行这样的分析,那么他关于意识形态与知识理论相联系的机制就远没有阐述清楚,他的结论就是唐突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布鲁尔只能将知识理论家独特的个人因素解释成自然因素,如此布鲁尔就事与愿违地论证了自然因素对知识理论的决定作用。(3)布鲁尔可以认为波普尔和库恩对意识形态的不同选择纯粹是一种巧合。这样布鲁尔就不得不再次违反他提倡的因果性原则——他无法对社会意识形态与知识理论的联系做出细致的因果解释。强纲领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总而言之,布鲁尔很难找到能够弥合他的论证跳跃性的补偿方法,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其次,即使我们承认布鲁尔的论证是成立的,但是这并不能由此推断我们必然接受如下结论:知识完全是社会建构的。因为,我们仍然可以进一步追问,社会意识形态的起源。对于这样的追问,布鲁尔或者给出无穷倒退论证(用更深沉的社会意识形态解释意识形态)或者引入自然因素解释意识形态的起源。前者在逻辑上和事实上(不可能有一种不在任何自然环境下形成、不受自然影响的、纯粹的意识形态)都不能接受。而后者却是对社会建构的一种反讽。
再次,布鲁尔将隐喻作为论证方式使用是很不严谨的。笔者很容易就能提出这种论证方式的疑难。比如,社会因素中的对立与矛盾如此繁多,知识理论为什么只反映出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既然社会因素能够用隐喻的方式影响知识理论,那么自然因素对知识理论的影响,通过隐喻的方式不是来的更方便吗?为什么人们不用这种方式,而是用更严密的逻辑论证展现自然对知识的作用呢?或者人们为什么不能用严密的逻辑论证展示社会因素对知识理论的影响呢?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在此如何解释?布鲁尔不会真去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他们惯用隐喻就是为了方便得出哗众取宠的结论。通过隐喻,他们方便地把科学文本处理成一个神话、一首诗歌或一个弗洛伊德的梦;通过隐喻,他们方便地寻求隐藏的幻想、令人讨厌的意识形态的罪过、无意识的象征;通过隐喻,他们能方便地在受精过程中看出男权主义,在流体力学和统计学中看到性别的影响;通过隐喻,他们能方便地暗示,编造动机和结论;总之,通过隐喻他们能无中生有,无端捏造![4]隐喻这种后现代的文风将“不可理解性变成了理论的优点;隐晦、比喻或双关语已经代替了证据和逻辑。”[5]这样做很方便他们得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结论。但是,思想上的投机和懒惰不能成为否定科学知识规范性和普遍必然性的理由。
5 结语
综上所述,布鲁尔通过将科学与社会常规类比,试图说明科学不过是社会争论和协商的结果,科学所具有的普遍必然性不过是社会制度的权威性,从而解构科学客观性。这种类比论证缺乏说服力。就连布鲁尔本人也已经认识到科学的客观性与社会常规的权威性的本质差异。他对试图寻找科学知识规范性的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化解释同样不成功。因此,布鲁尔论题:“科学是一种社会意象”远远没有得到合理的论证。事实上要排除自然以及人类理性的逻辑规范对科学的普遍必然的规范性是不可能的。
除了上述各种论证的缺陷外,布鲁尔对科学客观性的解构还使他陷入相对主义泥潭。正如他所说:“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建立在某种相对主义之上,这是不容否认的。”[3]252这种相对主义科学观下,科学归根到底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是一种具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和价值观念的研究风格。“它并不需要任何具有终极性的形而上学认可来支持它,或者使它成为可能。在这里,正像我们不需要任何绝对的道德标准,而是需要那些得到局部接受的道德标准那样,我们不需要任何诸如绝对真理这样的东西,而是需要具有猜想性的相对真理。如果我们可以接受道德方面的相对主义,那么我们也能够接受认识方面的相对主义。”[3]254但相对主义必然面临自我反驳的困难:如果相对主义是真的,即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那么它的这个论断本身也是相对的,得不到普遍的承认。另外,如果一切知识都具有社会的相对性,那么强纲领作为在某个具体社会中提出的知识口号,就只能在某个社会实用,而不能作为一条对所有科学知识进行说明的教条。如此,强纲领对自身的合理性进行了反驳或限制。总之,布鲁尔对科学客观性的社会学消解是不成功的。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陷入了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的偏见。[6]
但是,必须承认布鲁尔的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观仍然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科学确实不是一经发现即永恒而绝对的真理,实践的和社会的因素确实对知识起着重要的影响;人类并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除了理智以外,人类还有丰富的情感、欲望等非理性的心智现象,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科学的客观性;社会建构主义对知识的主体间性的强调也不无道理,等等。这些因素对科学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些作用能否在规范知识论中得到说明?这对规范的科学哲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刘保,肖峰.社会建构主义:一种新的哲学范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柯志阳.强纲领与知识的社会建构[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5):29-35.
[3]大卫·布鲁尔,艾彦 译.知识和社会意象[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4]诺里塔·克瑞杰主编.沙滩上的房子[M].蔡仲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85-178.
[5]艾伦·索卡尔.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试验,载于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C].索卡尔等著.蔡仲,邢冬梅等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62.
[6]安维复,崔璐.“自然转向”的对称性原则:问题、重建与评估[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7.
(责任编辑:王保宁)
Is Science a Kind of Social Imagery?——A Criticism of Bloor's Social Constructivism View of Science
YIN Weiku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The key point of David Bloor's social constructivism view of science is that science is a kind of social imagery. On the one hand he tries to illustrate science just as social convention,by drawing an analogy between the objectivit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authority of social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self is the product of social routine,further deconstruct objectivity of science,by seeking a metaphor between scientific normative pursued by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deology,This analogy argument unpersuasive. The objectivity of science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authority of social convention. Therefore,the thesis of "science is a kind of social image" is far from being rational argument.
Keywords:Social imagery;David Bloor;Social constructivism;View of science
中图分类号:B03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6.02.008
作者简介:尹维坤(1980-),男,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知识论、科学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