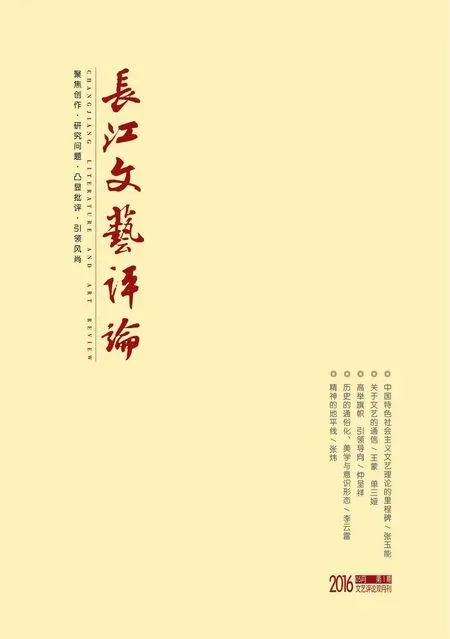“草根作家”、“在场经验”与底层文化生态
◎蔚 蓝
“草根作家”、“在场经验”与底层文化生态
◎蔚 蓝
“草根”、“草根性”的话题一直有着广泛的社会公共性,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以及进行文学研究的一种话语资源,在各种不同的话语方式的阐释中,在不断延续的大众话题热中,构成了一条长长的话语链,诸如“草根性”、“草根化”、“草根文学”、“草根作家”等等。在当代中国社会,“草根”已成为一个流行的行销术语,被打造成携带有特定时代意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符号。让人产生一点想法的是,“草根”抑或是“草根性”这些在现实中耳熟能详、具有巨大的社会聚焦力和关注度的词语,却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找不到相关词条的解释。疑惑中也说明了“草根”不是可以单从字面表意中去直接做解释的。它的实际指义往往体现在字面表意的引申和拓展中,在不同的观照者和接受者那里,“草根”这一词语的成色显然有所差异,“草根”所含括的阶层或文化等级也视具体的对象而被赋予不同的解释。诸如“草根”阶层一般直指“底层”和“弱势群体”,也有一些人自诩为“草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真的属于草根阶层,而只是以此来表示其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主义的疏离;也有的是借“草根”的话题,包装打造自己,以期更能迎合当下社会潮流的平民化、大众化的趋向,这可能也是“草根”这一词语在释义的包容性和现实的指认性上的特点。不过,对农民作家来说,“草根”从字面表意就很形象地显示了他们的身份特征,和那些自我标榜为草根的人不同,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草根”,生活在底层,与乡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真正是贴近地皮如草根般生生不息。他们的文学之根深植于乡土文化土壤,创作也更多地寄怀于故土人情,是在乡土视野中完成着最质朴本色的文学表达。对处在底层,而又被边缘化的他们,湖北省作家协会曾实施“湖北农民作家扶持计划”,具体扶持资助10位农民作家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让底层也得到阳光的映照,同时也是对农村文化星火的呵护,而这些作品也为理论上阐释“草根作家”的话题提供了例证。
一、“草根”作家与“在场经验”
作为“草根”的农民作家,他们的写作状态多数都属于“在生存中写作”,或是对“自我生存的表述”。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近年来大热的有关“中国经验”的话题,倡导作家要以拥抱现实的姿态介入对中国经验的阐释,留下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印象和大时代的集体与个人的记忆。显然,要求文学创作表现中国经验,回到经验常识,回到中国真正的历史或现实语境中,这是对主流精英作家的呼吁,而这些“草根”农民作家他们本身就生存在中国乡村最真实的现实语境中,写作和生活对于他们而言是基本贴合在一起的。他们“在场”亲历了20世纪后半期直至当下几十年里中国农村在不同发展阶段所经临的各种问题,成为乡村历史和众多生活事件的亲历者和目击证人,他们“在场”见识了时代变迁对农村的影响以及农民生活所发生的各种新的变化。即使他们走出去成为城市的打工者,也依然与故土乡村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因而他们多是以“在场者”的身份,对中国的乡村社会进行着“在场经验”的表达。这种近乎是原生态的对自我生存的表述,与主流作家笔下常见的乡村叙事有着很大的区别,在一些乡村叙事中,“农村”往往被符号化了,成为一种载体,只是被作为故事叙事的外壳,借此来叙写民族寓言,表达作家自己的创作理念和文化思考。或是通过叙写对乡村的记忆来反思历史苦难,或是在文学的想象中对乡村进行美学意义上的重构,这样的乡村叙事与现实中真正的农村生活,还是存在着隔膜感和间距感的,有的甚至挨不上边。
而这些出自草根的农民作家的创作,虽然叙事上还不够成熟老到,也明显地缺少架构长篇小说的经验,但他们对中国乡土经验的多视角观照下的叙事,突显出的是充满动感的现实中的乡村经验。通过他们的叙写,可以看到这其中既有来自乡土的各种农事、农经的原生经验,有反映农村世相百态的通识经验,也有隐匿在乡村意象之后的隐秘经验,以及自身作为农民生存处世的民俗和人情传通经验,像王能明的《郝家祠》、肖吉芳的《风雨缪家庄》、张开宇的《马庄的风云人物》、朱雪的《梅花塘》、李旭斌的《布袋沟》,从这些书名就能看出写的是某一方的乡土故事。郝家祠、缪家庄、马庄、梅花塘、布袋沟这些也许是虚拟的地名之下,便是他们的“草根”根系于此的故乡乡土。他们成长和所经历的特殊的时代,以及家庭和个人的苦难经历,使他们积淀了他人所不可援用的生存记忆和感情积累,正是这种长期在农村生活所积攒起来的底气,为他们走上文学之路提供了站脚的平台,也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大量可用的素材,以及可以攀缘想象的生活的枝桠和根系。所以他们小说的取材,所传达的内容及塑造的人物,不但体现了乡村现实的当下性和真实性,而且也体现了创作上的一种原创性。
明显地,他们的小说所表现的“在场经验”既是一种个人的经历和记忆,也是对中国农村社会的集体的时代记忆,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发展情势,也聚合了乡土社会的人情百态和世俗心相。余书林的《荒湖》叙写了荒湖边黄、吴两大家族祖孙四代为独占作为贡品的黄湾藕和凤姣米而厮斗浮沉的历史,将从乡村老者口传下来的地方史和乡风民情融入其中,带有独特的地域历史色彩和浓郁的民俗文化色彩。《风雨缪家庄》真实地记录了历史转型时期乡村曾经经历的艰辛和痛苦的风雨历程,以及新的社会变革给农民所带来的精神和生活上的冲击。《梅花塘》以郧西汉江边的小山村为背景,从梅花塘几代人不同生存形态的细致记录中,展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农村的发展与变化。《布袋沟》以解放初为开端顺接写至当下,横亘了古老三几十年的命运浮沉。《郝家祠》以郝进财从少年到离世为叙事主线,时间线段上从解放前延续到改革开放后的新农村建设,在70多年的时间跨度中,呈现出农耕乡土群落丰富的生态世相。
以人物个人经历作为贯穿主线,来书写乡村在蜕变过程中的潮起潮落,也成为熊衍锟的《古河潮》、熊章友的《断碑》,还有《马庄的风云人物》等其他几部小说的构建模式。有意思的是,几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以不同情形的出走而远离生根之地,最终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归乡土。最远的是《荒湖》里从台湾回来的黄发权,最财大气粗开着保时捷返乡的是《古河潮》里的马驹。最倒霉的被小偷打劫一空连回家的票都买不了的是李俊勇写的《南来北往》中的李明浩。最特殊的是朱雪,她是在小说的文字里寻找着一条回乡的路。这些农民作家笔下的人物,即使是走得再远过得再富,也始终难以摆脱乡土的牵制,而比土地的牵连更难割断的,是从他们生根之地滋长起来的乡土文化心理和故土情感,这些早已化入了他们的骨血,像无形的根紧紧缠住了他们,让他们回归故土,振兴家乡。这种趋同或趋近的写法,也让我们看到了在农业文化背景中构成的情感模式和文化气质,成为农民作家创作深层心理的主体特征。故乡乡土是这些农民作家心中恒久不褪的记忆,是渗透于他们人性人情之中久经岁月冲刷而不会剥蚀的东西。对农民生存感同身受般的焦虑,对农民命运的关切和同情,和农民一起承受着时代变迁中所不可避免的痛苦和不安,成为他们创作中最恒久稳定的个性心理因素。因而他们所表达的“在场经验”更能真实地反映出农民的生存欲求和命运变迁,以及农民精神历程中所必然经历的新旧杂陈的复杂情态。
二、起于民间草泽的韧性和顽强
这些被称为“农民作家”的人大体有两类,一类来自基层的文学创作队伍,他们出生于农家,生长于乡土,经过多年在文学写作上的磨砺,有一定的创作实力,作品数量已达到一定规模,取得了一些有目共睹的创作实绩。他们的身份比较复杂,具有兼容性和多样化的特点,有的基本是属于职业作家,靠写作生存,这倒不一定说他们能完全依赖于稿费生活,而是依凭于写作他们得以进入基层的文化机构,文学成为他们生命价值实现的方式和目标。其中有些人是介于职业作家与非职业作家之间,这种身份的定位也是带有相对的阐释意义的。而另一类“农民作家”则是“在生存中写作”的人,他们本身的生存形态就是一介农民,劳作于田间地头,或是以农民工的身份背离乡土。和普通农民不同的是,他们会将这种个人的生存体验通过精神物化为文学作品,他们大都是写过少量作品的基层作者,或是来自乡村底层的一些文学爱好者。但不论是哪一类人,他们最初都出自民间草泽,从总体的类似性去把握,他们都基本符合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辞典》对“草根”的释义,一是群众的、基层的,二是乡村地区的,三是基础的、根本的。当然,相比较而言,那些“在生存中写作”的农民作家,可能更贴近草根作家的指义,他们非主流,处于乡村最底层,更平民化,当然也就更加边缘化。
这些农民作家如“草根”一样遍地生长,平凡而又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广阔的大地上生生息息,正像湖北作家协会主席方方所说的“湖北有着广阔的乡村平原,湖北的乡村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那些散布在平原和山间的村庄里,有相当多的文学爱好者。他们热爱文学,痴迷写作。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多端,也无论观念如何新旧交替,更不顾生活如何艰难辛苦,他们都不肯放弃这份对文学的热情。为了写作,有人甚至卖了房子卖了牛,写下的废稿纸摞起来比人还高。父母抱怨,妻子不满,儿女吵闹,他们都绝不回头。一写一辈子,自尝其苦,也自得其乐。”[1]这段话正好说明了草根作家两个特点:广泛,遍布湖北各地,甚至有些还是很偏僻的角落;顽强,他们追求文学理想的过程,艰辛而曲折,是以顽强的意志和韧性的坚持而一路走来。
无疑,对文学的热爱,成为“草根”农民作家的精神动力,也使他们有了人生的目标和使命感。在一些农民作家那里,这个目标一开始并不是要出版作品当作家,对有些人来说这几乎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的目标很现实,就像周春兰娘家贫困没有权势而被婆婆、叔伯妯娌们欺负,又被丈夫看轻,所以她要用文学找回人生的尊严。在繁重的劳作之余,“在摇摇欲坠的房子里,在唯一一张书桌上用小学生作业本写出了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在两年内将书稿修改了六稿”[2]。一个农妇为了尊严而写作,她从写作中收获的是不被一般人注意到的精神动力。的确,写作给他们提供了证明自己的机会和契机,给了他们宣泄情感和灵魂的力量,而且也可以让人另眼相看,受到乡民的尊重。
韧性的坚持几乎成为每一个草根作家的特性。70多岁的熊衍锟“一生痴迷文学,当过乡村教师,命运坎坷,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之笔,虽然所获甚微,仍然执著痴迷。”[3]朱雪“生于郧阳偏远的农村,家境贫寒以至13岁便辍学”,“文学是她的梦想,也是她改变生存环境、寻找自我、挑战命运的路径,一条荆棘丛生的路径。”她完全是靠刻苦、勤奋和拼劲、韧劲自学成才。[4]而李俊勇在“多少个寒来暑往,一盏孤寂的油灯下,我开始了遥远的作家梦”,“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的重担压在了我的肩膀上,结婚生子,四处漂泊,但有一点,我坚持着,始终坚守着心灵的那一方绿洲”,“是文学改变了我的一生,是文字让我感受到生命存在的意义”。[5]为了文学,他们许多人都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在与文学漫长的磨砺过程中,曾经因生存缘由的中断而又在不舍中的续接,个中的忍耐和艰辛,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才会体会到其中的刻骨铭心。在多年的寂寞坚守中,他们一点点地建构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空间,并且在其中自尝其苦、自得其乐。
“草根”农民作家因为处在底层和社会边缘,这反倒使他们的创作心态变得沉静而平和,比处在潮流中心的人拥有一份更健康的心性。文学本身就是越来越寂寞的事业,即便是那些大家,也同样得耐守寂寞。身处边缘而不放弃文学,偏居一隅定心读书和写作,寻找自我的精神归属,也就使农民作家的创作有了更纯粹的文学意义。
三、“草根”作家与底层文化生态
不可否认的是,“农民作家”或说是“草根作家”本身就是一个标签,如果没有“作家”这样的后缀,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也会成为生活中没有自我表述能力的“沉默的大多数”。即便长期生活在底层或是农村,熟稔乡镇政体、村乡世相,稼穑农事、民俗风情,对农民的劳顿和生活的困窘,对农民的诉求和希望,还有农民对乡村政体的应对智慧,甚至是在某些利益盘算上的狡猾等等,有着最切近的感受和了解,但他们所遭际的人生命运和现实生活境遇,普泛情况下只能是被别人所表述,被那些与他们有着社会或是文化地位差异的主流精英作家所代言书写。尽管后者可能并不一定真正了解当下的中国农村社会。他们叙写的乡村经验有些是来自过去的乡村记忆和短暂乡间的生活体验,有些本身就是在都市的书斋里想象虚构出来的文本,这样传达出来的乡村现实和农民的生存境遇,必然会有许多的虚饰或遮蔽,并不一定都能产生可靠的叙事效果。
所以,农民作家或是草根作家创作的意义之一,就在于他们打破了以往的沉默和被遗忘、被遮蔽的常态,拿起笔来用自己的作品对生活发声,且不论表达的效果如何,至少是印证了曾经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他们,不是不能表述自己,也不一定必须要由别人来表述,由那些精英或主流作家去代言书写他们的生活。就像10位农民作家,在湖北省作协的培训和扶持下,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每个人都充分地发掘和展现了自我的表述能力,着重于对自身长期积淀的原生经验的表达,成功地将自己的一些个人经验和生命感知融入了小说的写作。像周春兰的《折不断的炊烟》明显地是写个人的经历,突显出女性作家创作中常见的亲历性和自传性的特点。在创作中他们很自信地依凭了本体经验的可靠性,有些生活表述是起于想象的虚拟经验所无法得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文学经验与审美经验的不足,作品的鲜活感和生动性也由此而生。
对这些草根农民作家来说,出自他们笔下的这一部部长篇小说,几乎都是竭尽全力的倾心之作。作协整体推出和媒体的宣传造势,也让社会看到了他们的存在和努力。作为“草根”的农民作家,他们的创作行为本身已成为一个吸纳众人眼球的社会话题,各级机构和媒体都在表达着对底层草根创作的关切,并且强调着这种关切的必要性。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出于某种需要的关注和重视,过于夸大草根农民作家的自我表述能力,也是不够恰当的。各级机构的扶持,媒体的宣传和造势,只能一时地把社会的关注赋予这些以前不具有任何影响力的草根农民作家,这种社会反响短暂而又有限。客观地说,这些草根农民作家的文学自我表述,仍然只是一种弱势的话语,不论是在社会的公共话语空间还是在文学的话语场域中,他们发出的声音依然只是在边缘,他们的作品一般很难获得大范围受众的接受。即使是那些写得并不差的小说,也难以真正地进入到文学批评的公共空间中,因为当下的文学场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市场意识占据着出版营销主体位置的社会语境中,这种要由官方机构拿出人力、财力、物力去扶持的创作活动,是否能够经常性地持续下去,这也会成为许多人心底的疑问。
但肯定的是,这些草根农民作家的自我表述,对改变或是救赎他们自身,对改善乡村文化生态,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这,远远超出了他们作品本身的价值。首先,文学创作之旅给他们提供了舒展生命和张扬灵魂的力量,提供了他们改变自身命运,或是通过写作所带来的发生新变化的可能性。而且从这种写作经历中逐渐累积起来的不仅是文学阅历和创作经验,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动力的累积,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认知,以及对人的尊严的自醒和确认。就如周春兰这个每次在省里开会遇见,总是风尘仆仆地提前离会赶回乡下割麦晒谷的农村女性,却是将写作视为自己的精神动力,“因为这种动力在我的生命里跳跃着一种不可低估的生机和力量,生于土地,息于土地,有了更新的意义,这种意义不再守就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6]写作抚慰了她的心灵,改变了她的现实处境,也舒缓了她艰难人生的伤痛。
的确,他们这种对精神层面的追求,提升了他们生命的状态,让他们走出了以往狭小的天地,不再像祖辈一样只是为糊口而耗尽生命。这种个人精神上的变化,也会成为一种正能量,影响到他们周围的人。像周春兰出书后,令乡亲们刮目相看,也有村民向她讨教如何写作。正如方方说的,“通过他们的写作,向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传达一种生活方式。那便是:在农村,业余时间除了看电视看录像赌博打麻将之外,还另有一种活法,就是读书写作。这是一种更值得尊敬的生活方式。”[7]用文学的写作获取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目标,并且以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和改变底层文化生态,这是草根农民作家的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最积极的社会意义。
蔚蓝: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释:
[1]方方:《湖北农民作家丛书·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
[2]杨彬:《生命的坚韧和希望——〈折不断的炊烟〉,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300-301页。
[3]刘保昌:《艰辛与快乐——〈古河潮〉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314页。
[4]吴道毅:《朱雪与她的〈梅花塘〉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278页。
[5]李俊勇:《留在春天里的记忆——〈南来北往〉创作随感》,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240页。
[6]周春兰:《折不断的炊烟·创作随感》,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298页。
[7]方方:《湖北农民作家丛书·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