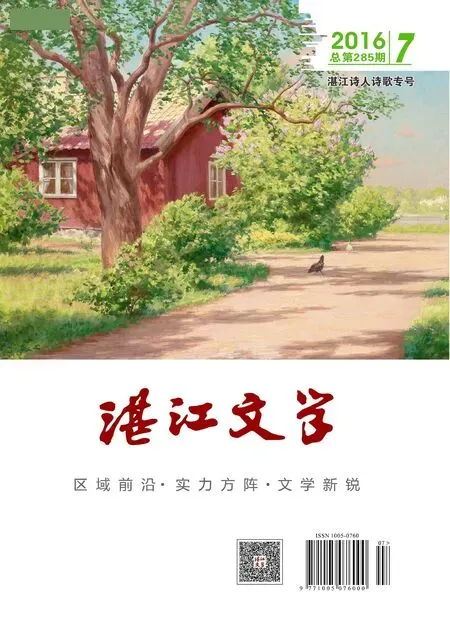在学习诗歌的路上
※ 袁志军
在学习诗歌的路上
※ 袁志军
孔夫子有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不学诗,无以言。”诗歌,被冠上了无数美好的寄托和遐想。她记录了我们青葱岁月里五彩的歌吟,是心灵跳动的强音!有人说过,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或长或短有过一段钟情于诗歌的日子。在自己成长的岁月里,尤其是在那如诗的青春岁月里,无不怀着倾心而炽热的心情,朝拜缪斯。
我的诗歌的写作,最初是在高中时代开始萌芽。我是理科学生(当年的班主任认为我应该选学文科),不断强化训练逻辑思维,但那腔沸腾的热血和感性无以寄托,就寄情于模仿古体诗词,虽对平仄不得要领,但乐在其中,哪怕是打油诗,籍以抒发了满腔的青春激情。及后考上大学,学的工程专业,却喷发了诗歌的狂热和创作的井喷。当时(1990年)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现武汉理工大学)担任水蓝蓝诗社总编,编辑了一本社员诗刊,投寄到甘肃省刊《飞天》,在《大学生诗苑》栏目选发了13个人20首诗歌,这是那个阶段我的诗歌创作最可以称为标志性的事件。
学生时代,诗歌是我情感的出口。
1992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到了一家交通部属辖大型国有企业湛江港工作。工作半年之后,我从见习技术员调到机关总部宣传处企业报编辑部,担任副刊版编辑。在这个平台上,职业(专业)接触诗歌的机会多了,编、改投稿的诗歌机会不少,自己也陆陆续续写了一些诗歌。而当时的宣传处长(四十年代出生的老政工)到办公室质问:这些是诗歌吗?前言不搭后语,逻(狗)辑(屁)不通,我搞不懂你这个现代诗歌……这样的江湖,从这开始,为了不影响“饭碗”,我的诗歌写作绝对不触及现实和工作这个“形而下”的土壤,走那些风花雪月的虚空飘渺。随着职位的变迁,特别是做到了集团公司中层(尤其是作为党委书记),必须要“讲政治”,许多只能内心独白却又无法抒怀的感受,寄予诗歌,诗歌就成了我灵魂的出口,成了自我救赎的文字宗教。
在具体的诗歌写作层面上,我的感受是:
等待灵感。灵感是一个非常玄妙的近乎唯心的东西。
臧克家说:“诗思来潮,半夜五更,便扭亮了小灯,急速提笔,恐怕稍仪迟疑,诗情跑了。”灵感的到来让我们变得手足无措,会欣喜,会紧张,会不安,仿佛连心底那一丝最微小的情感亦被勾起。可以说,灵感只是给我们带来了微稀光明,但却让我们寻着这抹光亮,看到了整片光明。当灵感来临时,会感觉心中涌过无数情思,或许会想到天地,广阔的空间,这伟大的造物;抑或会垂怜微小的事物,以宽厚的仁慈来注视生命的平凡。在充满灵感的世界里,不需要太多理性的驾驭,只要愿意,可以将爱情比成受伤战士对仅剩的一条腿的怜惜,也没有人会拒绝向一株小草俯首称臣……灵感中顿闪而过的情绪,一并决定了诗歌世界中的结局和命运。
当灵感来临时,可能会有这样几种状态:或许你是一个热爱生活、有丰厚生活积累的人,各种熟悉的情境你思考了很久,在你的潜意识中积聚了很久,而在某个瞬间突然膨胀扩张以至一发而不可收拾。或许你在一个静谧的清晨,一个安详的午后,一个悠远的午夜,独自默然静坐。周围很静,你的内心一如周围一般,也很安静,你任凭思绪如烟飘飞,在毫无预兆中,灵感悄悄地扣响了你的心门。又或许你正在桌前冥思苦想而不可得,有些倦了,掬起一捧水,轻轻拍打在脸上,看看窗外,伸个懒腰,风拂过,也可能在涌起的音乐波浪中,激起了脑海中闪过的一丝清明,瞥见了灵感的踪影。
真情投入。除却奇妙的灵感,诗歌创作同样需要真情的投入。歌德曾告诉过我们,诗的骨子里是渗透着情感的,具有抒情的美;放逐了情感,也便放逐了诗。情感是一块调色板,让诗人随心所欲,描绘出构想的意境。运用真情实意进行创作,是一个自然真实的过程,在那样一个情境中,我们吐露的是最珍贵的心声。
肆意想像。一个原始而灵动的生命,内心叫嚣着焦躁和不安,掩藏在平静的外表下,只想要凭借诗歌,去宣泄久已积聚的情绪(心灵的能量),抚平不得宁静的心。因为蕴含情感,诗歌会让我们产生共鸣,产生一种感情的满足,心灵的颤动。海涅说过,读者内心的情感,或者能被作家振奋起来,或者又会被作家刺伤。这也是诗歌能够长久打动人心的独特魅力。
语言训练。每一个诗者必定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前期可能更多的是模仿,日积月累,终于遇到(发现)了自己喜欢也适合表达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
其实,我远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一直在诗歌学习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