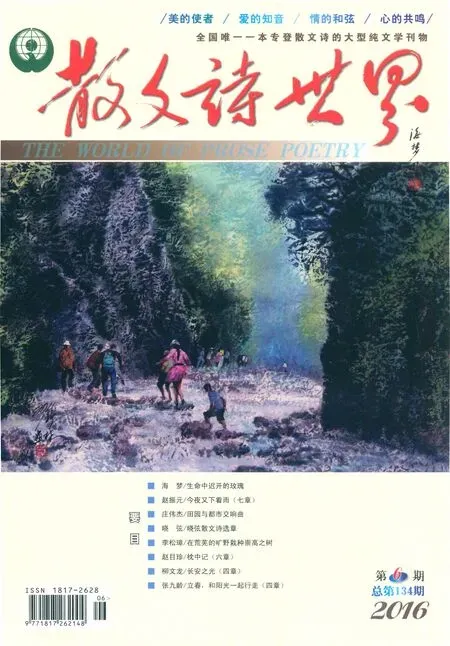碎微的揉捏与塑造(九章)
四川 空 也
碎微的揉捏与塑造(九章)
四川空也
珍 视
一注阳光,斜窗而来,
几多尘埃,活跃、飘飞着,无数影相,印在地上。变成了
尘土,文字,或思想。
我们的生活有许多看不见的东西在我们的周遭活跃飘飞。视而不见,习以为常,麻木不仁,高高在上。
人,活得挺累的,特别在中国,为了竞争,为了金钱,为了成功,为了名望,所有的感觉、知觉都在时光中麻木了、迟钝了,根本不在意一注阳光的妙处。
心灵的尘埃越积越厚,没时间打扫。
就像一本书搁置桌上,灰尘积满,视而不见。
是谁偷走了我们的时间?
又是谁不打扫书本上的尘埃?让它失去原有的光泽和墨香?
偶然,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海的世界,水下400米深处,没有阳光,却有生命。
一个美国女科学家潜到那里,与鱼儿碰触,鱼儿会发出萤火般的光焰,照亮幽深的黑暗。
由此,我的心中大亮:
一个人从事自己内心喜欢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坚持,即使失败或成功,都坦然面对,百折不挠,最后成为一粒照亮自己或他人的星火。
哪怕在阳光下是一粒不起眼的尘土,也要活跃飘飞。
珍视小小的自己,阳光下会散发出不一样的芳香。
有了一炷了悟的感觉,从幽暗的深处,找到通往阳光的路径,轻飘而上。
现实和梦里,都在燃烧——
生命之火。
聆 听
生命之书告诉我,人孤寂的时候,要用自己的双耳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我这样做了,坐在自己的书屋,什么也不做,让自己的心慢慢静下来。一心只听四周的声音。
刚开始的时候,窗外的体育场四周的树上,无数知了一阵一阵拉开它们的歌喉,那声音先觉得是一阵烦,后又拉长、变调了,你停下,我接上,给晒得正旺的太阳一把无穷的力。
此时,没有鸟声,也没有汽车声,仿佛它们都被太阳融化了,四周出奇地静。
我的心在其中期待几许。可是除了蝉鸣还是蝉鸣,它们的热闹比儿时伙伴们的撒野狂欢还要热烈。
自己的心仿佛一下回归到了那时,回到山坡上一片又一片的柑橘林,上面的蝉子也是这样一唱一合地整整唱一个夏天,青青的橘子也被它们一天天唱大唱黄。到了满天星星的时候,它们还唱,只是没有守柑橘的老人唱得那么动听、深情。
我依在树旁,仰望天空,想了些什么,已经记不住了。只是觉得要好好念书,将来离开这个蝉鸣的地方,到省城去工作。
梦倒实现了,但是就从来没时间像今天这样静下心来细听蝉鸣和鸟叫。
它们在我的心里是死掉了。
我在它们的声音里也死掉了。
正如一场大雨,秋后的大雨,将所有的蝉鸣打哑。让它们再也不能在我的耳边鸣响。
知了回家了。
是该回家了。
书上那么说,一到秋天,蝉子从树上,又爬回泥土,冬眠。春天之后,慢慢爬上树,为夏日欢唱。
小小的蝉虫,懂得生命的智慧和规律,该唱则唱,该藏则藏,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别占,占了一个位置,就要为夏天起劲歌唱。
如果命运不好,成为鸟儿的食物,就尽天意了。
自然的声音,有时就需要我们去听。听懂了,明白了,理解了,我们的心才会回归自然,找到自己的位置,为生命歌唱。
生命之书告诉我,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看它是否和自然接近,越接近,越了解自然,智慧才会无穷地增长。
荷 影
灵机一动,去到荷塘。
正值朝霞临空的时刻,心底与天空一样灿烂、恢弘。
满眼的翠色盖过泥塘,微风一吹,卷起波浪,沙沙声响,正如心律,在鸟儿的鸣叫中敲击鼓响。
玉碎的声音。
清清浅浅的流水述说衷肠,述说那段久违的故事。
这片泥土,曾在我的名下,因为扛枪,因为带兵,不久就演变成他人的了。
就像临走时那样,饱含泪水,迎接曙光。
妈妈矮小的身影挺立塘边,如一枝尖荷闪亮,爸爸直立塘中,如一柄莲蓬壮实,左右为伴,默默无语。让我不能回头久看。
荷影,深深地扎根心底。深深地扎根在高楼大厦之间。梦里,不时幻出,柔柔的风,清清的香。
被诗人溢出田田的水水的情怀。
凝视那里,清清的流水,泛出无限的痴迷。
痴迷之中,有我的影子,注视荷花、荷叶、以及莲籽。它们在岁月中好像没多大变化。
我的心思好像起了无穷的变化。
就像那粒石子,抛向水中,倒影立马破碎,久久才能弥合,重复原影。
就在那一瞬间的抚平中,妈妈和爸爸的身影闪出。
从山坡上的那两堆旧坟里,柏树边,我了悟到了生命的真相。
荷影,又在一个明媚的早晨,与我的心灵相通,越过老屋,飘香塘中,时髦的女子,别搅乱了清清的、淡淡的荷香。
让它弥留我的心底,不致溢出。
梦里梦外
梦外,手拿一支笔,漫漫勾填心中的底色,将多余的肌肉剔除,剩下一架光骨,游走纸上。
隐去了许多的细节,包括茂盛的树,高高的楼,架在空中的彩虹,都在一弯河水上,留下浅浅的墨影。
眼前的真实,已荡然无存。
只剩下一架骨头,空着。
有些时候,错觉很美。
线条与线条的连接,重新组合不同的整体。
置放不同的灯光里,让想象去不断地填充。
就像我们正在似睡非睡的梦里,人,突然变成一堆白骨,仍然可以从地上爬起。
飞起一拳将它打碎,不一会儿,它又重新拼接、站立,继续朝你赴来。
与你决斗。
梦里,你长满了肌肉,却不见骨头。
全是一种颜色。
线条与线条隐去了。手里的笔,画不出那个模样。
茂盛的树,高高的楼,架在空中的彩虹,都在一弯河水里,留下真实的倒影。
分毫不差,习以为常,美么?
没一点儿创意,倒立水中,发呆。
一支笔,穿梭于梦里梦外。
织起张张新奇的画布,留给人间。
蝉 翼
透明的,蝉翼,
不同的光线下,有不同的色彩,让人猜想。
新娘,摇晃在树下,薄薄的婚纱,透明。
失去翠色的银杏,有点变深,绿油发亮;
地上的草坪,刚修剪不久,冒出些嫩芽,大片铺开。
欧式的窗,欧式的墙,欧式的房顶,将这片大地全欧式化了。而人的肌肤和毛发,仍是东方的,永远也改变不了。
一嘴的土话,一脸的笑容,秋天的阳光有了些厚重。
蝉鸣早已停止,偶尔在树上还能发现它脱下的衣裳,
一整件,如穿婚纱的新娘,一样抢眼。
在某些暗淡的光线下,婚纱的白,也会变暗,变黑,
那当然是好事,白天走了,黑夜又来,
透明的婚纱,在月光下看,有如一件完整的蝉衣,完美而又轻巧。它被脱在一边,让人联想。
而真正的蝉衣,可是味好药,能给人治病。
我多么想听那些蝉子懒懒地鸣叫,在树上叫醒我的长梦,一阵高,一阵低,马拉松式的,把月亮的脸也从树梢上,拉进婚床。
正是这些时候,来一阵微风,将荷田的花香也一道吹来,悠香悠香的,更让人心醉。
还有那些蛙鼓,可以敲醒我的诗情,沉醉其中,翩翩遇仙。
透明的蝉翼,奔圆月去了,
她的体香,仍留在桂花树上,依稀可以嗅出。
啊,抢眼的婚纱和漂亮的女人,早以脱去了肉身。让我在树阴下到处寻找,她抛弃了的整个夏天。
一枚蝉翼,透明,
轻轻一棱,粉碎于地。
无有,即空;及空,为有,便生万物。
露水和草,又迎阳光,朝霞满天,碧波相映,诗和我又在其中慢慢升腾。
我变成了一枚黑黑的蝉翼,那是白色的婚纱变成的。
芦 花
有人赋予你思想,因而,扛起了秋天,
淡淡的云,飞起的鹭群,
没挽留你的视线,
和沉着的心。
河水打身边走过,承载着阳光的欢愉,
撕碎了你的影子,
还不向你说上一句,
仿佛他们生性就是那个样子,目中无人。
挺立,且听风声,
述说的心事,是那样的轻描淡写,给天空一撇一捺,
暗示了许多无法用语言回答的事情,
让季节读懂。
生命的帆,随它而去,
白茫茫的,如云一般,
滑向生活的岸边。
消失的,只是静默无言,一朵朵诗的语言,淡化了人间。
打 捞
趁着酒力,我打捞着盛唐漏网的月亮,
仍在水中,癫狂,
一管水袖,舞出,无数的思想,给注目的人。
这不是摹仿,是演绎,
是一个朝代的盛世,
在新梦中展开。诗和酒的大醉。
仅凭那双空手,可以上天擒获月亮。
甚至,可以摇动桂树,抖落满地金银。
捡拾富裕的生活,喂养肥壮的诗。
诗仙呀,您在上天,看到了而今的诗人,遗传了您的基因,
趁着酒力,打捞您不曾捞起的月亮。
它已在我的手中,闪闪发光。只是,一件仿制品,如真的温暖。光芒照亮世界。
光 柱
穿过浓密的枝丫,点燃心中的希冀,在静无声息中,美脱去了语言,抛开了描述。
它存在在那里,等你发现,等你发掘。当然是脱去了凡俗,在一种清雅中,寻到的光明。
实在太抢眼了,几片金黄的叶片,告别她的母体,自然飘落而下,
承载她的,不分轻重,一概接纳,当然是坚定的磐石。
托付给他,一种温润的向往。
仅是一瞬,光的温暖,告诉她生命的最后时辰,有不同的味道,
灿然于怀中,即使冰凉下去,甚至化为泥土,她也含笑如初。
到了初冬,本该如此。
一生的光芒,悄然留给了石头,且是凉了的石头。
光柱射了下来,横竖捎来一丝温暖,让她美丽的颜色更加完美。
条条细纹组成的扇片,似乎藏有的光辉,不经意地全部归还于泥土。
走完路的人,与走完一生的杏叶,巧妙地相遇。
能惦记的,当然是她无言的美。给灵魂一丝丝的慰藉。哪怕时光如此的短暂,
那黄与黑的对比,本身就道出了世间奇妙的现象和光影。
悄然涂抹于灵魂之中。是画呢?还是诗呢?
两者之间,谁又能道个明白。
光柱和杏叶,她们早就诠释了如何对存在的关注,领悟才会更加通透、彻底。
宝 贝
无力的风,会摇落你,我亲爱的宝贝,
在这个无人问津的地方,漫漫填写一生的履历。
除了金黄,别无他样,
坦然地给心一些敬畏。
昨夜的雨,让你的脚步停留,依恋少了些许,
也是心甘情愿,为本不完美的世界,洒下一些壮丽的诗句。
我真心地拾取,握于手中,似一卷经书,让人赏鉴不够!
没有重量,似乎又有重量,在心里,
不一样的华丽和沉默的陨落,悄悄给了逃不脱的季节,
一些无言的答辩。
心甘情愿,坠落入泥,
即使枯萎了所有的梦想,又失去了灵魂。
但在你转身的那一瞬,委身于地,金黄映日。
沉甸甸的,不实为另一种洒脱。
丢失的,只是暂时,
拾于手中,再一旋转,
有股温暖敷热内心,在冷冷的时空中,一种神力,凝固永恒。
只好认真地掂量。
无力的风,会摇落你,我亲爱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