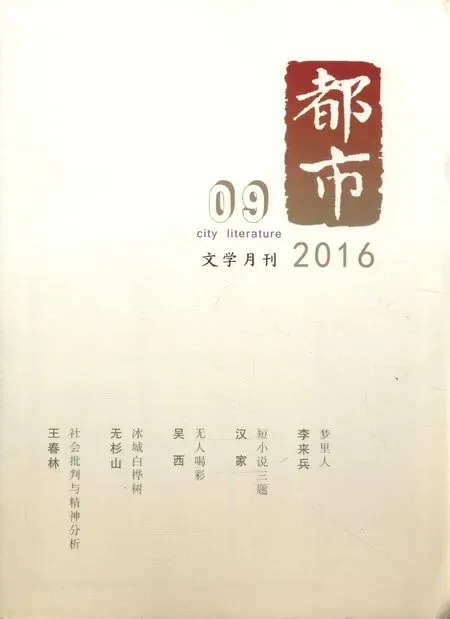梦里人
李来兵
梦里人
李来兵
每天早上醒来,艾薇总会掉过身来,把胳膊环过我的头顶,将她一夜养起的胸脯紧紧捂在我脸上。如果她没有这样做,那肯定是昨晚我们都不高兴了,其实不高兴早已是我的常态,只是不知艾薇怎么总看不出这点来。尽管如此,没有什么能影响我们贴在一起的欲望。我吮吸着艾薇熟透的桑葚果似的乳头,直到她呀地尖叫上来,这个早晨才算有了丝清冽之气。她越过我的时候,还是要意兴未尽匍匐上一会儿:有两个小孩,一个棕色的,一个黑色的,她这样向我复述几小时前看到的,他们一如真假美猴王,互相伸出胖指头,“你是假的!”“你是假的!”又说有个只能看出轮廓的男人整晚都站在她在加油站的床边,她想呼叫,可无论声音在喉咙里怎样上天入地,都不能破口而出,她所有的努力都是和床板的小范围斗争,天亮后,她发现床板上多了个蝉蜕般的人形,可她并没觉得有疼痛感,她拉着同事找遍了房间里所有的床底、门和柜子后,也没能找到那个人。
你已经第三次梦见这样的事了。我尽管忧心忡忡,可也没有第一次听到后那样吃惊。表面看来,艾薇风和日丽,疏懒散淡,可她的内心总断不了波诡云谲,她薄亮的皮肤下仿佛有个真空层,包裹着异世界,我虽然看得见,却永远摸不着。
早上起来的前半个小时,艾薇边洗刷,边马不停蹄向我讲述那些杂七杂八的梦,再慢一步,她就会忘至脑后。我把这些梦收集起来,我们在网上的情侣空间因此显得卷帙浩繁。艾薇每每表情无辜地划拉着手机,问我到底有没有添油加醋?
真是找不到可以救你的药了。我软弱无力地咬着牙。
要什么药,有你就够了。洗漱过后,艾薇的声线重新变得甜美细嫩,最初我就是被这声音吸引的。忘了和你说,你往东走,可能要穿过一片树林,树林前有条浅浅的小河,那片树林应该不会太厚,然后就会看到奶牛场的老王,你不要怕那些栅栏里的牛粪,你过去找到那只缺了半个耳朵的黑白花奶牛,前半夜都是它和我说话的,你问它到底说了什么。
它和你说了半夜,你都记不住一句?
我可能同时梦到别的了。我只记得它的眼神,里边有两堆篝火,我攀着它的眼球,可是太光滑了,抓着它睫毛的手好像很快就抓不牢了。
你在奶牛的眼球上攀岩?
我大概要到篝火旁边去。
篝火旁,很多人手拉手又唱又跳?我觉得自己像个抵在气球上的钝钉子。
艾薇摇摇头,不知道。
走的时候,艾薇正啪叽啪叽往脸上敲丝瓜水。灯光把她的额头照得油光闪亮,她敲完脸蛋,把剩余的都顺着颈部的曲线抹了下去,她的脖子鹅颈一样修长性感。细长的酒窝仿佛嗖嗖蹿升的小火箭。
那个老王是谁,先前就认识?我撩起碎花布拼接的门帘,那是她妈给我们专门做的,门帘在胳膊上耽得时间稍长,我困得心烦意乱。
我就记得大家都叫他老王,你去问问。
大家?难道在这个梦前,还有连环梦相辅相成?我头疼得厉害,幸好撞上一群路过巷子的凉风,我迎立在那儿,希望它们从眉心正中穿过去。
我在怀信街的路边小摊买了几条现炸麻花,最近艾薇总说她胖得太不像话,拒吃一切油腻之物,但除了鸡肉和鱼肉,她几乎没排斥过任何,她从十几岁开始吃鸡鱼过敏,脑袋动辄就像使了紧箍咒,她抱着头团团乱转。我告诉她一个小秘方,每次她疼痛难忍,我就把她揽进怀里,弓身吻到天昏地暗。是不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奇方?艾薇懵懵懂懂揉揉头顶,真的不疼了啊,绝无仅有怎么讲?
我给艾薇打电话,她已经在去加油站的公交车上。早饭我去了解决,她说完,就挂了电话。她大概被挤得够呛,呜哇一声的尾音清脆尖利。我嘴里叼着麻花,告诉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城东,他虽然没说,但我看得出,他和我一样怀疑城东的不着边际。但我只能这么告诉他。车顺着最宽的仁德路到了高速收费口,我只好就在那儿下了。我混在许多汽车后进了匝道,然后看着它们飞快将我抛弃,趁路上没车的当儿,我发动脚步跑到对面,跨过护栏,从坡网找了个撕开的口子钻过去,几头黄牛看似悠闲却毫没松懈地吃着脚下,盯着网里,它们肯定以为我是一团浓缩的草料,不远千里向它们暗送秋波,我浑身鸡皮疙瘩地挺在原地,我大喝引来了扬着鞭子的牛主人。
姓王的奶牛场?他抓耳挠腮地想了想,你还是到下边问问吧。
下边两公里内的确有几家奶牛场,可除了遍地的苜蓿,它们和艾薇梦里布置的河林无关,我只好继续沿着荒僻处行进。在上了那个土崖后,远远看到一湾水,河岸上也有细密的树木。当我支点不稳地终于将自己带过去,却发现后边是一片更无边无际的玉米地。
艾薇,你骗我?
我没有,我真的听它絮叨个没完,你是不是再换个地方。
我已经累得天旋地转了。你来接我?
没想到艾薇还真请假打车过来了,到了高速口,她又不知该如何为继了,要不要报警,让他们用手机信号定位你。
我气得牙齿嘎嘣作响。附近还有空军部队呢,你直接要架直升机全天下都一览无余。
艾薇在加油站一天一休,晚上和同事就睡在加油站那间工作室里。加油站包吃住,每顿饭都有十元补贴,晚上的伙食简单到只有稀饭和馒头,这样她们就宁愿自己吃泡面,或在附近买米线刀削面什么的,艾薇不希望我去加油站,比较晚的时间,也不许我打电话。我想见到她,机会只有她外出买饭的时候。
到那个面馆,要过人车汹涌的怀安街,同事担心穿着工作服不好示人,买饭的差事总是艾薇的,艾薇乐此不疲,除了这是个放风的机会,她很兴奋身上的反光条人见人看,车见车躲。过了马路,是城市气息不足的大肚子,花树和灯光仿佛缺少观瞻而心思阴森地静悄悄,艾薇警惕,又忍不住好奇地向纵深处瞅,她大概预感会有只华彩抖擞的波斯猫跳将出来,尽管那只是个瘦小伶仃、像个破布娃娃的泰迪。
树丛里忽起一阵滚石般的痛哭,艾薇吓一跳,蹲下身,看清那人坐在地上,一条腿别在另一条腿下,边拍边哭,旁边散落着美目镜和包,艾薇捡起来递给她,有了听众,她的指责更加如日喷薄,这让夜晚的广场每每泛起幻觉般的低微回响。她称泰迪为没良心的,而且那只指一不二的胳膊迟迟不肯落下,小泰迪心意缭乱地沿着马路牙,时不时回头看下她的脑后。怎么了大姐,小狗狗惹你了?
不是她又是谁。看起来有四十多岁的女人向泰迪的方向拧拧手指,带动胳膊和身体也旋了半圈,你问问那个没良心的,妈妈我不过是给你戴个耳钉,她就把自己的耳朵硬生生拽破了,她还撒着欢儿地跑,说不要就不要我了。你要还认我这个妈,你就过来拉我一把,扶我起来,你看你看,她怎么舍得哟……
艾薇笑着说,我虽然什么也不是,我拉你吧。女人推开艾薇,不行不行,她不拉,我今天就不起来。
艾薇要过去再说服泰迪,撞到了我。她们要是骗子呢,我撸起她就走,艾薇一步一回头,一直没放弃最后的结果,她说如果那女人是,狗狗怎么会骗人呢,你没看到,她也是需要个人牵线搭桥吗?
我告诉艾薇,这样的把戏,人们多了去了,她猛地呀一声,想起可能已经超出买饭应该正常的时间,大步向面馆跑去。半小时后,我接到艾薇从加油站打来的电话,你还在广场吗,我刚才忙着跑,没看到那娘俩是不是还在广场大眼瞪小眼,万一真遇到坏人呢。你能不能帮我过去看看到底怎样了?
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内心寒彻。你的眼里只有一条小小狗?你还欠我一个“老王”!
什么老王?
你心里知道。
我不知道。电话发出响脆的啪嚓。
我想冲到加油站去。但我呼呼睡觉了。我想着艾薇笑靥如花地和同事分享所见的百般精彩,胸口一块青石浮起又落下,拖着把我塞入令人口鼻窒息的梦里。
我还横在被窝,门口闪进一缕亮光。乱纷纷的卷发垂下来,有几条直接伸进我的鼻孔中,我打了个喷嚏,艾薇不躲不闪,她凝神看我,总是那样充满欣赏,嘴角的笑意像泉眼温和而富有感召力,她一寸一寸有节奏地俯下来,整个脸虚化为黑白两团,我分花拂柳向她挺进,那是个甜蜜的巢穴,我跳进去,就再也不愿起来。
我们就那样又睡了半个上午,我不敢惊扰她,胳膊一动不动垫在她脖颈下。
艾薇醒来,我已做好了午饭,我出去买了她喜爱的玉米辣肠,五个灌汤包子,觉得不够,又点了一份凉拌土豆丝,我计划动手做蛋汤时,她从被窝向我伸出胳膊。可别冻感冒了,我忙把它掖进去,艾薇的手执拗地勾牵我,加上眼神,我只得放下活计。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离不开你。
我们永远不会分开。我坐起来,摸着她绵软的脊背,快吃饭了,大概已经凉了。
让我吃了你吧。艾薇的眼里,缱绻未退。
艾薇边吃包子,边和我说起加油站的事。我没怎么听得进去,我问她昨晚又梦到什么了,多了,她把蛋汤悬在半空,眨巴着眼,一口气数了五个梦,由于语气太连贯,我还以为是两件事呢。
以后我还是先向你汇报梦。
不能说汇报,你讲给我,我把它们记录在空间里,这样等我们老了就像看自己年轻时主演的电视剧。你又梦到我了没?
艾薇的嘴慢慢蠕动着,有。我梦到你赤身裸体坐在水库边的石头上,我想过去,可是被青草缠住了脚。
虽然被她梦里这个情色意味颇浓的形象噎得够呛,可艾薇口气挚真,一点都没有猥亵的意味。我过去揽住她的头顶吻了吻,你已经十几次梦到坐在奶奶宽大的窗台上,你为什么总是回到小时候?
可能是我想奶奶了。你不知道,她那时对我和弟弟真的很好。
她活到现在有一百岁了吗?我眼前闪现了一下我奶奶,我从没见过她,我爸爸说她是个儿科医生,她扶着屋中的顶梁柱休息,晃动的中间,一条胳膊就给晃折了。
多了吧。艾薇说。她张开嘴,我这半颗牙,和你说过吗,是小时候掉到旱井里磕掉的。
知道,你还和十个女生扎堆挤过那个同学家的吉普车。
艾薇呵呵笑起来,这不是梦到的。
我还以为你所有的都是梦里人呢,没有现实,只有梦。
这是什么话?艾薇警觉地抬起头。
没什么。我淡淡的,去收拾桌面了。
午后我去单位上班,顺便上网把她昨晚所梦记录下来,艾薇打电话说她正陪她妈逛街,可能晚上不回去了。我吁了口气,马上拔出烟。我们一起时,艾薇就让我戒烟,后来或许觉得太过武断不好奏效,就常凑到我的嘴边检查,自然,最后她的嘴也钻了进来。
当我集中精力回想,才一一看清那五个梦:湖底有条鱼,眼睛水晶般昼夜生辉,一群布偶在柜子下舞着鸡毛掸子追打,王尔德的绿乌龟拍她的腿,许多鹅卵石浮起来变成了小船(原来我把这几个梦合成动漫片玩具兵总动员了);她拉着弟弟的手拼命跑,他跑不动了,赖在地上,把土蹬得簌簌掉落,悬崖就是奶奶的窗台。
我盯着这些梦,学艾薇摸到一片斑斓的冰凉。艾薇总是梦到格列佛游记式的大人国,是现实太强大,还是她内心深处果真另有奇异?她自己并不能解释,我的解释也算不得自圆其说。但我注意到这次出现了一个棱角分明的名字,王尔德,她的同学?初恋?还是身边的什么人?
或许就是她小时候的邻居,远房亲戚,或纯粹的路人甲。问题是这个名字我从来没听她提起过,我想起“奶牛场的老王”,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人。我想给艾薇打电话,可是和她妈在的时候,她有着同样的规矩,我和我妈在一起能有什么事呢。我认为这肯定不是总堵在我嘴上的那个嘴。
没有艾薇在,时光一如烧热的沥青灼烫黏稠。我在街上溜达了一大圈,也没觉得有什么好做。虽然盯着路边的烧烤摊,但我脑海反复翻炒艾薇的那个梦。绿乌龟说明那个梦的场景在家里,而艾薇肯定在那里出现过,我看到她围着那个圆形笨拙的大玻璃缸,从脖子到耳根洋溢着水汽般的微笑,这时王尔德在里间会怎么叫她:艾薇,还是薇薇?不,他不知道她的乳名娟。
我不太清楚我几点睡下的,总的来说我睡着了。半夜我醒来一次,但坚持没起,我摊开四肢,闭上眼,觉得现在到见到艾薇前的时间还是结实的。
或许是昨晚过度耗费,再睁开眼,已经是上午十点多。我抓着头皮,好容易才想起昨晚都干了什么,我坚信了什么,但这一切落空了。艾薇并没有出现在这个烦乱的早晨,她肯定直接去加油站了。手机上也没有她的任何信息。我给她打电话,确认事实的确如此。慌忙中,她似乎提了一句泰迪的女主人。半个小时后,我才完整地问到,艾薇说她在路上看到那个女人了,穿一件火红的短款呢服,显得浑身暖洋洋的,但旁边没有泰迪。
你说那小爱爱会在哪呢?艾薇应该在离加油机十几米外的那个厕所旁,上岗前,她就是从这个基本常识开始了勤学苦练。
我不知道。你还是很挂念那只小狗?
嗯,你没看到她俩都很孤单吗,那个大姐我只看到背影,说不准她的前脸满是哀伤呢。
她或许又嫁新人了呢。
你这是什么话?过了会——我很好奇艾薇这次说话经过了思虑,过了会,她沉甸甸抛过来一句,你就希望这个世上的人都阴暗如你吧?
——我阴暗?
那你怎么那么说大姐?
艾薇,这个世界说大很大,说小也很小,可我常常摸不着我们的世界哪里是边缘,我们始终生活在雾海中,我们虽然天天执手相握,可我看不清你,你的爱是什么,鸟还是云?我不知道你的胸怀里给我分配的是一把椅子还是一座喜马拉雅,你是世外仙姝还是人间圣女……
我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也不发达的普通女人。你什么都别说了,我知道你积累久了,大姐我自己去找。
我到了加油站。我认为艾薇以为我这就算去了,实则我在很远的地方就把自己逼停了下来。许多车环绕在加油机周围嗷嗷待哺,我伸长脖子等艾薇露头,那些车走空了,只看到那个面色粉白的同事。我正好过去。同事有些抱怨,车越多她越不在。
她去哪儿了?
说请二十分钟假,上厕所。
我看看旁边的厕所在心里笑,艾薇每次撒谎都慌不择路。想着此时她正在广场焦急奔走,又莫名忧伤起来。她请假去高速路找过我,现在却是为找一个陌生人。
差五分钟还没有她,我打算不再接着躲下去了。我快步朝广场走去,在健身区与艾薇擦身而过,她趔趄了一下,但是不至于跌倒。好像在那边,她随手指了指身后,看看手机,我只有一点时间了,是回去续个假,还是你接力?
你说呢?我放缓声调,目光调侃地盯住她。艾薇的酒窝细长了起来,眯眼,向我凶狠地啵一下。
但我忘了确认那个巨大的扇形空间,哪个点至少是哪条线含有“大姐”。视野里人不算少,风晃动着东南角那片树丛,惊得偷栖枝头的风筝拔脚就走,树下的围堰积满了去年的落叶,铺着彩色鹅卵石的小径仿若阳光堆砌的河流,把林间的幽静鼓涌得意志松弛,马路的喇叭声没头没脑钻进来,每次都像来不及湿脚的潮汐。隔一段就会出现一副石桌凳,上面镶嵌着姿势不同的背影。我没找到那种火红色,也许是陷入了思维定势的窠臼。那么只有从她的身材和体型着眼,我旁若无人地快速掠过每张桌子,加上蓦然回首时足够小心翼翼,难说有什么意外。两个模样相当的女孩牵着一只穿花肚兜的泰迪,它的尾巴也被数个发绳扎成朝天辫。泰迪始终努力看我,不表示它和艾薇的小爱爱可以叠合。
我穿过树林到了马路上,这表明我在放弃寻找,即使加上艾薇那双目力浅显的大眼,和她种在心里根深蒂固的热切,也不好从前面的林林总总中一眼就析出我们所要的。我从路边的水果门市买了支小布丁,觉得与其这样无望地寻找,不如也到椅子上去等等时间继续加长一些,我要的是艾薇,虽然我不确定艾薇是不是怀抱同样的希望。
就是在这种无心插柳的状态下,我好似看到了那个女人。广场南端的舞台还贴着不知哪时的红色满幅背景,它下边台阶上的地毯也因为一直没有拿掉,显出一种生命力萎缩的疲态,从西南方斜倾的热力充沛的阳光正好搭上另一条边,这让三角区里的一切都含混而渺小。不是那个人的动作连续又夸张,我很难想到那里本应也作为重点扫描区域。
我马上过去,我在林边看不到的舞台西端站了不少观众,他们的脸上布满深浅不一的笑,目光却毫无例外直勾勾指向舞台中央:那是一个人的舞台,她眼睛一眨不眨盯着额头上方,额下的部分没有不在颤动的,甩起来压迫得嘴唇嘟成呼哨的脸庞,同样跳荡不羁的胸脯,不太长的腿明显踢踏乏力;她应该和着《小苹果》的曲调,每个动作都有节律地重复三下。她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舞蹈中,即使脸上已经水光粼粼,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她目光坚执,神态纯真,好像有条安宁又自由的道路在前面越来越宽。
我不敢贸然闯上去,尽管我确定无疑这就是艾薇说的“大姐”。但观众们好打扰,一个人的奋勇,也是一个人的单调,他们总有看厌的时候,我拉出一位大妈,给了她支烟,因为我看到她鼓掌的时候就把烟叼在嘴上。那是谁家的大姐?
不知道,昨天就开始跳了,一看就疯了,男人们都盼着她脱裤子,我把那几个灰鬼都赶回去了。
这时,背后果然传来一声声“再脱,再脱!”他们都为此前进了几步,但还是不敢完全到她跟前去。“大姐”已经将那件火红的外套脱了,肉粉色的衬衣下,过于肥大的胸脯吹弹可破。
大妈,过去拦住他们不行?
切,拦得住这群狼?她扫兴地往后退,你是谁,哪的,管这干啥?
我?我看着自己的鼻尖,梦里来的。大妈赶紧唾了烧剩的烟蒂,落荒而去。
我在广场角落给报警台打了电话,然后听着附近有警笛声响起,才缓悠悠回了出租屋。
我问艾薇,她怎么就意识到这个女人会有问题。艾薇迟疑了下,直觉?女人的敏感?大概还有我在梦里见过她。
我说这可是你梦里的人第一次出现在眼前。
对于我不是。
你还见过其他人?
你这么说不客观,不是我见过,是他们本来就在那儿。
那是一个什么世界。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那是梦还是生活?
梦里的一切也是生活。我给她最后这句话惊住了,但我还是觉得不能琢磨透。艾薇难道真有两个世界,而且两个世界都是真实存在?
王尔德是谁?
你别再提那些乱七八糟的了。艾薇改换了一副模样,脸上笑意四起,腔调也变得温柔如猫,她抓着我的膀子,我们几天没见了,想过我吗?
我想你没有一分钟隔断。
真的?
你不相信?
嗯,我知道,你是最好的那个。
还有其他人可类比?
你又来了。不理你。艾薇跳下地,可我才不许她就这么轻易了呢。她假意挣扎一下,我们双双滑进被窝。
醒来后,艾薇又说起加油站,昨天有个没挂牌的宝马,司机加了二百块钱油,身上却只有一百,他说信得过他就等下次送过来,电话也不留一个。马后炮,是同事答应的,她知道,也不好怪她了。
加油站的规矩,加油员不论是谁出差错都是有难同当。这意味着,艾薇毫不知情又跟着把几天省下的饭前亏了出去。你有责备她的冲动?
我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
那你们就悬崖勒马吧。
悬崖勒马?你让我从那里出来?我重申不想让你养活我。
不,不是养活不养活这个老话题。你不觉得你们都沉浸在梦幻中吗,除了正常工作,你们都整天干什么,加油站现在到处弥漫着梦幻气息。
我们整天,不都是在正常加油收钱,收钱加油?
我又觉得被什么卡主了嗓子。咳嗽了几声,有些东西反而坐进了胸口。人生有多少不适,表现在我和艾薇间尤其明显。我觉得内心尖利的部分没有那么锋锐了,或许是我也绕进了艾薇的气场,但谁说这样离她不是更近了一步呢。
这样,她却更高高在上了。
艾薇一点都看不出我,我只能解释为她一点都没有看,我就是紧贴着她却只在她表面漂浮的小舟。我们可以在身体的汪洋里尽情游弋,但却永远到达不了对方的海心。那个地方存在吗,它是一片浩茫的广宇还是只有一块千疮百孔的礁石?你爱我吗?嗯。你是我的好老婆。你也是一个好老公。我不好,我总是和你生气。你是情绪化了一些。只有一些吗?目前是。
我会努力加油。我放松地笑了一回。今天周末,咱们出去玩会吧,你想去哪里。
哪里都行。艾薇恢复了平常若有所思的样子,显得心不在焉。要不我们一起洗衣服?多久没整理家了。
你在想什么?
我妈不知怎么样了,我想带她到医院看看那只胳膊。
那我们还洗衣服吗?
还是出去走走吧。
你到底最想干什么?
那就先整理家。艾薇立即动手去拆窗帘,然后看我妈,有时间的话,我们再出去转。
我们租这个屋子快三年了。不知觉已攒起一个家十足的烟火气,炕上最底层的地毯是她和弟弟要的,我觉得直接在上面放地板革需要铺垫,从单位带了许多报纸,因为地板革没有心仪的花色,我们跑了好几家店。潮虫把地毯撕开几个洞,翻上好多土粒,有几张报纸写了字,仔细辨认,都是我的,还有一张我的画,两个背影牵着手:我想起三年前那个午后,阳光从门头的窗户上直射进来,艾薇在地下收拾碗筷,我靠着被褥涂鸦,那时我就在怔怔地望着我们的戴河和草地。时光似乎瞬间乾坤大挪移,我们依然在这里,但爱情已经老去三年。艾薇,记得石塘路的晚上吗,我们在泥泞的路上边走边吃猪头肉?那是你提议买的。
最后我们进了那家店里吃了朝鲜冷面?艾薇习惯性地把一只虚握的拳头抵近太阳穴,另一只手放在这只的臂弯上,这说明她在进入记忆。如果所有一切都可以忘记,我们的戴河必定像肌理一样已经铸进身体。
我们还买了糖炒栗子。街头那口热气腾腾的大锅,杆子上吊着电灯。我进一步引导。
12块。艾薇脱口说。
对,我呵呵地说,谁说你健忘呢,我们的都还在呢。
谁说我记得了。艾薇的脸上漾起兴奋的潮红。我们没有坐上最后那天的邮轮,现在想想还是遗憾。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重游,我隔一天就得上班,否则工作又丢了。
可不是这份工作太难得了,不过神游一遍也是好的。现在满眼都是你赤脚走在沙滩上,还有水里那个劈波斩浪的外国大胖子,原来是个女人。那群雪团似的海鸥,它们就从你的手指尖飞了过去。
我们捡了很多贝壳,还专门买了珍珠粉,在那个小店你第一次吃到蛏。
我最记得的是,咱们一起和那个店里的老板吵架,我没吃出煮熟的玉米居然真是酸的。
嗯,我们的故事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你知道我最想你什么吗,趴在你的背上,暖和又舒服,要不是怕你累,我就在上面睡着了。我经常做这样的梦。
我没有记录。
那是我忘了和你说。
我以为你只会梦到赤身裸体的我。
周公说,那是不祥之兆,一般会有病,每次都灵验吧。
我略加认真地想了想,好像是。那么多感冒。现在我再背你。
咱们干活呢。艾薇加紧动作,很快就要收拾完了,也不知我妈同意不同意带她去医院。
她怕咱们花钱。
她全身都是病。有一天我梦到她没了,我哭得稀里哗啦。
你不能这样梦她。
没有办法,我指挥不了做梦。艾薇的思绪忽然在这儿转了个弯,你真确定那位大姐是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那么最少这几天她安全了,但小泰迪呢,它会怎么样?
你能给它梦个善终的结尾吗?
我说了梦不由我。
你确认这不是气话?
你老婆我从来都是乐天派。
我打定主意今天出游,太久了,我们那部动辄就熄火的老桑肯定也如箭在弦。只是祈求我们别在医院耽搁太多。上了车,艾薇给她妈打电话,说去接她,我听到她妈说哪儿都不想去,坐着挺舒服的。你弟弟正教我在电脑上打麻将呢。艾薇回过头,征询我的意见,老人家至少今天感到不需要,我说。艾薇仰下身,那我真的没什么事了。
我们这就走?
嗯。艾薇闭上眼,你还是先在城里绕绕。干什么,我问。
我看看我的重心稳不稳。
不明白。
没事,你绕绕吧。她继续眯起眼,向我猜测这是不是天合街,这是不是信用联社,这是不是开元。
我故意不作声,艾薇笑着打我一下,你不说话我怎么知道对不对。我说你就躺着做几个轻松点的梦,猜那个干吗。
在汉芬超市的小巷里,我下去买了一大包吃喝。阳光在楼体巨大的玻璃弧幕上闪射如火,我的影子很有力地印在黄土上,许多脚步在上面落叶般卷来卷去。右手的米线店和左手的修脚屋总是同时出现在我们的中午,我们走下来的那条小路,一棵粗壮的臭椿常年神色严峻,树下的门里有对双胞胎,那辆遮起纱顶的婴儿车,我总觉是推着他们的爷爷亲手做的,我们刚到这里时,从旁边坍塌的土墙上发现了一株枸杞,艾薇摘了几颗,用手擦了擦就扔进嘴里。
我都梦到我们在水库边了。
我们不去水库,找个陌生的地方吧。我拉上车门,但实际上我也不知该到哪儿。但意识告诉我,我们在水库方向的边线冲刺。
我们的好多第一次都在水库,但第一次做爱不是。艾薇说过至少两回应该在夏天的青草丛里试试,我不知她为什么会想到那么极端,艾薇想象力的毛发总是不从毛孔里长出来。但她的三庭五眼比例极其标准,除了臀部稍显突出,她算得上是八个半头身。我总是力图纠正她走路摇摆和站着含胸的姿势,不到两天她就会大叫头疼。
艾薇睡着的时候,脸上山明水秀,眉眼笑意氤氲。我摇摇她,到了。到哪儿了,她起得生猛,差点穿过车顶站起来。我正梦到大姐要和我说话了,她原来抽烟。
应该到市界了。艾薇斜倚在我怀里,我在她的脑门上又揉又吹。车子在最后一下忽然冲不上去了,我干脆就在那里熄了火。
我们站在半坡上,鸟瞰刚才路过的村庄的全貌。前面向上倾斜直接蓝天的地方,给我们留下足够多跋涉的空间。你梦到她怎样了,我问。
我躲过好多狗才到了她身边,你都见过她了,可我怎么都看不清她的面孔,我就问她你的睫毛是不是假的那种,她的嘴唇很厚,牙齿小了点,唇上有淡淡的胡髭。
我根本没看到她那么细。而且现在我也怀疑,她就是你说的那样。
你进入我的梦里了?我还梦到了我妈,她每打一张牌,就向我眨巴几下眼,好像是要我别告诉人家她的牌面。后来我就觉得是她和我两个人打麻将。
给你妈打个电话吗?
不,我觉得她这时很好。
我搂着艾薇的腰,带着她往上走。她减肥有效,正好够我把手绕半个包围,插进她那边的兜里,她的身体一涌一涌的,传导给我极幽秘的惬意。艾薇躲避山风的时候遇上我的嘴唇,她的唇薄俏温软,里边湿润润的红火苗随时会烧得我战栗起来。
这是十月靠后的几天,山坡上的梯田密布着短尖的玉米根茬。大团大团的白茅系在田埂上,像盛典仪式前等待号令的气球。艾薇在西山出生玩大,东山上的许多植物仿佛都是从小时候映射过来的。她抓着高过头顶的沙棘树让我拍照,我们还发现了几个黄鼠狼洞,看到几片蛇蜕,因为没有受到侵扰,这里的蚂蚁个头都特别大。但坡上有被烧得矮了一大截的杨树,再高处的树木却傲然笔挺,沿山峰的走势成行成列。我们不知会不会走到那里,从那儿翻下去应该就是另一个市域了。你希望那是哪儿?我问艾薇。
艾薇捏着下颌,眼睛怔住,埃内斯特·勒古韦,有这么个地方吗?
这是你梦到的名字?我离开一点艾薇,握住她,恨不得目光变成扫描射线。这名字奇怪,它不是一个外国作家或科学家,而是一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从哪儿记住的。但它肯定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地方。
艾薇,你真是一座无穷无尽的富矿。这么多年我都没能完全了解你。
你说的是哪方面?你了解我那么多干嘛?
我们相爱,我就得尽力知道你,你说不是?
你能进入一个人的心,可永远钻不到他(她)的大脑里去。我就没有把你开凿得体无完肤的欲望,我觉得我们这样挺好。
那你是爱我的吗?
爱啊。你温纯敦厚,善良自信,性格细腻,主要是我们总有美好的感觉。
我看着远处,你好像说得一点没错,可我总觉得空得慌,为什么。
我不懂你的感觉。我们还是别说了,你看那边,那是不是一座庙,还有人对吧。她搭起手,迎着阳光望对面山腰。
我顺住她的目光看去,果然看到和山色差不多的一座白茬庙,活动着的人大概是在施工。从附近看不到上那儿的路。下边是一条宽大的河床,已经干涸得砂石历历。河床一直向南隐入千回百转的峰群。
我们原地坐下,尽力贴近,好形成一个避风港,这样快速吃了点零食,又喝了半瓶水。脚下已经是个很深的沟壑,我站在边缘望了望,下边还有残存的绿色,山谷间羊群婆娑,牧羊人好像戴着顶老式军帽。沟谷再往上,山体又弥合了,从我们斜前方铺开一个四十五度左右的缓坡,如果要上顶峰,那不失为一条捷径。我们上去不上?
你背着我吗?艾薇脸上绽出那种浅尝辄止的坏笑。
我深呼吸一口,蹲下了身,艾薇却没上来。算了,你就是青松,也会让我这大雪压垮的。我们还是走着公平。她钩住我的手,就像我们每次出游那样,但是路边总有东西吸引她脱开我,一朵憔悴的野花,或一只蹦不起来的蚂蚱。
看起来坦荡如砥的坡面一旦踏在脚下并没有那么平顺,土质的山体偶尔会现出一条类似星球皱纹的断裂,这证明我们始终在一种看不见的运动中行走,而我们的运动,不知又有谁能看在眼里。
我迎着漠漠刺脸的风,半弯腰前行。一失神才会觉察出手里没有了艾薇,我以为她又找到了什么宝物,也没停下,她要是肯于跑两步追上来,我就背起她,我们上不到峰顶,至少我们的气概指着那里。
可我走出几百步也没听到艾薇的脚步声,回望过去,视野里也没有她。我连翻带滚,边跑边喊,既没有她的身影,也听不到她有声音回应,我狠掐自己,抬脚踢得泪眼模糊,这是梦?
我一路跑到车前,没有她,立马转身跑进村庄,所有人都被我流星赶月的样子骇得面容失色,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我又冲上山坡,差点在那条山谷边飞翔起来。
你知道我那天穷尽想象,使用了所有办法。可直到太阳虚瘪,化作漫天霞霭,夜晚潮水般将大地淹没,也没捕捉到艾薇的丁点蛛丝马迹,我闭上眼,绝望地认为,她只是回到了梦里。
(责任编辑梁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