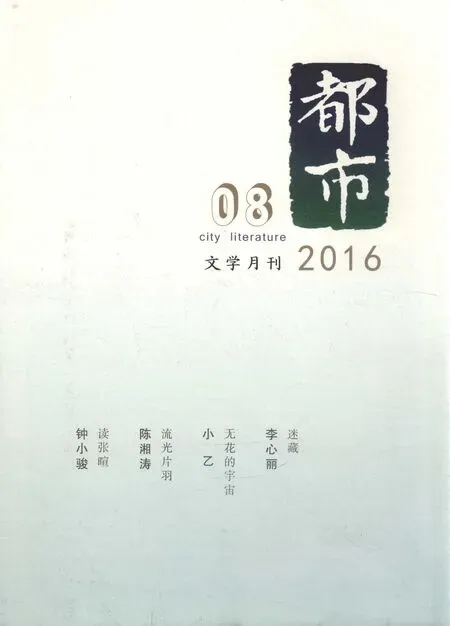雁门有苍狼
——评张卫平的散文集《心中的菩提树》
张玉
雁门有苍狼
——评张卫平的散文集《心中的菩提树》
张玉
我认识张卫平其实时间不长,大约在我2014年签约山西省文学院,才开始在一些会议和活动上见到他。当然在此之前,我是看过他的作品的——是看过,而非读过,因为我看的是电影而不是书。那年冬天,我们在汾阳贾家庄,晚饭后大家零散在大厅里,张卫平谈起他的散文、小说以及最近的剧本创作,他侃侃而谈,谈到文字的秩序和力量,他认为不要追求形式的华丽,而要直取核心,句子要像北风一样寒冷直刺内心。我直起身子表示赞同。直至今天,我写这篇文字时,又不禁想起了他的话,以及他博客的名字:“北方的狼”。张卫平是典型的北方男子,声音洪亮,体格粗壮,更兼一头浓密略卷的须发,确实有几分狼族的模样。我这样想的时候,眼前浮现出一匹毛色青灰的狼,孤独地蹲踞在雁门关下,向着月亮发出寒冷的长啸。
作为一匹狼,张卫平关注的东西粗犷、桀骜,他那质朴而充满野性的语言有一种生猛的血的味道,具备了撕裂咽喉的穿透力。雁门是一种征伐,菩提是一种救赎,它们都是他的本色。他的文章意象简约,内容密集,思想天马行空而清晰有序,写作激情被置于一种理性的思辨之下,这是一种语言和思想的秩序,他的文章往往能在短短数百字间表现出开阔的境界和宏大的视野,有罕见的高度。
一
“登上雁门关关楼,遥望苍茫群山,心中会慢慢涌动一种久违了的感动。夕阳正沉向远山,冷风挟带着远古的羌笛声直面而来,耳边似隐隐听到一波一波滚滚而来的喊杀声
“雁门关似乎天生为战争而生。刀与刀的碰撞,迸溅的除过火就是生命的鲜红。雁门关不相信眼泪,雁门关遵循的是胜者为王的道理。一个王朝在雁门关前倒下,另一个王朝随后在雁门关上挺立起来。雁门关上始终刮着强硬的北风。”
这是我在张卫平的新作《心中的菩提树》中读到的一段话,这一辑的回目叫做“遥望雁门”,这几篇有关雁门的章节,是全书中我最喜欢的文字。它确实像一阵“强硬的北风”,将张卫平写作的艰辛与关隘吹送到我的眼前,他用全部身心所承受的艰难的青年时代和北方古镇的坎坷道路,已在岁月长风的呼啸中铺排成一座雄关,成为他“西北望,射天狼”的一把长弓。
“遥望雁门”最终呈现的,并非渗在字里行间的雁门关的铁血历史,更不是充斥眼界的对遗址的凭吊和感怀,而是归于精神吐纳的仪式、血脉传承的使命,如同一个通灵的巫者在龟甲的纹路中辨认出一种神谕。
张卫平是出色的电影编剧,散文中视角的转移和情节的展开是和电影的镜头切换很像的。譬如这里:
“进入雁门关峡谷前,路过一个以石头命名的村庄。这是一块硕大的顽石,石上赫然留有一巨大的刀痕,据说这是杨六郎试刀时留下的痕迹……另一种版本的主人公是李自成……这是决定两个王朝命运的一刀,刀落下去,石破天惊,崇祯皇帝只能黯然退回历史深处了。”
一个巧妙的转折,由一位英雄带出一段史诗,他轻而易举地在同一个空间,加载了不同的时间。这样重叠迷离的叙事使读者不觉沉浸在故事的铺陈中。“遥望雁门”给我的感觉就是从顾炎武、杨延昭和李自成的足迹展开的,那是千百年来掠过雁门的蹄声和刀影,那是整个北中国从未停止的劫难和动荡。张卫平从他所崇拜的英雄的视角前转动镜头,调整焦距,他穿过雁门关睁开他打量关外的眼睛,那绵延峻岭,无疑是他文学生命中最初的关隘,由此注定他雄关漫道真如铁的一生。
当然,话说回来,这只是一位作家对生身故土的惯常眷恋,只不过在张卫平身上显得过于热烈和深刻。但有一点是惟有张卫平才能够达到的,就是他在叙事中托出的沉重的思考,他大量穿插的个人抒情,恰好达成了对雁门关和战争史的认知。他不仅对乡村的贫穷、苦难作出了描摹,还对历史的凋零、敝落进行着反思,甚至隐约对世界的空旷和虚无表达了自己的疑问。我牢牢记住了他在雁门关前的悲伤,那种刻骨铭心的诉说,那种由一重关隘到另一重关隘的行走、冲刺和突破,我认为可以看作是他不断自我回归的一条路线,也是他写作这部书的重要情怀。他内心对雄关古镇的崇拜,终究还是要通过写作来消除,并最终成为屹立于此的雁门关。
二
与“回望雁门”相比,“风中的泪滴”一辑则显得平实而亲切。我本来不大喜欢这个标题,总觉得张卫平这么一条粗豪大汉,取这样一个文艺女青年式的题目做故土文字的总结有点滑稽,但是在看到那篇同题散文之后,我放下了那点忍俊不禁和想打趣他的心思。那是他青年时代的一段真实经历,这段经历他曾经在聚会时给我们讲过,那是有关初恋、有关青春的故事:
“我一个人慢慢走在小街上,从这头走到那头。有时候停在街中间的小桥上,听桥下的水哗哗地流过。与这种郁郁的心情相比,更难驱遣的是那雾一样无孔不入的孤独和寂寞……”张卫平辗转陈述,尽管隔了多年,仍然能感觉到当时的萧瑟,这个开场本身就带有宿命的暗示,它在预言一个凄婉的故事。在他的孤独中,美丽的初恋女孩轻盈登场:“冰冷的冬季、温暖的火炉、如豆的蜡光……十几年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晚的月亮。天空是碧青碧青的,远处的旷野霜一样铺满了清冷的月光。我们走到镇子外的水库上,结冰的湖面镜子一样辉映着天上的月亮。”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当月光如水照亮人面,相恋的人却不知道命运的冰层在寒流下冻结。类似的故事还有几个:《飘逝的红头巾》《北方的红高粱》都写到这种带着无奈的伤痛、含着泪水的深情,这几篇初恋的故事,揭示了几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贫穷、苦难和它们带来的屈辱和伤害。张卫平如此,英姑如此,三舅如此,一场起点脆弱的恋爱,任你铭心刻骨,任你柔肠百转,也只是早已注定的死局。是啊,贫穷如此残酷,如此令人绝望。
但是故乡的贫瘠与荒凉始终阻拦不了张卫平内心对美的追求,他总是情不自禁地讴歌自然,他不忘记注视故乡北风中那凌厉的酷烈的大美;尽管他已经脱离了在乡间劳作之苦,但他仍然深刻地铭记住劳动的激情与光荣,关注苍天后土的去向及命运;他曾经饱尝求学就业之痛,也终于通过读书入仕的传统方式走出纠缠了十数年的乡村和讲台,他毫不避讳自己对它们的逃离,故乡是隐痛的泪水,却又是梦想的起点,精神的家园……文中那种对乡村场景及生命、真情的记录,那种浩浩汤汤的叙述和渗入骨髓的缅怀,使人深深地看到了一个时代之殇、一个少年不屈不挠的成长、一个人对故乡的背离和回归,……当逃避直面为担当,当屈辱扭转为幸福,当生命转化为灵魂,一切都将变得更加辽阔,这是我们这个群体共同的境遇之肇始,也是我们共同的梦想之涅。这些文字,堪称为所有乡土文人永恒的心灵史诗。
三
“太阳正在落下,红红的霞光血一样涂在城墙上
十二红再也没有回来”
张卫平仿佛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小型剧场,他混迹于所有的演员中,你循着他的声音,去辨认十二红、贾先生、纪烟袋……他用密集的意象和思维歌唱他的山冈。
“渴望崇高却往往平庸,企图不凡却难以走出日常。弗朗西斯哥不正是一个个的我们?
这是一个企图破而又永远也无法破的局
我们只能在这种宿命里寻求种种可能”
张卫平的有感而发不是单向的,而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就像这个众声喧哗的世界本身。当我悉心读到文集的收稍,我感受到他的人和文章呈现出的那一种正大的气象。在当下闲情逸致和剑走偏锋已成为常态的文学界,这种毫不媚俗的传统姿态多么难能可贵。这是一种稀有的文学品质,发出文以载道的光芒。尽管他有着如此磅礴而雄浑的笔墨,但他并不愤怒、亦不控诉,只有热爱和希望。这种人性与文章的练达,是中正里的豁达,大气里的品味。
远去的雁门,终于随着书卷的合上隐没在苍茫江山之中,然而在我心中,它一刻也未曾离去。雁门已然寥落,雁门又不会寥落,雁门是永恒的,也许它只是一个载体,记录着北风和杀戮,折射着血泪与伤痛,只要你有激情和梦想,有关山万里的情结,你就会站立在雁门之下,站立成寒冷而孤独的狼。
它们全都似真似幻,更为本质的是时间,时间的秘密无人可以洞察,雁门关沉默不语,那么硬的北风荡荡而去,更多的风迅速呼啸而来,以至于我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缝隙。现在,我离开这一波回肠荡气的阅读,回到所谓的现实,我又看到那匹忧郁的、孑然一身的苍狼,它不仅仅是张卫平,它属于雁门,属于大地,属于文学,属于遥远的北方。
(责任编辑高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