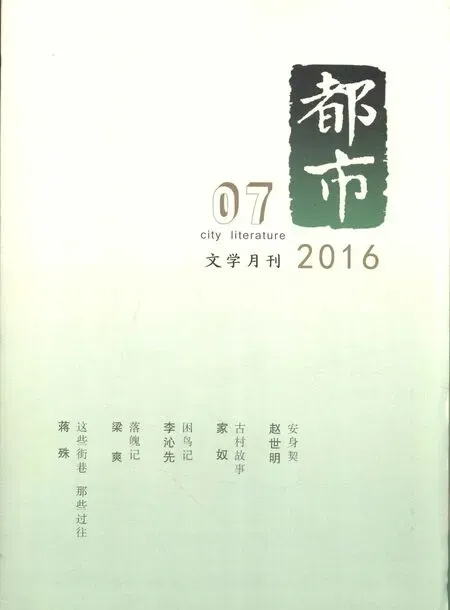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评蒋殊微小说《自己的墓葬》
邓迪思
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评蒋殊微小说《自己的墓葬》
邓迪思
张爱玲有一句“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蒋殊的文字,是见了生活,变得很低很低,然后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很难把蒋殊与她的文字联系起来,因为尘世中的蒋殊,是一个精致高雅、温默娴静的女人,有人说蒋殊是《红楼梦》里出来的人物,她带着浓浓的古典意味。她不像一个生长在黄土高原上的女子,更像是从上海、苏州来的大家闺秀,一举一动都有着雪柳玉樱般的妩媚姿态,美得沦肌浃髓。
她大气,但不傲气,同时接地气。
蒋殊是一个很善很真的女子,她在营造文字的厚味之时不失本真,情感流露自然,这不像某些故作高深,玩弄技巧的作家,总能看出些斧凿的痕迹。于是,读她的文字时总有些小小的触动,为了那不藏不遮的本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写文章也是为了保持本色,把生命的根建立在大地和故乡之上,无论飞得多高,也要俯瞰那片深深眷恋的黄土。
她没有吸收多少西方文学元素,她的营养是东方文化,更多的是民俗文化。
对她来说,守住自己的心灵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自己的墓葬》笔墨轻松,全文几乎都是短句,但短短的话里包含着长长的意味。这是一个与死亡相关的话题,但蒋殊没有用沉重的笔写,而是淡淡地、轻轻地道来。
她陪着母亲,看匠人给母亲造墓。
“表哥打来电话,说明天就完工了,你们是不是抽空回来看看?”“告诉母亲,她松了一口气说那就下周吧,一桩大事了却了也就罢了。”这个开头平和得吓人,为母亲造墓的大事就用两句对话了结。
“突然,一只喜鹊飞过来,落在工匠竖在那里做标记的石头上。叫了两声,又飞离。”“母亲说咱回去吧,今天是个好日子!”结尾又是这样喜庆,和坟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平平起,淡淡收,蒋殊在文字中不露声色,却有千斤力量。在母亲的喜悦中藏有一块巨石,女儿的无语中暗含一阵汹涌的眼泪。
活着的人是忌讳说死字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母亲。但母亲不避讳,女儿避讳得紧。
“更重要的,是你说不清自己什么时候死。”“母亲最后这句话让我惊了好长一阵。”母亲的坦然和女儿的惊讶形成对比,在面对生与死的态度上,母亲显然比女儿看得开。而母亲越是轻松,女儿越是沉重。
“这不,电话很快就打来了,墓葬,已完工。”“回乡。”如果借网络语言来评价这样的写作的话,则是,信息越短,内容越丰富。蒋殊在这里几乎是电报的风格,但是话里有沉沉的诗意,延展在读者的联想中。
“人的一生,可以用一辈子来形容,那么死后呢?是多久?”“什么时候是头?”生的尽头是死亡,死亡的尽头是什么呢?这好像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话题。就像问科学家,宇宙的尽头是灭亡,灭亡的尽头是什么呢?答案也许攥在上帝手里,人类无法回答。哲学问题,常常是无意义的,有关生死,无关生活。
尽管蒋殊在这篇散文里用了大量短句,但是没有丝毫急促的感觉,相反,觉得静静的、慢慢的。每一句,都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秋日的午后,斜阳淡淡的,风儿轻轻的。远处掩埋墓葬的尘土飞过来,咬在牙缝里倒觉得暖暖的。”这样的景色描写也独具匠心,特别是“暖暖的”三字,意味深长,墓上的土究竟有什么样的温度呢?
蒋殊的这篇散文带着自己的体温,带着对生命的沉重思考和对母亲的深深爱意,但是,隐藏于无形,所有的感情,都在文字外,这是最高明的地方。
蒋殊的文字没有悲痛感,虽然写的是为母亲造墓。她的文字情感色彩是明亮的,一会儿轻松,一会儿平静,有些地方还幽默诙谐。但是这样的文字恰恰充满了情感的张力,有一种强烈的压抑感。
她总是让我想起云南哈尼族作家莫独写的《为母亲搬家》,那是一篇为母亲迁坟的散文,也是平静得很。
蒋殊着意描写母亲的平静,但想必她能够感觉到母亲内心的波澜。母亲不知道和父亲谁先死,母亲担忧墓漏雨,母亲担心子女找不到墓的位置,母亲捡墓上的小石头扔向远处,这些细节描写,暗暗地显露了母亲的心。
母女都平静,都做出轻松的样子。母亲平静,是为了不让女儿忧伤;女儿平静,是为了母亲不想到死亡的痛苦。
平静的话语里,泪水漫溢。
无疑,这是一篇杰出的作品。
蒋殊最擅长的是写平凡的事物,能够从平凡的事件中发现独特的意味。她要在尘埃上开花。
她是一个美丽至极的女子,因为她在生活的尘埃上开出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