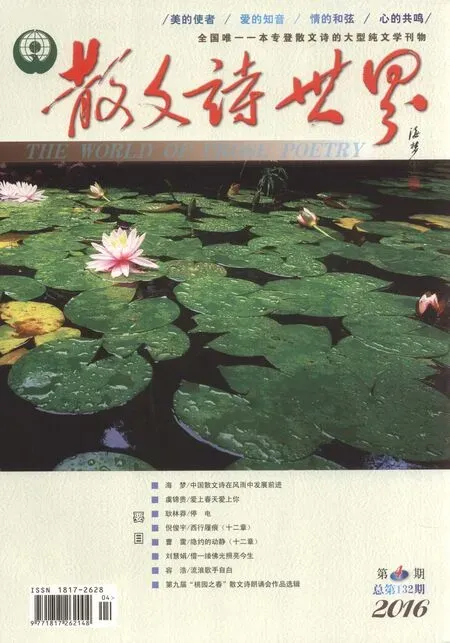春风唤醒雅江潮
湖南 洪孟春
春风唤醒雅江潮
湖南 洪孟春
1.桃花传讯
雪域桃花率先在林芝盛开。随后,像一股暖流,逆袭雅江。只三天,开遍加查;再三天,开到贡嘎。
我早已守在江边,迎候桃花,像迎候一位仰慕已久的女神。人生只若如初见。有兴奋,有忐忑,也有一些杂念。
迟到的桃花语笑嫣然。走过一千里风尘,攀爬四千米海拔,似乎都不在话下。
我问桃花:春风已度,你为何姗姗迟来?
桃花含笑:你别误我行程,我想在明日拂晓,开到日喀则。
我默然。春风劝我稍安勿躁:亲!桃花只是传讯,还有春天的万紫千红,正前赴后继,涌向高原。
2.鸟 群
雅江水暖的信息,是黄小鸭最先在微信上发布的。从晨曦初露到日上三竿,刷爆了朋友圈。有点赞,有评论,还有留言。
此刻,黄鸭们都已入群,下水,在江面上游弋,嬉闹,讲段子,调侃那位瘸腿的兄弟。也有少数默不做声,顾自潜水。
黑颈鹤起床有点晚,三三两两徘徊在江滩。也许是怀疑微信上的消息不一定可靠,面对昨天尚且刺骨的江水,他们止步不前。
直到潜水的黄鸭跃出江面,黑颈鹤才幡然醒悟。他们清晰的看见,鸭嘴里叼着一尾鲜活的嫩仔鱼,正铆着劲儿,挣扎。
黑颈鹤不再犹豫,纷纷展翅,一个箭步钻入江心。
黑小鹤走在最后。她把隐身在江堤内的斑头雁也拉进了群里。
3.红 柳
今日春分。每一棵柳树都展开尘封已久的乐谱,和着雅江流畅的节奏,润嗓子,唱红歌,忆苦思甜。
我听见歌声如泣如诉,细数着冬天的凛冽。
我听见歌声如痴如醉,畅想着春天的吉祥。
春风是位优秀的指挥家。春风拂过,江边的红柳像一群能歌善舞的卓玛,舞姿优雅,歌声嘹亮,整齐划一。
4.春耕典礼
三块圆形石,从大到小,依次叠起。太阳,月亮和星辰,像三尊佛,供奉在地头,也长住在藏民的心里。
再盛一碗糌巴,倒一杯酥油茶,在佛前摆好。盛妆的男女涌向田间,次第展开,载歌载舞。这一唱一跳,一眨眼,延续了上千年。
还得给牦牛献上洁白的哈达,还得让铁铧犁出丰盈的波浪,还得往地里撒下饱满的青稞……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黄道吉日,全村的人把全年的希望,全部托付给了春天。
5.吹柳哨的卓玛
吹柳哨的卓玛,情窦初开。她把满腹的心事,吹落在柳枝上,与露珠一起,凝结成一颗颗鹅黄的嫩芽,像一串省略号,吞吞吐吐,欲说还羞。
吹柳哨的卓玛,独坐在石头上。她看见江堤之外,风平浪静;江堤之内,草长莺飞。她看见两头热恋的牦牛,搂搂抱抱,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亲嘴。卓玛耳根一热,随即有两朵红霞,停泊在腮边。
我正好从江堤走过,感觉情窦初开的卓玛,有三分妩媚,两分娇矜,剩下一半,全是未解的风情。
6.拾肥的波啦
羊群饮水之后,牛群也陆续来到了江边。
此刻,夕阳斜照。江堤上的牛羊打着饱嗝,在熙熙攘攘的步伐中寻找回家的路。
拾肥的波啦撇开羊群,跟在牛群后面。只一袋烟的功夫,硕大的柳条筐已经超载,冒着新鲜的热气,像一锅刚出笼的荞麦馒头。也像波啦肥沃的梦想,在缓缓升腾。
田野上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刚刚破土的麦苗吐着舌头,舐舔着初春的气息。不远处,有一群尚未吃饱的灰雁,突然从田间惊起,仓皇掠过柳树林,消失在暮色里。
波啦抬头,看见顽皮的小孙子,手执一柄弹弓,扑面而来。他呵呵一乐,随手拾起一串环肥燕瘦的鸟鸣。
注释:波啦,藏语意为老头子,老大爷。
7.阳春白雪
这个阳春,忽然飞起了白雪。不知是冬天对春天的向往,还是春天对冬天的怀念。尽管是雪,最多让我打个寒噤,却不能阻挡我,迈入春天的行程。
牛羊早已出圈。候鸟早已远行。冬小麦早已破土。雅江里也响起了涛声。不用多久,又将是满山草绿,遍地虫鸣。
三月的雪,只能远远的伏在山头,望着我。望着我如何用一双手,播种春天的希望;用一支笔,撰写春天的诗歌;用一个镜头,采撷春天的风景;用一串充实的日子,丰满春天的梦想和这座原本厚实的高原。
8.两朵高原红
雅江的春潮已经涨到脸上,滋润着你。你援藏三年的光阴,绽放成两朵色素沉着的藏红花。
你曾经说过,脸上没两朵高原红,不好意思回故乡。
你一诺千金,终于兑现。你看,春风又一次吹绿了雅江两岸。却不知明月,几时才能照耀你,重返家园。
9.雅江古渡
无论潮起潮落,雅江都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河流。
我想:每一条河流,都有渡口。每一个渡口,都有往返的船只。每一艘船只,都承载着不同的使命。每一种使命,都向往勇于担当的肩头。
你的肩头。我的肩头。其实是两个隔着时空的渡口。三年以来,一直有一只载着相思的雁,或一叶扁舟,往来穿梭。要么是一根坚韧不拔的扁担,一头挑着雅江边的千多个日子,一头挑着麓山下的千万缕乡愁。
如今,扁担已经弯如弦月,曲似镰刀,更像一座风雨之后的虹桥。哪怕使尽最后一丝气力,我也要用这座虹桥,架通隔空相望的两个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