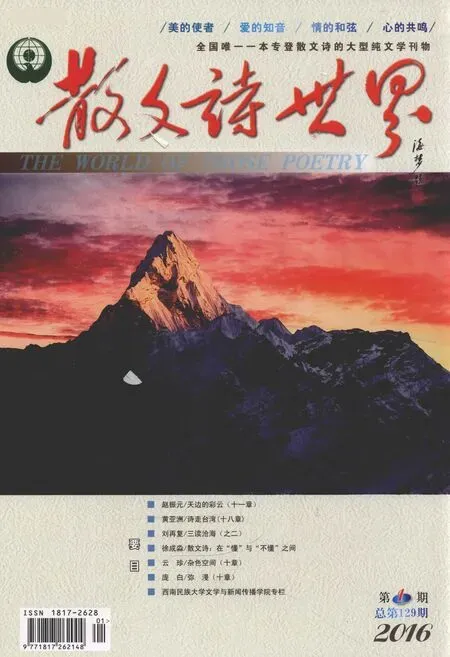诗走台湾(十八章)
黄亚洲
诗走台湾(十八章)
黄亚洲
世界诗人大会选择寺院开幕
开幕式很重要,必须,选择合适的温度、湿度、氛围与情怀,最好还要联系使命、职责与光荣。
就为如此,诗歌与宗教并肩而坐,互递茶水。
不少主讲者都是身披袈裟或心披袈裟的。后来颁奖,我也没有看见奖杯与证书,只见佛祖将莲花、金刚杵、海螺、金鱼,相赠于诗人。
每个与会者都感叹这样的开幕,出门上车,心跳节奏,均匀如木鱼。
确实,每首诗的诗眼,都应由观音净瓶里的甘露洗亮。
也不见得是坏事:将来全世界诗人写诗,头一句,均以念经开始。
本届世界诗人大会主席,是个僧人
他把观音请到诗歌面前,又把我们请到观音面前。
依我现在断定,观音本来就是一位浪漫派诗人。她举右手,将杨枝浸入左手的水缽里,只一挥,清凉的诗句就一行一行下来了。
这一刻,白色黄色棕色的诗人代表都默立在她的莲座下,诗的露珠与礼花的碎屑同时落满双肩。多么的好,一首长诗的多语言翻译,瞬间完成。
请观音拉开大会序幕,道一大和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杨枝的抖动与诗歌的责任,都是诗人们今夜辗转反侧的原因。
有的经卷读起来,大气磅礴,每一句都如诗行;有的诗歌念上去,鸡零狗碎,每一声都不是经文。
有一种互译,正在死去。为什么我们的心跳,总是不像观音的足音?
黎明,所有善良的露珠,都是三更或者五更的诗人的泪水。
再走苏花公路
战略选择是在岛子东侧,太平洋全面扑向台湾,你能从呼啸中想见排浪的巨大而猛烈。
太平洋在岛子上留下最远的那条弯弯曲曲的浪线,现在叫做苏花公路。
在已经干涸的这条浪线上,人们掸尽泡沫,装上一些交通牌牌与圆圆的镜子。也有可能,拐角处那些亮闪闪的小圆镜,是在说明,泡沫没有擦净。
我的汽车颠簸在这条公路上,至今还能感受座椅下的波峰与波谷。车轮始终保持耐心,仔细描摹着太平洋西岸的轮廓线。
若是描画错了,海风就会拿橡皮擦去,我的车随之转弯。
我必须,让我的方向盘与太平洋的情绪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我再有自己的个性也不至叛逆。我的祖先就是从太平洋的波浪底部上岸的。
就为此,我要试着以观察一条脐带的目光,亲切地看待这条公路。
脐带剪断,卡嚓一声,花莲到了!——我想以大哭的音质大笑出声,花莲你好啊——我新鲜无比的世界,可能就此,莲花盛开!
贴着太平洋夜行
隔壁的太平洋黑了下来,而我们还在爬行苏花公路。云层吃尽了星子。
打开车灯。尽快,把我们的汽车做成一座放平的灯塔。
必须为自己开辟道路。让自己的心脏,团结成北斗。这样悲怆的感觉,在台湾早已是共识。
你没有他法,你是男人。
太平洋屏住气息,四肢都不动弹。他侧眼看我们在漆黑的悬崖上蠕动,车灯锯开大山。
估计太平洋也有点赞赏我们的一意孤行,理解岛子的轮廓要台湾自己描画。灯塔作为移动的鼠标,这应该很有创意。
有时候,要学着感谢太平洋的绝情与提前而至的黑暗,还有身边暗藏刀剑的绝壁,它们迫使一座贴地的灯塔表达出生命的顽强,它们成全了北斗在内部而不是在外部体现了智慧与价值。
因此,只有夜行,才有黎明。
才能把太阳捺入灯塔,让太平洋顿时惭愧,满脸羞红。
花莲有点妒嫉太平洋
太阳同时照着太平洋与花莲。时间一长,花莲就有点妒嫉太平洋的广阔了。
花莲努力把自己撑大,要撑出更多舒展的草坡、花圃、亮晶晶的养殖区、不加修饰的树林与原野,还学着海浪的泡沫样子在蝴蝶谷制造蝴蝶。花莲不比太平洋小,花莲敢与大洋争宠。
当然,也有点妒嫉太平洋的朴素,所以花莲坚持不施粉黛,让青山绿水始终保持村姑状态,令山坡上的牛群与渔港里的鱼蟹全体裸露,叫笑容与花粉都有风的模样。
花莲还要捧上七彩湖与鲤鱼潭,指出这是已经安睡的海浪,是太平洋溅上岸来的诗眼。
很高兴 “阳光花莲”的荣誉通过了太阳的论证,很高兴太平洋与花莲像亲姐妹一样挽起了手,很高兴嫉妒是美丽的动力而花莲运用自如。
云层洞开,又一批阳光下来了,姐姐妹妹,谁先接招?
东华大学
东华大学以她二十一年的历史以及更加年轻的笑容,欢迎我们。
欢迎一部分诗句呈流线型,转弯九十度,流进阳光颜色的校园。欢迎诗歌一辆接一辆刹车。
在大教室响起诗歌朗诵的蜜蜂般的嗡嗡声时,草坪上的小花一朵接一朵开放了。
校园精神叫做自由、民主、创造、卓越。这当然是一朵花的四个花瓣。
校园在一般情况下都很安静。蝴蝶与昆虫都约定沉默。倒是不远处太平洋的水声,有可能以风的青少年的样式,隐约传来。
孩子们安静地成长,这很好。只是有时候,一只篮球会砰然击中球筐:自由、民主、创造、卓越,欢声四起。
花莲,蝴蝶谷
要学会蝴蝶的步子,一跳一跳的在这里参观。我甚至也要抖落翅膀上的一些粉,那是从大陆带来的尘霾,基本上都不是诗歌。
我要学着做这里的七十种蝴蝶里的一种,从三月舞蹈到十一月,在腊月与来年二月间躲入树阴休闲。这样的节奏有点接近苏浙小调,我愿意接受。
我实际上想做一只青带凤蝶,朴素间有些华贵,我写诗也是类似的追求。
说实话我真的喜欢许多梁山伯祝英台围绕于我,太阳布置灯光,风与溪水分别调试越剧的不同调门。作为剧中人我有巨大的悲悯和愉悦。
至于我化不化蝶现在不作定论。请允许我倚着青石与芭蕉思考一会,就像腊月至来年二月的蝴蝶,闭眼,垂下双翅,想想这个世界是不是全是蝴蝶谷,值不值得再度进入。
花莲街路
由于两侧的楼屋都不高,所以花莲窄窄的街路都不像是巷子。哪怕路两边停满了安静的小汽车与小货卡,花莲窄窄的街路仍然不像是巷子。
花莲的街路白天几乎没有行人,只有风与我两个,并肩而行。
在花莲街路上走动的,主要是太阳、汽车和摩托。从速度看,摩托第一,汽车第二,太阳第三。至于带咸味的海风,我无法计算在内,它有时快过第一,有时慢过第三。
远东百货睡得晚,要十一时才开门,对街的潮州手工馄饨面倒是勤快,一大早就用葱花撒香了半条街路。
路有中山路、林森路、和平路,这些称呼总是与海峡的历史与现状脱不了干系,虽说花莲位于台岛至东,离海峡最远。
理发店门外温馨地置放着靠背长椅,我的这些文字就是长椅上坐出来的。理发师推门而出,鞠躬问我是否要光顾,我赶紧婉言谢了,倒不是怕染成乌贼,而是怕剪成海带。
花莲男人
相信我,这一群上岸的鱼,就是花莲男人。
袒露黑黑的肩膀与胸肌,一手握酒,一手拿槟榔嚼,四顾说笑。海浪正在化成海风继续抚摸他们。他们是太平洋的儿子,穿着花短裤与海绵拖鞋。他们的肌肉是带棱角的,如同礁石。他们无论坐着和走着都好生性感。
他们的笑容与台北男人的也不一样,未经一丝雕刻,起落如同波浪。
台湾女孩子来玩花莲,除了看太鲁阁与蝴蝶谷,就是看花莲男人。
要看看这群上岸的猛烈的鱼!
这群有鳍的鱼!
这群带尾巴与牙齿的鱼!
他们骑上摩托,海水就让道了。他们走向女人,礁石就下潜了。
女孩子一定要及时抓住他们,只怕他们一个转身,眼前就只是茫茫的太平洋了,唯有鱼鳞和阳光的腥味,剩在手心。
在花莲火车站买名小吃
花莲的名小吃像我们乘客一样,乖乖排列在月台上。
她们的姓名是:麻吉、白梅、奶梅、花莲薯、沙琪玛、花莲芋、剝皮辣椒。她们不带行李箱。
她们穿的花衣服,都有行李箱的形状。
她们隔着“民营贩卖台”的玻璃看我,带着各自土地、山坡与海洋的滋味。
浪花的嘴唇。山坡的丰满。土地的体香。
切成小块的花莲被包装着,希望我能带走三天的回忆。
她们一齐转眼看我,真的希望我停下脚步,同时,在身体内部升起欲望,邀她们同行。
带走一位也行,一位也是花莲啊。
谁让我是一个多情的男人,我连着消受了好几位。我的诚挚的邀函,是我新換的台币。
在开往彰化的177次的一个小小座位上,我们愿意一齐挤坐。
被美丽挤压,那怎么能叫苦。在花莲缓缓移动的时候,我已与一大团甜蜜融为一体,此生不再分离。
彰化鹿港,天后宫
我要以这样的联想来理解妈祖的意义:如果在台湾中央山脉的主峰上,立起一面巨大的风帆。
一个岛屿的劈波斩浪,比任何一条大船所遇的风云,更为诡谲。
台岛原先就供妈祖,清将施琅打台湾,又从湄州带来一尊。就此,我猜想,妈祖一直在以自身分分合合的灵性,思索这座大岛的命运。
神龛里,几位妈祖均垂眼默坐,以余光看我。她们同意我的思路。
但我惭愧自己不是大副,甚至,也不是水手。我嘴里没有口令,心间没有航向。海草里一只垂直跳起的小虾,都可能比我有力。
波涛上窜,历史落泪。
中央山脉上的那根大桅,这一刻,满风了吗?
我很想呐喊,但又不知为谁吼叫。
妈祖,似乎,并没有这么感伤。她只垂眼,甚至顾不上继续看我。真相是,她拥有太多的波涛,太多的珊瑚与暗礁,太多的惨叫与欢呼,航线自在其中,而且非常准确。
在王功村吃蚵
日头近午,我们尖利的牙齿,又将对准哪一类弱小?
感慨的是渔村主人的辛苦,竟将一座面目狰狞的礁石,切成如此均匀的碎粒,端上餐桌。
每桌再配三把尖刀,一定让我们这些摇头晃脑写诗的,做餐桌上的漁民,网罗一切,稳准狠。
对准碎粒状的礁石刺下去,果然都能发现一小撮细皮白肉,这些在刺刀下死死包裹自身的弱小。
哪部战争史里掉出来的这些细微末节?哪一场载入青史的战争没有这些细嫩的眼泪?
现在,这些眼泪的浓度,相当于海水。
流过台湾海峡的海水,都叫做泪水。
拿刀的手应该颤抖,太平洋把少女保护得那么精心,选择最丑陋的盔甲做成校服,却仍然要面对第一轮的刀尖与第二轮的牙齿。
刀尖与牙齿的后面,站着人类的肉欲。
不怪豪爽好客的主人,只怪伤风溅泪的诗家。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易于受伤的心,变成了蚵壳里面的形状?
这或许是需要的,面对慈悲的大海,让我们至少一次,痛感诗句的伪善。
而牙齿与刀尖继续轮番肆虐,整个中午,战争不放过任何弱小。
餐桌血肉横飞,海峡刀光闪闪。这或许是必须的。
王功村的蚵壳艺术
请再一次评估渔人的力量。
何等的力量,不仅见于他们张大的十只脚趾死死钉住甲板,也见之于他们敢把十个手指张开,专门将大海的一份罕见的丑陋,打捞成艺术。
把蚵的那种千篇一律惨不忍睹的烂衣裳,织成皇后的新装与公主的婚纱。
蚵,终于有福了,忽然就在橱窗与展厅里,站成绅士、思想者、佝偻老者、妙龄少女、舞动人生的男女,甚至,周身涂满太阳的色泽,成为报晓的金鸡。
有福了,破衣烂衫的蚵,你们通过捕捞,成为名模。
这世界没有贱民。渔人通过蚵的命运,认识了自己,与自己的家人。
彰化,芳苑灯塔
我更愿意将它视作一柱旗杆,因为我是在黄昏接近它的,这时候火还点在太阳身上。
一柱不倒的旗杆。它巨大的旗帜,是噼噼啪啪的长风。
三十七点四公尺,台湾最高与最年轻的灯塔,这让我立刻想到台湾的人,台湾的那些头颅与脊椎骨最为年轻的人!
他们站在宝岛的最东端,把头颅抬在蓝天白云之中。他们知道太阳就要坠落了,他们要把在心房里点燃的火,举到思想的高度。他们知道自己有能力取代太阳。
換一个说法,实际上,它已经把太阳按倒在地平线上,切成了三百六十五块。
它知道自己永不熄灭,可以永远帮助到每一个迷航的人,所以它这一刻敢静静地站在黄昏里。它愿意等待。它不怕时间。
只有时间怕它。因为它会瞬间爆发,占领空间。那时候大海会突然成为天宇,星星刹那间成为鱼群。
让我现在再一次注视它,除下帽子,抬高脸庞,就如同向一面旗帜致敬。
我看见太阳正在落下,火熖正在上升。我看见天与海的交接班,无可避免,已经开始。
我在台湾获得一块奖牌
这里是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灯火辉煌的礼堂。麦克风通知我上台,有一块奖牌从天而降。
飞来太平洋一只闪烁的贝壳,或是一粒有带幽光的珍珠。
台阶没有几级,却是达至九霄的天梯,云雾是两侧绵延的扶手。
诗歌就站在舞台中央,向我伸出手来,我注意到她裸露的后背长着天使的双翅。
“美国世界文化艺术学院院长奖”,我听见了翅膀拍动的声音,多么动听。
这一响动,甚至,也同时出自我的后背,有这可能。我的诗句一直在土地、山冈与水洼爬行,这一刻,飞离了地面。
感谢台湾,一头通过海峡的波纹,牵起我腐乳和油菜花的故乡;一头通过太平洋的浪花,连着美国加州那所郁郁葱葱的学府。
走下颁奖舞台,请第一排的朋友及时帮我卸下翅膀。我的诗句急于恢复百脚的爬行,许多长野草的坡地与有蚊虫的水洼,在候我光临。
这是我再次飞行的本钱。
桃园市,庄敬公园
在同安路、庄敬路、新埔十街之间,庄敬公园小小地站着,拉着一小片阳光。
她拥有很小的一块圆形绿地与更大一些的水泥地。水泥地上站着一小片树林。树上花瓣落地的时候,找寻土壤有点困难。
汽车与摩托的啸叫从四个方向同时侵入,她每次都奋起反抗,用小鸟回击。盛夏的时候,火力不够,再辅以坚强的蝉声。
二十张靠背长椅是她最有用的装备。连那两个蹒跚的老人与一群蹦跳的儿童,都被她编入了守城的士兵。
我先是在尊爵饭店结识桃园的海蛤与生鱼,然后就穿过汽车的缝隙,进入鸟鸣。我要向她请教庄敬自强的哲学。
身处灯红酒绿的中心,守身如玉,并且努力照顾老人与孩子,还要坚持向黄莺与云雀学习歌唱,男人你这辈子还在寻找什么啊!
台 北
台北活在太阳的侧后方,活在波浪的臂弯间。台北是南京、重庆的影子。台北活在阳光底部的阴影里。
我们承认台北是台湾的中心,但不认可是首都,因为我们长期不认可一个岛屿是一个国家。然而台湾百姓奉其为都城,视总统府为笼子,敲锣打鼓选一个领导人然后将之关入,看他表演,透明的演出服比咏装还悲惨。
显然,台北是一座制度,总统府是其中的关键条款。都城的本质便显现于此。宪法执行宵禁,盘查路过的月亮与星星。
军舰和潜艇巡弋于护城河,这里的百姓知道什么东西需要精心保护,尽管力不从心。螺旋桨与金鱼打在一起。
我降落于桃园机场,踏着阳光底部的影子,走向南京与重庆。我带来的是杭州的风。我们这一批城市,纬度大体相同,只是我们的这个影子,偏南一些。
确乎有点不爽。在历史的坐标里,这影子,未免拖得过长。
但这是必然的。
只有太阳沉默,星星闭眼,我们才会在闪闪烁烁的灯光里互为影子,互道辛苦,并且,还能,高声回答同一声宵禁的盘查,以标准的国语。
国父事迹陈列馆照片:看见孙中山作画
我要在今天赞叹孙中山绘画的天赋,虽说他画的这个太阳可能动用了圆规,或是一只没有缺口的茶杯盖;画太阳那十二道光芒,可能用了直尺,或是一本书的硬皮书脊。
但他,画得精准。他很明白,太阳的运行就在于精准。
而且他以同样的精心描绘了光芒身后的黑暗。他画黑暗的时候令铅笔摇动猛烈,叫乌云越积越浓,以让携带十二道光芒的太阳最终从纸面上骤然站起,几乎直接就跳上了党旗。
再后,直接,跃上了天际。
显然,他与这轮太阳有一项共同的理想,那就是不能再让乌云与一个国家合成一体。
一团乌云的四边,不能是一个国家的国境线。
十二道光线,也可以理解为一面齿轮的利牙。国家必须剥离黑暗。
这样剧烈的运动,工艺是精准必是前提。因此,他为分娩中的太阳明确写下这样的尺寸:“日体十分,光芒长四分半,圆阔半分。”
孙中山确实是看重工艺的精准的。他的每一道光芒的锐角,都刺中了黑暗的神经,以使黑暗与中国同时抽搐起来,黎明在其间挣扎。
我不能不在今天赞颂孙中山绘画的果决与明快。我能在黑白对比中感觉一位政治艺术家的愤怒与喜悦,尽管他打造的锐角,至今还在苦苦磨牙;他愤怒描绘的黑暗,至今,还有可观的残余弥漫于山河,以鸦群与灰霾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