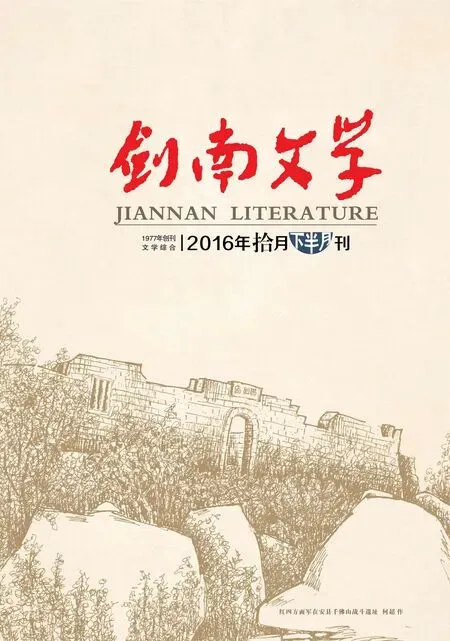张爱玲与曹雪芹的女性书写比较分析
□陈寿琴
张爱玲与曹雪芹的女性书写比较分析
□陈寿琴
引言:本文就张爱玲和曹雪芹小说中的年轻女性形象进行比较分析。从艺术旨趣、文化景观、审美情感等角度来分析两位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生悲剧,以及女性书写的特点,并进而探求他们审美意趣的差异在于张爱玲的有人性深度的“俗”味与曹雪芹的有人生高度的“雅”美。
张爱玲和曹雪芹的小说都聚焦那些辗转于家庭或家国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生存图景之中的女性。两位作家以生花妙笔描画出不同时代的“仕女图”。在他们描绘的图卷中透出一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的悲剧意蕴,令无数读者黯然神伤、唏嘘不已。毋庸讳言,在悲剧女性的书写上,张爱玲的小说深受《红楼梦》的影响。但是两位各禀才情的作家在女性书写上又呈现出不同的艺术旨趣、文化景观和审美情感。本文拟就对两位作家笔下的年轻女性形象进行比较分析。
张爱玲和曹雪芹的小说都善于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对女性人物进行真切地描写。不过,两位作家在艺术旨趣上似乎又体现出不同的追求:一位直面残酷的现实,以冷峻的笔墨勾勒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夹缝中的“新闺阁”里的悲剧女性形象;一位营构理想的境界,以超凡脱俗的笔触勾画出众多才貌兼备的古典悲情女性形象。
一、世俗的庸常
张爱玲笔下的悲剧女性形象最具特色的是新旧时代交替中的没落淑女。根据其现实处境来看,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比较旧式的川嫦、长安们。她们生在败落的封建大家庭,现代的自由、平等思想对她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到底还是撼不动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伦常文化,所以就其生活底子来说,依然还是旧的暗淡的。《花凋》中的郑家已经彻底走向败落,但是郑家的女儿不能出去做工挣钱,那是丢不起面子的。所幸郑家的女儿个个貌美,于是她们就有了成为女“结婚员”的资本。温柔的郑川嫦在“媒妁之言”的婚约里,对未婚夫产生了一种爱意。然而,正沐浴在“爱情”阳光中或婚姻的展望中时,她却被肺病纠缠。她的肺病不像林黛玉的肺病那样具有一种特别的诗意,反而成为她悲剧命运的现实缘由,因为它让势利的亲人厌弃,使讲究传宗接代实用目的的恋人“移情别恋”。她的生存处境岌岌可危,无助的她爱又不得,生又不能,只能孤独地死去。她的死没有悲壮,只有无尽的悲哀,因为她始终都没有抗争过。因为她所受的家庭教育使她不可能“抗争”。川嫦的悲剧人生在于亲情的冷漠,爱情的幻灭,肉体的死亡。她的死何尝又不是一种解脱呢?在此,张爱玲的笔墨正视人生的虚无和人性的自私。《金锁记》中温顺的长安寂寥地活在家长的阴影下。她虽然进过洋学堂,但是始终都没有想过要挣脱旧式伦常的束缚,任由青春变得灰暗无光。本来她与留过洋的童世舫相互喜欢,因为“变态”母亲的干涉和莫须有的猜疑而葬送了爱的权利和享受平凡婚姻幸福的可能,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只能陪着衰老的母亲枯萎下去。她不用担心生存问题,可是谋爱无望,婚姻无着。她觉得她的牺牲是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显然,母爱异化和封建家长制导致了长安的悲剧人生。
另一类是比较新式的白流苏、葛薇龙们。《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曾经如娜拉般勇敢地逃离了夫家,回到娘家。当娘家人把她的钱用光了,就打着“三纲五常”的旗帜劝她又回夫家去为刚死的前夫守寡。她为了摆脱在娘家尴尬的处境,为了生存,放下自尊和体面不得不选择做范柳原的情妇。所幸,在香港沦陷的特殊战争情景下,她用尊严和身体换来了生存的保证,得到了她想要的婚姻和名分。叛逃此一夫家的流苏,又回到了彼一夫家。流苏对柳原是有爱情的,但是谋生的迫切性压抑了谋爱的诗意性。因为流苏谋生与谋爱是一致的,所以,就少了因爱与生存的错位所造成的撕裂般的痛苦。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在谋生与谋爱的严重错位中痛楚周旋。薇龙是封建家庭中的女儿,因为家道不济,有主见的她主动接受了姑妈梁太太的“物质帮助”。她父母回上海了,她留在香港继续求学,从而脱离了封建家庭的约束。而后她被姑妈培养成香港华人交际圈中的新秀,从此她就逐渐陷入了物欲的泥沼里。后来她爱上了漂亮的混血儿乔琪乔,又陷入了爱情和婚姻的黑洞里。为了满足姑妈的淫欲和乔琪乔的金钱欲,她自愿混迹香港社交圈,成为为姑妈弄人和为丈夫弄钱的工具。葛薇龙明白她自己想要什么,而且知道自己的艰难处境,就是难以超脱现实物欲与情欲。如果她是艳丽的,那也是一种俗艳,交际花式的功利性艳丽。她的职业就是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中上层社会的男人,在经济上依附于众多男人,而不是唯一男性——丈夫。这里,传统家庭伦理和道德被现代欲望消解了。在她的婚姻中,她爱丈夫而丈夫不爱她,丈夫爱的是钱,因为钱可以买来各种感官享乐。现代都市社会,婚姻成为爱与物质的交换,她不是为了谋生而结婚,是为了谋爱;可是谋爱不得,婚姻给人一种不可靠的虚无感觉。婚姻成了饮食男女实现欲求的一种载体,而少了现世安稳的那份笃定。
由上观之,张爱玲笔下的这些悲剧女性既要承受封建大家庭衰败的生存压力,又在依稀存在的爱情纠葛与人伦桎梏中承受日常生活的压抑。新旧转换的社会里,这些败落旧家庭中的年轻女性几乎没有求生或追求爱情的本领和勇气,所以她们大多首先以求取婚姻来谋求生存或爱情。这就可能导致爱情与婚姻的错位或爱情从婚姻中的滑落,于是婚姻变成了一种理性的实用性的选择,缺少了自由感情的审美性。张爱玲借这些女性人物悲剧性的荒谬处境反观了人情的冷漠和人性的变异。
二、优雅的超逸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画了各具风采的女性群像,简直就是一副中国古典仕女的“清明上河图”。曹雪芹笔下的女性人物大都才貌双全。以林黛玉、薛宝钗、妙玉、史湘云、“贾府四春”等为代表的女性人物无不是才华横溢,美艳如花,都是兼具外美与内美的古典“美女”典型代表。不过,这些悲情女子宿命般地演绎着其优美伤感的故事,真应了那句“红颜薄命”的谶言。
颇有诗人气质的林黛玉多愁善感,伤春悲秋,又孤高标世,风流袅娜,目无下尘,自有一种阆苑仙葩的脱俗气韵。她对纯洁、真挚爱情的全身心投入最令人动容。姑且不论神瑛与绛珠仙草的凄美神话对这位“世外仙姝”宿命般的影响,单就她为爱情泪干、呕血而逝来论,黛玉的塑造最具诗意;因为她为情而生,为情而死,她是人间至情至爱的化身。她始终保持了灵魂的高贵和情感的自由,所以能超逸出世俗的牵绊。正如有论者所说,林黛玉“以感伤为人生主调。她摒弃了世俗生活追求,把生命纯然升华为审美化的情感追求。[1]”作为封建时代的女性,黛玉的爱好不在女红,而在读书作诗。她读写是无功利性的,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细读她的那些缠绵悱恻的诗,可以见出一种超然与高洁的精神品质。尽管她活在世俗之中,却又超然于外。这位大观园才女的才情心性积淀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寄寓着封建时代理想化文人雅士的高标风范和人生形态,即保持生活的“入世”情怀,追求精神“出世”的自由。
博学的薛宝钗艳压群芳,艳丽妩媚,娴静华贵,别有一种端庄典雅的韵致。虽然“金玉良缘”在世俗中取代了“木石前盟”,然而这朵娇艳“牡丹”在得到了宝二奶奶的头衔时,却在婚姻中失去了爱情。薛宝钗的悲剧人生和葛薇龙的悲剧人生很相似,为爱而谋取婚姻,可是丈夫的爱却在婚姻中缺席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葛薇龙就是现代版的薛宝钗。妙玉气质美如兰,才情出众,富有灵气,多情曼妙,另有一种高洁雅致的风度;她以“出家人”的身份小心翼翼地爱着贾宝玉,却无法得到宝玉的完整的真心,而且在后来还遭难陷泥淖。实际上,黛玉、宝钗和妙玉都可归为谋爱而不得的悲情女性。相对而言,史湘云任性自然,活泼洒脱,真实率真,具有一种自然潇洒的美质;但是她的命运依然不在她自己的掌握之中。贾探春不仅颇有才华,“文采斐然”,善长下棋和书法;而且志向高远,热情大方,胆识过人,霸气凌然,令人“见之忘俗”,理家的能力紧赶琏二奶奶王熙凤,最终却远嫁他乡。贾惜春画画得好,虽逃过家难,却只能青灯古佛,孤独终老。其他女性人物几乎没有什么好的结局,贾元春荣宠等身,最后还不是富年“薨逝”;隐忍的贾迎春、秦可卿等都是如花年纪就凋零了。她们个个都饱读诗书,诗词歌赋酬答,琴棋书画俱佳。好一道绝美的风景线,这风景中有的是风姿卓绝的闺秀,舞文弄墨的佳人。可是,这些佳人逃不出“华美闺阁”的魔咒,她们的青春与爱情、才情与诗意、志趣与追求被埋没于与世人隔绝的“理想世界”之大观园,不为外人道,也不为外人知。这也是封建伦常文化或男权文化对女性最深重也“最自然”的钳制与限定。
这些真情、率性、充满活力的、富有才气的美丽闺秀们温文尔雅,矜持含蓄,生活情趣高雅,具有封建淑女特有的美德和优雅。她们不为考取功名利禄而读写,只为生命的快乐和精神追求而弹琴下棋,吟诗作画。她们在大观园的生活,充满诗意,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栖居”。然而在现实中,家族的兴衰直接影响到这些贵族女性的命运。贾家的衰败使这些理想化的女性最后都走向悲剧人生的境地。曹雪芹又用超逸的笔为这些跌落现实的悲剧女性构筑了想象中的太虚幻境,将爱情、理想、生命交付给浮世外的虚幻之境。而曹雪芹的高超之笔还在借跛足道人的《好了歌》表现“万般皆空”的人生感慨,他想向世俗之人揭示“人生无常”的这一超越性智慧。于此,她的女性书写达到了一种超拔的人生境界。
比较而言,张爱玲的小说具有世俗的人间烟火味,所以她笔下的女性人物都活在居家过日子的日常生活中,活在庸常中。就如杨义先生所说,张爱玲在“中西境界相错综之处,变幻出一幅幅充满苍凉与不安的洋场仕女图。”而曹雪芹饱蘸诗意情趣,为这些生在温柔富贵乡的才情卓著的仕宦闺秀们画像,画出了一幅幅优雅的深闺仕女图;最后又将美丽毁掉,让其在无望的爱情中死去或在措不及防的家族败落之际承受灭顶之灾。作者为他钟爱的青春女性绘出了凄美的图卷,目的何在?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精神告诉人们如何摆脱欲望、在俗世间得以解脱。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女性书写的审美趣味上,张爱玲的有人性深度的“俗”味与曹雪芹的有人生高度的“雅”美构成了不同的女性书写图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似乎始终都有一种难以超脱的世俗之气,她们耽误于世俗化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情趣,在人情的庸常中打转,缺乏曹雪芹笔下那些才情女子的高雅志趣和精神追求。也许,她这样写似乎更真实,更贴切生活本身。她写新旧文化更替时期的洋场淑女,将其置于“谋爱与无爱的困局中,用爱情与婚姻永远的错位来揭示女性生存的无奈与存在的荒诞。”也写出饮食男女的生之欲求与现世安稳的追求。张爱玲世俗女性书写的深刻在于,其在人生的无聊与庸常中发现了人生的虚无,揭示了人性的自私与虚伪。而且铺写出一种苍凉、颓废之美。再者,她营构的颓败王国中的女性都有一种永恒性:“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年代,任何社会,到处是她的家”。所以,在她《自己的文章》中说,“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能给人回味和启示,也能展现美、人性。
而在曹雪芹的诗意“女儿国”则充溢着古代淑女的仙气、才气,充满着美好的青春,纯洁的爱情,率真的性情。文采精华,雅趣横生,保持灵魂的雅洁和超逸。他还用神话与现实的二元对照来塑造人物,并以“情”为中心,在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中来刻画理想化的古典美女。可是美终究被毁灭:现实故事以悲剧收束,从而揭示家族衰败的现实利益、伦理规范等对女性的重重捆绑,进而展示人生的变幻莫测。临了,他又以感伤的笔给众女儿以新的归宿,即太虚幻境,为情与美的幻灭谱写一曲哀婉动人的挽歌。用周汝昌先生的话来说,曹雪芹“以诗心察物,以诗笔画人,以诗境传神,以诗情写照”。由此可见,曹雪芹的女性书写,境界高妙迷人,充盈着中国独特的空灵飘渺的韵致与美感。
张爱玲与曹雪芹都擅长在特定的文化时空中表现悲情女性,并揭示出在婚恋、家庭(家族)和人生追求中的女性文化心理。其文化景观迥异:一个揭示日渐式微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相互缠绕,一个展现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雅致与局限。其审美情感不同:一个“以深切的理解对女性的异化给予慈悲的同情”,一个“为女性青春之美的毁灭而恸伤”。其艺术思维取向上也存在差异:一个侧重揭示传统与现代文化冲突下谋爱与谋生的错位和人性的脆弱、黯淡,一个侧重展示封建伦理文化重压下情的幻灭和美的毁灭,探询人生虚幻的“色空”观念和形而上的精神超越。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古典小说与现当代小说比较研究”(KY2015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