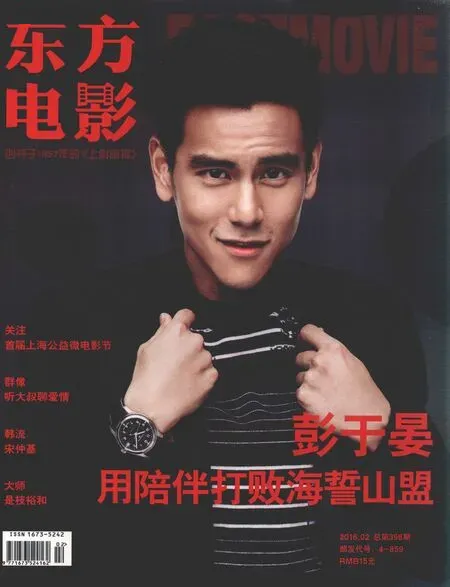是枝裕和宛如走路的速度
文/甘琳
大师
是枝裕和宛如走路的速度
文/甘琳

走路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宛如走路又不只是走路,更像是在表达一种人生态度,一边走路一边思索亦是人生。是枝裕和以“宛如走路的速度”命名自己的第一本随笔集,这个题目不仅代表着这本随笔集的调性,也是是枝裕和对其创作和日常的一个交代。从第一部长篇剧情电影《幻之光》到最近大热的《海街日记》,是枝裕和始终在以一种温吞的态度讲述着他所理解的影像世界:创作者并非是世界的掌控者,而是先死心塌地接受世界存在着的种种不由自主的前提,再把这种不由自主当作“有趣”的创作因素。
一路走来
1962 年,是枝裕和出生在日本东京的清濑市。1987 年他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加入 TV Man Union(电视人联合会)独立电视制作公司,拍摄了近十年的纪录片,之后才转向大银幕。他并非科班出身,出道前既没有像同辈导演黑泽青、周防正行、青山真治等人师从著名学者兼电影评论家莲实重彦的经历,也没有行定勋、冢本晋也等人丰富的 8mm 或 16mm实验短片的创作经验。甚至,是枝裕和在校期间,连任何一个电影俱乐部都没参加过,他谈及自己拍摄电影初衷时表示:“本来进大学是想写小说的,进去后发现没什么意思。当时早稻田大学附近有很多电影院,我在那里度过了很多时光,后来就决定去拍电影。”早年电视纪录片的从业经历不仅没有消磨是枝裕和的创造力,反而令他变得更加细腻。是枝裕和这样评价自己的电视生涯:“不像电影那么迁就导演的作者性格正是电视具有的独创性。如果电影是有乐谱的古典乐,那电视就是经常即兴演出的爵士乐,与观众共享逐渐消逝的时间。”
导演增村保造评价日本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导演善于对伤感的爱或者母性的爱做出诗意性的描写,并将这些东西与山川风光等大自然的抒情要素融为一体,以此磨砺出他们的细腻感性”。是枝裕和的作品很好地演绎了此番描述,并与时俱进地对日本文化中亲情和家庭的血脉关系进行雕琢。他的作品继承和回归了小津安二郎、成濑巳喜男等表现平民家庭生活的“庶民剧”大师的影像风格,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和东方诗意风格。

是枝裕和从1995年的剧情长片处女作《幻之光》开始就奠定了其现实主义叙事的生活流风格。《幻之光》讲述了一个因前夫自杀而终日处于困顿状态中的女主人公顿悟的故事。2004年的《无人知晓》虽然改编于真实的“1988 年东京巢鸭儿童遗弃事件”, 他却尽量将这个骇人听闻的社会事件淡化,并透过极端节制的影像镜头设定,迫使影片尽可能工整简洁。影片的色调温暖鲜明,光线明亮,不恣意渲染故事本身的悲剧性。是枝裕和早期的作品可以被归为“社会派”,直接导入奥姆真理教事件的《距离》、以弃养儿童事件为由头的《无人知晓》等都非常具有社会记录性。2008年的《步履不停》是他创作起承转合的一个高点。影片描写了横山家在长子死忌这天,家人的日常生活状态。电影表面看似没有突出事件,也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展现得无非是一家人吃饭闲谈的日常生活,但我们却能在厨房刀切萝卜的声音以及蒸笼水汽的氤氲中看出这家人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与生活历史,日常生活细节的表层之下实则蕴含了强烈的戏剧冲突与情感张力。《步履不停》之后的作品不再具有其早期作品明显的记录批判力道,但我们可以发现,是枝裕和不少电影里的男主角都不约而同以“良多”为名,“良多”这个角色母体,是是枝裕和自身经验的投射,也是其“人比剧情更重要”的创作导向表达。

记忆与影像
我们生命的每一小时一经逝去,便立即隐匿于某些物质对象当中,这一对象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就会永远寄存其中。我们是通过那个对象来认识生命的那个时刻的,我们把它从中召唤出来,它才能从那里得到解放。在是枝裕和的作品里,时间的可逆性往往可以通过回忆的对象化和物质化得以实现。
《幻之光》里,由美子无法忘记死去的前夫。虽然新的丈夫把她带到一个靠海的看似开阔的渔港生活,但对于由美子来说,时间已在这个远离都市的地方停滞不前,她的主观空间依旧是逼仄的,她依旧内疚、困顿于前夫的自杀,逆光拍摄以及室内空间的压迫强化了由美子心理情感的自我封闭。当她回到与前夫的旧家,站在走廊上,突然转过头来看向镜头,久久不能将视线移动开来的那刻,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回望过往记忆的欲望。隐匿的记忆被由美子召唤出来,即使我们能够暂时摆脱现在和过去,从将来的视点看自己,但因为我们始终在世界中存在,始终拖着来自过去的沉重肉身,所以,我们不断地被拖回到现实。当然,这种对过去记忆的执念终究要得到释放,是枝裕和在电影的结尾处总会安排一个情绪迸发的情节。大远景的运动镜头展现了处于情感崩溃状态的由美子,她跟随海葬队伍徘徊于海边,脚下的泥沙不断地被涌上前的潮水卷走。民雄的劝慰配合着背景音乐裹挟、浸润着由美子的情绪,回忆影像本身依附于被唤起时的情境,乃至于糅合了当下的新知,它本来就是以扭曲的、变质的影像回到我们眼前。就算我们刻意追回逝去的时间,它也是透过意向性反复重构一个已然且永远逝去的影像,每一次的追忆都会增添这个回忆影像的虚假性,由美子的创伤起于记忆也终于记忆。
所以在接下来的纪录片《当记忆失去了》以及剧情片《下一站,天国》里,是枝裕和更是直接把记忆设计成了可以“制作的影像”。在《当记忆失去了》里,因手术失败而只记得手术之前记忆的关根每天起来都要观看家人为他准备的记忆,他通过与家人一起观看照片和录像来认知自己手术之后的记忆和日常生活。《下一站,天国》则虚构了一个天国中转站,服务人员帮助死后亡灵选择生前最为难忘的记忆并重现在电影胶片中,使之成为永生记忆,通过此种永恒,逝者才能进入天堂。但无论哪一种自我检视,都不及记忆问题对自身所产生的效果,甚至连死亡都比不上。至少死亡时的个体很清楚自身情况,甚至可以在濒死前要求一定程度的尊严,就像纪录片《没有他的八月天》里平田丰向是枝裕和提出停止拍摄的要求一样。但失去记忆却是被动的,在记忆与现实产生落差的时候,就有一种仿佛缺席自己人生的错觉。《当记忆失去了》里的关根已经失去了留存记忆的能力,《下一站,天国》里的亡灵对于自己的记忆更多是模糊和忘却的,他们无法精确选择自己最为难忘的回忆才一直停留在天国的中转站。相对于《幻之光》里由美子对记忆的执拗,对记忆的忘却同样是是枝裕和关注的焦点。人们通过制作记忆的影像,达成了一种关于真实的再认识,记忆原来是可以逃遁的,它与一切过往融合到了无限的平面中,进入一种集体意识的阶段。我们记忆最美好的部分其实留存在我们身外,存在于带雨点的微风吹拂中,存在于卧房发霉的味道中,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不屑于加以记忆,可我们自己却追寻得到的地方。

步履不停的日常
是枝裕和在自己随笔集里回忆父亲时,并没有用许多感人深刻的片段,他只讲述了一个关于电视与胡须的记忆。是枝裕和第一次观看电视节目不过两岁大,那时父亲长长的胡渣就贴在他专心观看体育节目的脸上,这种触觉让仅仅两岁的是枝裕和记忆深刻。在父亲去世,是枝裕和为其守灵的那个晚上,他看着棺木里父亲微张的嘴巴像是在打鼾,心想这样的容貌出现在告别仪式上实在不好,便将毛巾拧成一块,塞在他的颚下。当他的手碰到父亲长长的胡渣时,立即唤醒了三十年前关于父亲的记忆,是枝裕和开始哭起来,直到清晨都还流泪不止。这即是是枝裕和对于日常的体验,并不热烈却十分具象,是幼时旧屋前大片的波斯菊,是街边杂货店冰箱打开时冒出的冷气,是是枝裕和卧睡在茅崎馆聆听涛声的静谧。
从小到大养成的对于日常生活的精微观察,使是枝裕和的电影作品能在记录性中透露着经验性,视听的结合永远能让观众产生“啊,怎么这么生活”的惊讶。他善于运用固定的长镜头展现室内空间,为了弥补固定画面在表现空间时的限制性,是枝裕和常以画外音的方式扩展影像空间的表现力,打破画框的局促感,把画内和画外空间连接成一个整体。影片《奇迹》的开头,观众首先听到的是哥哥航说话的画外音,接着才看到他打开阳台门取下抹布擦拭自己的房间。观众同时还可以听到电视播报当地天气预报和新闻的画外音,紧接着的镜头是母亲在洗碗、外婆在练习手舞、壁橱上的电视播放着新闻。这一段戏多次运用声画对位的方式,描绘出一幅现实日常生活的状态。
剧情上的日常展现同样如此,《步履不停》里一家人一起吃鳗鱼,爷爷恭平从孙子的鳗鱼肝汤中夹走鳗鱼吃起来的场景即是一个例子。是枝裕和在拍摄时,安排饰演爷爷的演员原田先舔自己的筷子再夹鳗鱼肝,原田一听即露出了嫌弃的表情,觉得这种行为有损自己的男子气概。但是枝裕和却坚持如此,认为这是属于角色的行为。这种关于人物小细节的坚持其实是对于日常的坚持,日常的步伐可能不会统一规整,可能会无缘由地安插些不相契合的行径,但是生命的步伐不会停滞,我们必须要找出一种生活方式。即使可能会陷于迷雾或茫然,但起居作息都要继续,平常心才是道。
是走路,不是跑步
在好莱坞的经典电影里,每一个剪辑都是有逻辑背景的,多一秒少一秒都是过错。电影叙事经常将某个演化过程集结为一个短促的记事,以求验证一般性的道德认知。可是在是枝裕和的电影里,事件的消失与构成往往都是在事件消弭中缓慢进行的,剧情在即将发生的对峙前突然坠落,是枝裕和总是刻意回避对事件发生的危急时刻的描写,偏爱去选择一些断然会被主流审美忽视的瞬间。
《无人知晓》里,小雪的死在整个状况演变中是一桩事件,但我们却看不到尸体也看不到意外发生的经过。我们仅能看到折叠椅上踮起的脚尖特写以及打完球欢喜回家的哥哥的中近景描写,小雪侧躺着并没有面对镜头,直到京子说小雪再也醒不来了,我们才发现小雪是真的死了。同样,在《如父如子》的开头,是枝裕和并没有直接拍摄医院告诉良多夫妇抱错孩子的事情,而是直接跳转到良多夫妇听完医院陈述后的反应,完全回避掉了足以聚集成事件点的高涨情绪,更没有标志震惊时刻的音乐陪衬,我们只看到过肩镜头里良多夫妇低眉抵抗惊愕的克制。
台湾地区的电影学者黄建宏评价是枝裕和的这种叙事风格为“德勒兹式的时间-影像断裂”情境。“在不再发生事件的世界,导演意图营造出一种无事件中的激进断裂,即毫无反应的不正常与异常的完全静默之间的断裂。进一步,因为事件不在影像中发生,影像的感知内容不再同观众的感知内容相应合,无法在影像中找到认同位置的观众,势将批判着影像,而影像则隐然而不对称地批判着每日行于街上的观众。”
在是枝裕和的电影叙事时间晶体中,时间充分发挥了延绵的效应,时间存在于内在意识中而不是外在事件里。于是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是枝裕和随笔集的题目为什么是“宛如走路的速度”而不是“宛如奔跑的速度”,他的电影并不追求时间的加速与空间的扩张,他要温吞记录的只是正在过去的现在和被保存的过去。


死亡与血缘的变奏
是枝裕和的电影几乎每部都涉及死亡的话题:《幻之光》里头由美子的丈夫意外自杀、《无人知晓》中小妹妹的意外死亡、《空气人形》中意外被充气娃娃杀害的店员,还有《步履不停》中被交代死亡的老父亲和长子,更不用说以死亡为线索的《下一站,天国》,至于《距离》《花之武者》《海街日记》则是以死亡为前提和故事背景。不过,这些死亡状态总是用一种娓娓道来的哀婉来表现,用一种“平常心”的状态展现。是枝裕和对死亡的书写是间接而委婉的,面对亲人离世陷入痛苦是人之常情,但日本人更习惯于隐藏自身的悲伤与难堪。
生活需要继续前进,生存下来的人们才是影片表现的重点。他希望通过死亡感知生活,由虚无反思存在的生死观去关注生存者的情感状态,给予人们在生活道路上走下去的希望。当然,是枝裕和给予人物生存希望的精神并不是纯粹的善与美,他作品中的日常同样有着残酷、自私的一面。他对亲情的描述既温情又残酷,家庭成员间总是有着偏爱、间隙、误解等各自不同的问题。《步履不停》在处理母亲这一形象时,并没有把她的类型固定化,而是展现了一个现实生活中活脱脱的母亲形象。她性格中的残酷与辛辣,她的偏心、固执、自私等一些人性中的黑暗面,混杂着母性的光环一齐被如实地表达。
她表面上对女儿关爱有加,私底下却偏心儿子良多;与再婚的儿媳看似相处融洽,实则对她心存芥蒂与防备。长子纯平因解救落水儿童而溺亡,于是每年纯平忌日她都刻意邀请被救的孩子出席,表面上殷勤招待,私底下对他却是极尽嘲笑与不满。影片描绘了一个典型的现代日本社会的家庭结构,由于家庭成员间平时沟通较少,也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使得血缘亲情成为联结家庭成员的纽带,而饮食与闲话家常则成了展现家庭关系与伦理最为直接的方式。

所以,是枝裕和善于用东方社会家庭关系里最直观的产物—血亲,来诉诸日常家庭的羁绊与疏离。在《如父如子》之前的作品里,家庭伦理剧总是会诉诸遗传、基因的血缘必然性。阿明与兄弟妹妹的无责任感对应了母亲的失职(《无人知晓》);淳史的懂事对应了母亲的坚毅(《步履不停》);内向的哥哥负责照顾失落的母亲,外向的弟弟则搭配率性的父亲(《奇迹》),孩子与家长总是会在不同程度上体现血缘基因的遗传性。而在《如父如子》里,相亲的父子却是缺乏血缘关系的,此时的血缘不再是先天的自带,没有人生而为父,也没有孩子会天生亲昵那个所谓血缘上的父亲,这里的“血缘”更像是一种安静沉淀于水底的东西,混沌柔软,一如缓慢漂浮于水中的泥沙只有在回归平静后才能沉入湖底,这个过程不是一瞬间,而是许多年,甚至可以是一生。
于是,是枝裕和最新的作品《海街日记》又重新拾起了血缘家庭的元素,大姐幸和同父异母的小妹玲的血缘关系并不像直系亲属一样强烈,我们很难说出幸邀请铃来镰仓同住的原因是因为血缘还是因为其他什么莫名的情绪,四季流转,四姐妹的时间在步履不停的日常生活中被包覆成一个结晶,散射出记忆与未来的光芒。此时,已没有必要认定是否因为血缘的关系让四姐妹能够欢欣地围坐在一起吃梅子酒和白饭鱼了,血缘已经变奏成隐匿超越式的存在。对照影片中海猫食堂的转让,那是有血缘的家庭崩裂,而香田家里梅子酒的酿造那是日久生情的非亲血缘(非直系)的浓烈。
尊重人性
日本311大地震后,是枝裕和以一名影像记录者的身份来到灾区采集资料。面对如此悲怆的场面,配合着一手资料,是枝裕和本来可以大有作为,但他没有。面对生灵涂炭的场面,他看到的是人的悲怆而不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他并不想消费灾难。由此可以看出,是枝裕和一直秉行着的创作原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尊重人性。
是枝裕和尊重人物情绪,而回避用故事的完整形式,诸如倒叙、呼应等手法,来架构影片的叙事。在记录一名艾滋病患者最后生命的《没有他的八月天》中,片头该患者还对自己仅存的性命表现出潇洒的姿态,然而随着他生命的逐渐逝去,特别是当他的视觉被破坏了之后,影片中所留下的尽是这位患者在接近死亡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安。当被拍摄者要求导演“你们就拍到这吧”,是枝裕和当机立断停止拍摄,如此才免于看到更不堪的挣扎。这是他的尺度。而在剧情片里,《幻之光》里奇异多样却沉静不动的光;《下一站,天国》中咨询与排演的录像;《距离》中死者不为人知的心情、谎称家属的男孩以及家属对于身边人的一无所知;《无人知晓》中母亲留给孩子的指甲油……是枝裕和对人性的关怀与勇敢地介入永远不会落伍,恰恰是因为流于日常的情愫命中了影片的题眼,是这些日常事物搭建起了是枝裕和对于人性的理解。
是枝裕和的作品不以故事而故事,因为故事太满就容易牵动角色而过于虚假。电视媒体只顾总结不顾描述的从业经验并没有影响到是枝裕和,反而让他重新回归人的影像,思考人的问题。“我想写一个表面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故事”,这是是枝裕和对电影的承诺,也是是枝裕和对我们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