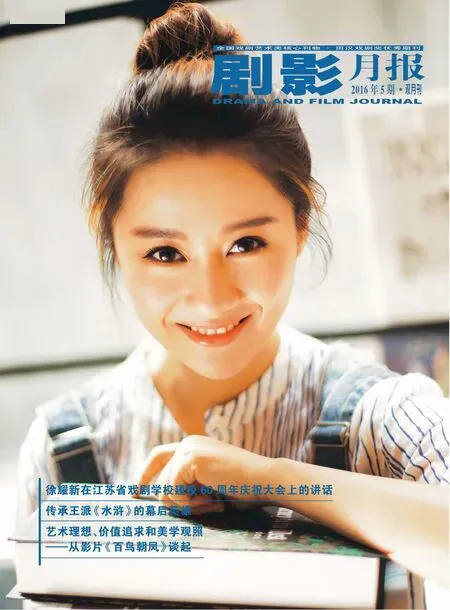昆剧《红楼梦》的人物与细节之美
——一人分饰薛宝钗和王熙凤带来的挑战
■徐思佳
昆剧《红楼梦》的人物与细节之美
——一人分饰薛宝钗和王熙凤带来的挑战
■徐思佳
江苏省昆剧院《红楼梦》折子戏的编剧张弘老师曾在文章中指出:在当今舞台上,除了以讲叙故事为主的情节剧之外,我们还需要另一种戏曲——比之逻辑的合理性,它更重情感之合理;比之故事的起承转合,它更重人物内心之跌宕起伏;比之训导,它更重趣味;比之刺激,它更重欣赏。这种审美品格,在昆曲折子戏中,有着集中地体现。《红楼梦》折子戏亦不例外。《红楼梦》之美,美在人物,美在细节。我在《红楼梦》折子戏中,一人扮演薛宝钗、王熙凤两个人物角色,如何用戏曲的程式之美塑造两个性格气质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是创作和表演的关键,也是难度所在。
众所周知,薛宝钗和王熙凤两个人物的性格和脾气秉性大相径庭,宝钗温婉大方,凤姐精明强干。在这部戏中,二者皆由我一人出演,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给观众带来差别不大,都是一人的观感和印象。因此,如何通过自身的演绎,运用戏曲的程式之美去呈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塑造出鲜明的人物特色?宝钗和凤姐二人次第出场时,让观众看到强烈的对比和反差,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画鬼神易,画人物难。若要在简单的情节中,实现人物情绪、性格特征等精致地展呈,就要求演员除了拥有深厚的唱、念、做、表的艺术功力以外,能够深入、细致地了解人物的生平、经历、性格等因素,仔细揣摩人物此情此景的心理活动,在表演中切入细微、立足细节,这样才能够准确把握表演的尺度,才有可能塑造出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
在《红楼梦·识锁》一折中,宝钗、黛玉、宝玉三者之间小儿女的呷醋,不同于村俚人家指桑骂槐、打狗撵鸡,他们是稚气的、雅致的,是酸溜溜、透亮亮的。宝玉多情而不滥情,黛玉拈酸而不做作,宝钗练达而不势力。他们所遭遇到的烦恼,都是人生最美好的烦恼,他们用来应对烦恼的姿态,也是生命本初最真诚的姿态。此情此景之中的宝钗,她的端庄稳重、温柔敦厚、豁达大度,未尝不是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需要——在贾府这个派系复杂、矛盾重重的大家族中,他不得不抱取“事不关己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待人接物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可厌之人末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因而面对黛玉的酸讽,她选择“且当檐前风铃过耳旁,闺阁雅量莫作鸡雏肠”,以此劝慰自己“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不去睬他”,如此浑然天成,方是宝钗的为人秉性。
然而宝钗即便再圆融练达,到底还是女儿家。当莺儿两次三番指出 “宝二爷玉上的八个字,与宝姑娘金锁上的八个字原是一对”时,宝钗该是又惊又急又羞又臊的,这种惊和急、羞和臊体现在宝钗的坐立之势、面上口中,需要我在表演时进行拿捏和把握。从“莺儿,你不去倒茶待客,反在这里发呆做什么?”到“胡说什么?”再到“还不倒茶去”,宝钗对莺儿的三次喝止之间,情绪是复杂的,语气要急、要略带愠怒之意,表情上则要既羞涩又要刻意掩盖羞涩,同时还要做出嗔怪之态,方能体现出此刻宝钗复杂的内心情绪。
综上而言,在表演宝钗的时候,我以闺门旦应工,更多地注重表现宝钗的端庄得体,因而身段幅度会收一点,不是很大,声音上也做了比较甜美的处理。
而到《红楼梦·弄权》一折,我以王熙凤的形象再度出场时,则要给观众强烈的反差,让观众忘了这两个角色是由我一个人演的,要让宝钗是宝钗,凤姐是凤姐。因此,王熙凤一亮相就是一个大幅度的抛袖,营造出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
《弄权》一折讲的是运送秦可卿灵柩至铁槛寺途中,王熙凤在馒头庵歇脚,期间受馒头庵主持净虚师太游说,欲插手张家婚事却佯装不想管,欲得一笔孝敬银却装作不稀罕的故事。此时的王熙凤,刚刚结束协理宁国府的风光,正可谓春风得意。加之其在贾府中显赫的地位、素日里的精干果决,因而她的眼神、语气、举手投足都透着一股傲气,对净虚师太的态度亦带有轻蔑。在这折戏中,王熙凤的唱念并不多,因此要更多地从做和表上去呈现其鲜明的人物特征,具体而言就是她的几个经典笑声、她看净虚的眼神、开关扇子的力度、她的表情神态以及声腔处理等。
在净虚陈述张家婚事时,她一方面字字听进心里,一方面又要装作不耐烦、不想管。因此,此时王熙凤的表情神态应该是不耐烦的,看净虚的眼神是不屑的,她坐在那边一边听净虚的陈述,一边做出很困倦的样子,摇扇子的动作也要显得懒怠,看净虚的眼神应该是斜向下的。当净虚以“都说府上今非昔比,徒有空架。到如今连这点小事也没奈何了,这点小手段也使不上了”的“传言”激王熙凤的时候,她要强耍狠的性格一激之下被强化,因而做了一个将扇子拍在桌上的动作,唱到“不惧不信阴司报应,决断事趁着性凭着兴”,这里的声腔处理相对比较凌厉,嗓音放得更开一些,语速相较于宝钗也要快很多,音强更强。此外动作幅度也更大,以体现其“杀伐决断”的果敢。
在表演王熙凤的时候,我更多的以正旦应工,除了以正旦稳重、端庄的表演风格去呈现其地位的显赫和个性的果决,同时也还要突出王熙凤这个人物风风火火的特点。这折戏中,王熙凤的唱念不多,更多的时间是坐在舞台上。那么如何让坐在舞台上、没有唱念的王熙凤既不显得没有戏,又不抢搭档的戏;如何拿捏“动”与“不动”之间的分寸是在表演王熙凤的时候另一个难点。对此我选择了在配合净虚师太唱念的过程中,随净虚的动而动,随净虚的止而止的处理方式。在这样的处理之下,一方面在戏份分配上比较得当,另一方面也恰好贴合了当时的剧情,展现出王熙凤佯装漫不经心的感觉。
以上是我在出演《红楼梦》折子戏过程中,如何一人分饰薛宝钗和王熙凤两个角色,如何在同一部戏中塑造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物形象的一点理性思考。至于如何更好地通过艺术手段去呈现人物,让人物形象更饱满、个性更鲜明,获得更好的演出效果,还需要在大量的演出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