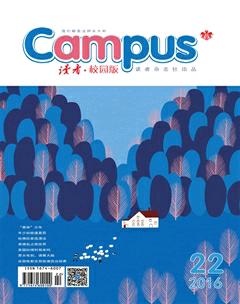孩子们在寻找怀特写过的那个农场
郭韶明
今年8月我读的书,是女儿推荐的。今年6月我推荐给她的书,她的小伙伴们都在读。E.B.怀特的3本童话——《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吹小号的天鹅》,是这些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新近最爱讨论的。
不久前的夏季旅行,女儿把《吹小号的天鹅》塞进我的旅行箱。她说:“你不是最喜欢怀特吗?连他的童话都没读过,怎么能叫喜欢?”于是某个傍晚,在爸爸们带着孩子们出去探险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乌兰布统草原静谧的湖边,看怀特的这本《吹小号的天鹅》。人们通常在3个年龄段更可能去读童书:一是自己小时候,二是当了父母以后,三是人到老年。现在,我显然正处于第二个阶段,突然特别愿意去读童书。
《吹小号的天鹅》写的是因叫声嘹亮而被称为“吹号天鹅”的一种野天鹅的故事。小天鹅路易斯生下来就是一只哑天鹅,名为吹号天鹅却发不出声音,麻烦就大了。有一天路易斯遇到心爱的天鹅小姐,他无法像其他天鹅那样用洪亮的声音求爱。
天鹅爸爸慎重地和儿子约谈了一次,在确定路易斯的确不能发声之后,说:“在你这种岁数,不能说话甚至还有点儿好处呢,这样就迫使你认真地听人家说话。世界上只管自己喋喋不休地说话的人太多了,肯听人家说话的人却很难找到。”
有一天,路易斯消失了,回来后脖子上挂着石板和石笔,原来他找朋友帮忙,去学校学会了读写。可是其他天鹅并不会读写。当他鼓起勇气给天鹅小姐写下“你好”来打招呼时,天鹅小姐却转身飞走了。这回轮到爸爸着急了。他去乐器商店给路易斯偷了一把小号。从此,路易斯有了一把小号,代替他的嗓音。
故事还很长,讲路易斯如何挣钱,如何把自己变成一位演奏家并在游船上演奏,后来又被高薪聘请到费城夜总会,挣到了一大笔钱,还清了爸爸欠乐器商店的小号钱,也历尽艰辛最终赢得了心爱姑娘的青睐。
这本童话的节奏很慢,作者娓娓道来。以至于8岁的女儿刚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还说:“我还以为这是一本烂书呢。”
我问她:“一本烂书的标准是什么?”她很直接地说:“读了好久,主角都还没有出场啊!都读了20多页,天鹅路易斯还没有出现……不过读下去才发现,这原来是一本好书呢。”
我当然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怀特在为儿童写作的时候从不换挡。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中,有人问怀特:“写像《夏洛的网》和《精灵鼠小弟》这样的儿童故事时,需要换挡吗?你的写作有没有针对某个特定年龄的读者?”
怀特回答:“任何人如果在为儿童写作的时候换挡,那么他很有可能最后会弄断挡杆。你应该往深里写,而不是往浅里写。孩子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他们是地球上最认真、最好奇、最热情、最有观察力、最敏感的读者,而且一般来说是最容易相处的读者。”
所以,小姑娘并没有被怀特漫长的开篇难住。她很快发现这是一本好书,于是推荐给她的小伙伴们。现在,他们都被怀特吸引。语文老师说:“我也没看过《吹小号的天鹅》,我们都知道《夏洛的网》。”
孩子们可能还不知道,怀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随笔作家,他在27岁的时候就与《纽约客》杂志长期合作,担任特约编辑和作者。作为《纽约客》的主要撰稿人,他奠定了影响深远的“《纽约客》文风”。
在世界儿童文学史上如此有名的怀特,其实一生只写过3部童话。《吹小号的天鹅》是最后一部。怀特之所以对这种天鹅感兴趣,是因为1965年《纽约时报》报道费城动物园一对稀有的吹号天鹅养了5只小天鹅,还刊登了照片。怀特于是写信给费城的老朋友,说他真想到费城看看,并托朋友拍些天鹅的照片并加以观察。后来怀特又收集了费城一二十年来抒情流行音乐的资料。于是,这部作品就诞生了。
在怀特去世两周后出版的一期《纽约客》上,他的继子罗杰·安戈尔在杂志的《城中闲谈》栏目里,写了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拜访怀特农场的故事。那天,病中的怀特没有接待他们,但欢迎他们的是童话故事的现场:几大家子的矮脚母鸡和小鸡在草坪上东奔西跑,胖嘟嘟的狗在尽职地摇着尾巴,还有鹅群沿着牧场小道吵吵嚷嚷。那个以前是猪圈的地方,就是小猪威尔伯的出生地;走廊是夏洛织网的地方。
如果怀特在孩子们探访的农场里劳作,那应该是这样的画面吧——他正在给鸡搭一个窝,忙得连擦汗和喝水的时间都没有,或者嘴里唠唠叨叨:“如果你没有把事情准备好,就会有一大堆麻烦等着你。”他认真地给农场里所有的装备列了一张清单,好让自己心中有数。
孩子们在寻找他们心中的那个农场,而怀特的童话就是他的生活。怀特对世间的一切保持“面对复杂,保持欢喜”的态度,他的文字让我们如此喜欢。
我从《最美的决定》这本书开始认识怀特。在女儿8岁的时候,把怀特的作品推荐给她。读完《吹小号的天鹅》之后,她天天说:“我什么时候能读你书柜里的那些怀特的作品?就《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吧,我喜欢这部。”
好吧。在她惦记我的书柜的时候,我可能也需要去读一下她的书单。与三四岁的孩子相比,8岁的孩子显然长于讨论和发现,他们会对书里的问题提出质疑和思考,他们也乐于推翻自己、推翻作者,不管作家的名头有多大。他们还可能提出很多问题,让你跟着他们一起思考。
她把书里某一页“路易斯说”中的“说”圈了出来,批评作者(或是译者):“路易斯怎么能‘说呢?它是一只哑天鹅啊,应该是‘写。”
哦,这是一个漏洞。
很快,她又有新问题了:“前言和后记是做什么的?我怎么觉得一点儿用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