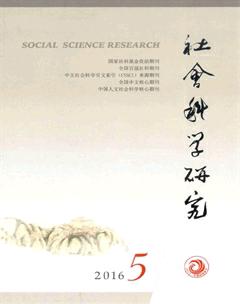东林视域下的《天主实义》与“补儒”困境
柴可辅
〔摘要〕东林学风之兴与西学入华,是明清之际颇为突出的两大社会思潮,而作为儒家时学引领者的东林人士,又与代表西学的耶稣会士,共同践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质性的中西文化思想对话。就学理言,儒学与西学存在根本性冲突,利玛窦通过降格太极和回溯“意志之天”,欲置天主于更高哲学范畴,这本与东林立场绝然龃龉。而东林基于广泛化格物与身心互为体用的思想新机,摄取《天主实义》哲学架构的首尾两端:本体实在与为善禁恶,对西学作重构性解读,终促成主流儒学立场以求同存异之心对待西学的突然闯入。然而,利玛窦“合儒”成功的同时,其自身的文化异质性亦渐受儒学思维范式之消解,《天主实义》第七篇专论性善,以分疏“良善”与“习善”重塑天人关系,正表达了西士试图突破东林视域的努力。但在天人二分的思维执定之下,西士们无法供给儒者渗透与涵摄宇宙的有效心灵之径,终陷入“补儒”困境,走向影响力的式微。
〔关键词〕东林学风;天主实义;合儒;补儒
〔中图分类号〕B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5-0153-07
一、《天主实义》的哲学架构及其
与东林儒学之龃龉东林学者大致在万历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东林书院落成的十年间完成集结,其间,他们与泰州学派大辩“无善无恶”论,而一举成为时学最重视的学术力量。与此同时,利玛窦从万历二十三年起撰写《天主实义》,到三十一年杀青出版。其间,他也在南京参与了那场规模空前的大辩论,并选择站在东林学风一边,呼应“性善”论。职是之故,《天主实义》采用中士与西士间的一问一答为其撰写体例,寄托着利玛窦证明西学在儒学体系中之合法性的冀求,并由此建构起中西文化之间哲学对话的有效平台。
基于此,利玛窦选择了阿奎那式的方法,通过理性的证明来架构西学的思想图谱。《天主实义》从人的良知良能切入,认为人具有一种超越文化地域性的普遍情感:人通过观察万物井然有序的自然运动,往往不约而同地向往某种元秩序之安排者的必然存在性,此即儒家所言“上帝”、西士所谓“天主”。(首篇)这一元秩序的安排者亦同时为绝对实有的最高本体。然而,它并非理学传统所指称的“太极”,因为太极是“理”,“理”不能离物而存,故太极只是依赖者,“不能为万物本原”。〔1〕(二篇)诚如儒家所论,最高本体创生万物而最贵人,但人的现实生活充满劳烦,反而不如禽兽自适逍遥,足证现世实为禽兽处所,人仅暂次寄居,真实归属则在后世天堂地狱。(三篇)依儒家之见,“气”为宇宙的物质基础,则“气”本身必无知觉,亦不能生创有知觉的人魂,故人魂唯系于最高本体之直接造成,使其较有始有终之万物而最近于无始无终之天主,是为有始无终的恒在者。此即构成人之所以最贵者,也是后世天堂地狱之所以对现世之人真实有效的原因。(四篇)灵魂恒在又非佛家轮回之论。设若将后世之彼的境遇作为今世之我善恶的结果,既是纵容今世之我行无忌惮,又消解了后世之彼的德性自主,最高本体绝无可能有此大不公。(五篇)西学之志,在以“意”“利”导人向善。道德工夫不应如阳明后学一般讲求所谓“为善不意”,名曰无适无莫,实常无所适从,反招致道德实践的玄虚空洞;而应“曲就小人之意”〔2〕,基于普罗大众的接受能力而谋求公共性道德实践方式来劝导善行,援日常求福之心意而导出向善本性,使其于行善之习的养成中逐渐脱落功利目的,最终归旨于善性的自然流露。(六篇)
综而观之,《天主实义》前六篇以天主论、灵魂说与天堂地狱说架构起西士一方的核心诉求,展现出始于天主实在而归于为善去恶的完整思想系统。并且,利玛窦以诉诸理性思辨的方式,将教义呈现为一种哲学论证,亦使得该系统具备与儒学的充分交集。然而,《天主实义》铺排的学理逻辑与东林为率的儒学的基本主张存在根本性冲突。它集中表现于两点。
首先,利玛窦显然认为心学与理学的区别仅是天理的居处或在人心或在事物,而无论天理究竟何所,主体的认知均是对人心与物理两者和合关系的确认,天理则必须依赖这种关系而存在,由此,天理只可能“在物后,而后岂先者之原”。〔3〕利玛窦并未真正理解明儒学术分歧的实质,一仍西学“内禀神灵,外睹物理”〔4〕的两分法先见,将心学作一种理学式的解读,又刻意回避理学“无其理则无其物”〔5〕的反驳——即从万物存在依据的角度理解天理本体性——而坚持以生成论的时间性为逻辑原点,强调“理本在物,不能生物”的思维序列〔6〕,那么他对儒学的整体性批判实质上没有涉及心学主流,而是坚信只消通过解构天理的实性、降低天理的位格,便可以直接将天学置于较儒学更高的范畴内,这既违反东林学对理学的操持,也不符合其对心学的取精。
其次,反教者众口一词地斥责西学为“媚儒窃儒而害儒者”〔7〕,姑且撇开表达上的过激,其对《天主实义》的敏感是到位的。他们所言“昔者大儒释帝为天之主宰,盖帝即天、天即帝,故尊天即尊帝也,何云上天未可为尊,并讳上帝之号而改为天主之号乎”〔8〕,正切中《天主实义》之言说的隐意,即试图将儒家的自然之天转换成意志之天,从而借由原初儒学“天”观念的多义性,推导出区别于理学正统的哲学范畴。这点已为东林所觉察,冯应京认为西学“时亦或有吾国之素所未闻,而所尝闻而未有用力者,十居九矣”〔9〕,明儒无论对西士抱何种态度,在认其与儒学思想史发展的自然进程相龃龉这点上则拥有明确共识。
二、东林视域下《天主实义》的可接受性
利玛窦与东林在根本性哲学问题上存在冲突,也基于此,东林对西士亦持论不一,唱应与批评俱在。不过,相较晚明儒佛之辩的空前激烈,西士所面临的批评要温和许多。这固然有因西学尚未形成思想气候,但更重要的是东林主动选择了一种与单纯“反教者的态度有所不同”的“主流学术立场”。〔10〕这很好地体现在他们更愿意秉持“欲以天主行中国,此其意良厚”〔11〕的宽忍心境来表达自身对西士“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12〕的警觉与规劝。“良厚”背后除了深明中西之异外,容纳西学的具体方式才是东林真正的关切点。
作为《天主实义》的破题,冯应京将“实”解为“不空”,从而以顽空风尚弹纠者的身份定位西士。李之藻则进一步发微冯氏,将西学之实归结为二:一则“谭天之所以为天甚晰”,一则“用以训善防恶”。〔13〕显然,东林着重摄取者,乃是利玛窦所证的天主实在性与道德工夫切实性,这两点恰好分居于《天主实义》逻辑链的首尾两端。
东林对利玛窦的第一个关注点——天主实在,存在着中西双方学理的紧张:一面是,由天主所代称的最高本体乃至高实有,这种一元论图式深契儒学终极实性的逻辑奠基;而另一面却是,太极实性被天主实性所取代,太极蜕变为依附于天主的第二性存在。利玛窦降格太极,是为淡化儒学的自然理性色彩,代之以强调从“制作”的角度审视原始儒家宇宙论中“上帝”的主宰与安养。在他看来,“物不能自成,必须外为者以成之”〔14〕,这就意味着天地万物并非自然偶合的产物,它如工艺一般是更高位格者意志行为的结果。
必须指出,原始儒家“意志之天”的意涵,经程朱理学洗礼后,基本已被抛弃;而西士选择重启这层意涵,这本应遭致视“自然之天”为理所当然的明儒的激烈排抵。不过,东林儒学所启迪的思想新机,却恰能提供给儒者绕开中西冲突之不可调和性的有效方式。东林认为,心念与行动本就圆融不二,每一起念均是宣告主体进入格物。而意识周流不息,格物势必也将无时无处不在,所谓“天地间触目皆物,日用间动念皆格”。〔15〕主体只要经身起念,就应一视同仁以之为“格”,如此,格“一草一木”即使于“六经《语》《孟》中未见说”,它所彰显的仍是“孔门一贯之学”。〔16〕如此,东林学实际已突破了宋儒“一草一木”说的格局。朱熹曾以“山川草木”归“形下之器”,并定义“格物”即“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17〕,却又警示“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一器用之间而望其有所得,是引沙而欲其成饭”。〔18〕理学对待“格一草一木”的审慎态度,可窥见其认知自然是有限而短暂的,但东林则强调:
故夫天地古今之赜,下至羽麟走植器数声律之微,无所不当格。〔19〕
从“天地间触目皆物”到“无所不当格”,东林一再重申格物对象不存在选择性,无论精粗深陋,均平等地向主体开放,并且除了自然事物外,同样须包含“器数声律”等社会、人工事物,即使原本不登大雅的百工技艺,也应进入学者视野。更进一步讲,当主体格物时,诚意、正心势必同时开展,于是不可斩然分格物与正心,“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明新止之物也。诚正修齐治平,皆明新止之格也。”〔20〕格物即是正心,故而说:“格者,止也、通也、正也”。〔21〕
东林所倡导的广泛化格物,一方面使得格物的对象极大地丰富起来,另一方面在道德哲学范畴内也导致认知外物获得了与修悟心性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为这两者的并行不悖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实际上构成心性学对盛行于晚明的实学思潮的回应,其主张则凝练成“苟其人志不在宏济艰难”〔22〕,“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23〕的学风。而当东林提出以“通百姓日用”为准来辨别学术真伪时,西学裹带的器用技术“高测九天,深测九渊,皆不爽毫末”〔24〕,正契合这一标准,依此得证西学义理“其神理当有所受不诬”〔25〕便有章可循。
这种契合又启迪儒者反思最高本体的传统心灵追溯模式。《天主实义》对“意志之天”的强调,是通过一种“匠人之工”〔26〕式的思维线性证得的;而东林学风所特重的广泛化格物与学以致用,则既已为工匠精神向传统道德哲学的渗透打开了思想空间。两者合力而带动起对“天”与“工”、“天道”与“人为”关系的重新沉思。把百工制作的实况推拓向天地生成之玄妙,通过技术的高度意志性来理解天道至理的实性,“如自鸣钟、铜壶滴漏、风车水碓、木牛流马、橐籥编箫,用之者以为自然,作之者几经智虑也,可仅云自然已乎?”〔27〕不造作、不走作不是德性修悟的唯一法门,现实生活中运用五官百体而几经智虑的人工,同样具备上寻本体的有效性,“自然”与“造作”乃体认天理之一体两面。可以说,正是东林学风对宋明心性学封域的修正,促使“仕者寅亮天工”〔28〕的内涵发生变化,由原本“法天而建官”所寄托的“贵忠”〔29〕之道,扩展为物生自天、工开于人的创用情怀,那些原本被排斥在道学之外存而不论、论而不议的器用事业,同样须憬然思悟、孜孜以图,并且对“存心养性之学,当不无裨益”。〔30〕如此,西士“意志之天”的向度才可能被悬置而不影响东林对西学的大体存纳。
东林的另一个关注点落在西士对“为善禁恶”的大声疾呼。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断言“恶”非实体,只是一种“善”的缺乏,而其之所以缺乏者,并非“善”在性体面前的不明,恰在于“善”在意识行为中的不彰。所以,为善去恶的道德工夫,仅就儒家善善恶恶的复性之道入手并不充分,而更应通过激发“善利恶害”〔31〕之心,实质性地规约人的意识与行为。
利玛窦强调“善利恶害”较“善善恶恶”更为时世所急需,不仅表达着西学尤重道德实践而对心性空谈保持否定的态度,其更深的意图在于从“善利恶害”之中作成一种明晰的行为责任机制。依利玛窦之见,“自己之魂只合乎自己之身,乌能以自己之魂而合乎他人之身哉?又况乎异类之身”〔32〕,身体与灵魂乃是唯一匹配的和合关系,因此,身体行为之不善的后果,将随着灵魂的恒在而牢牢锁定于道德行为者自身。从此意义而言,“善利恶害”非唯以利益考量来激励人的善念善行,它同时恰恰又构成一种内在而持续的道德紧张感,促使主体时刻保持对意识与行为的自我警觉;并且,这种道德紧张感在身魂不二的结构中,只能以身体实践中“为善禁恶”的切实落实为其表呈,而绝不能只停留于话头里。
这种以身魂不二引导主体追求“为善禁恶”之现实开展的实践气质,与东林学风的另一思想新机不谋而合。东林认为,“身”非肉身或意识的物理载体之身,彼只是躯壳,身区别于躯壳之处在它与主体意识进退同时,“譬之耳目手足,随处有伤,便浑身俱痛,以一体故也”。〔33〕所谓“一体”,强调的是身在发挥直接感受性时,主体之心始终在场,这样的“身”乃身心合一的整体,两者就存在之实态而言不可分割,彼此又都以对方的在场作为各自存在之依据:
心为体,则身为用。身为体,则心为用。无用便是落空学问。〔34〕
当身接应外物时,产生一种感,心因感而启动,此时身是本体,而心乃身之发用。同样,感而遂动之心随之现起一种应,此时则心乃本体,身循“应”而展开行动,是为发用。显然,身心交互于接洽主客体的过程中,其体用关系不能被执定。也正由于此,不能离身谈心或者离心谈身。而根据利玛窦的逻辑:“无形之心”即“本体之神”〔35〕,“夫灵魂,则神也”〔36〕,“心”与“魂”之用又均为司明司悟,则两者内涵重合,西学身魂不二之见,便在义理上与东林学的身心互为体用观念相汇流。
以身心互为体用批评心性学的蹈虚流弊,是东林的新见解,其意在要求学者立根于当世经济。陈龙正尝言“圣人见身为天性,提修身而心意知具存”,割裂身心势必导致“空理义以求真性,何以治天下国家”。〔37〕而中西双方在此会通思想,直接导致东林人更愿意将利玛窦西学的天堂观念解读为圆融身心后天理充盈的完满状态,而悬置其原意:
人死不带肉身,止是一灵。一灵所向,境界绝与人世不同,受享绝与肉身各别。〔38〕
《天主实义》所论身后唯灵是存,被儒者认为表征的是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所提供的并非躯壳的愉悦,它所指向的天堂作为至善之乡,即是超越时间维度的至善本体,升登之即是追溯终极实性的工夫践履。此番解读亦多有呼应,叶向高认为“西士以义理言”〔39〕,将天堂地狱定位为义理而非报应,明确表达了东林以儒学传统运思置换了利玛窦工夫论的逻辑前设,这样天堂地狱便“与吾儒畏天之说相类”〔40〕。而其立论所划分的今、后两世,实际上又当只是徵明性体隐与现的不同阶段,故西士为善禁恶的教化乃近于“圣学言现在不言未来”,“旨玄”而“功实”。〔41〕反之,当耶教意欲跃出这种重构性解读,还原其本义时,东林便批评其大旨将失去义理性,仅“画像而拜,视上帝如一人”,虽仍“以崇礼为事”,不免“肤浅”。〔42〕
客观而言,晚明学术的主题是“合”,这既表现为儒学内部朱、王分歧的弥合,也表现为儒学与其他哲学思想的深度交融。东林人渊源各异,但会通理学与心学以补双方不足,几乎成为共同使命,不断打破着原本的门户之见。这就使东林能为异见提供宽域,“但取其来龙真、结穴真,不必问其何方何向”。〔43〕在他们看来,如果一种学说来龙与结穴两方面真且实,则无论其间逻辑如何进行,均可接受。而判断真实与否的标准,则正是本体上坚持至善实性、工夫上主张切实践履,两者又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天主实义》恰在本体与工夫两端被认为是求实,再通过东林的重构性解读,才得以突破中西学理的冲突,被有限接受。所以在东林学风的语境下,西学与儒学汇合于“乐夫人之谭实”〔44〕而协济世道人心,也便构成晚明东林学风的显著气象,亦乃为求同存异的中西之“合”。
三、东林学风下中西人性论的
分歧:补儒困境一般而言,东林学风讲求经世致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涵养上推重真修实悟,职志于道德本体的真正落实;进学上要求返归经典,以熟习道统来明悟成己;社会生活中又强调具体事务的对处。东林思想中,终极实性在心在理并无妨害,重要的是作为学理结穴的为善去恶一条,是否具备可靠的本体支撑,以及这种支撑是否须渗透入具体生活后方能可靠地表达,其欲拾回的乃儒学教化的实效性与可确证性。依东林见地,立教之偏始自“无善无恶”,端正教化莫先于审定人性的价值。当证明何以性善时,他们提撕朱子“在天地言,则善在先性在后”〔45〕,强调“善者性之实也,善存而性存矣,善亡而性亡矣”。〔46〕以善为“元”、为实性本身,是“偏重由善以言理言性”〔47〕,此善充溢着形上意味,故东林说出“吾以善自人生而静以上,彼以善自五性感动而后”〔48〕来批评四句教中的“有善有恶意之动”,善非性之用,乃性之本。于是教化便始于形上之善、终于形下意动行为之善,“善只有一”。〔49〕无疑东林所谓“善”,是体用不二的整体,这样表达“继善成性”,扩至学风至少有两番启迪:其先,以善贯通形而上下,当下便使道德明觉备于日用人伦;其次,善先于性以凸现善之位格在人生而静以上,又势必暗示性之位格虽具本体却仍是人生而后,明善以知性便不能脱离身形具象孤立悬空。
由此,东林人性论事实上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以具体的道德实践为主体性发越之必由,并在此基石上建设形上。从晚明清初的思想史发展来看,气本论的勃兴正是对它的直接回应。无论黄宗羲“理者以气自有条理”〔50〕,还是王夫之“天人之蕴,一气而已”〔51〕,亦或颜元“若无气质,理将安附”〔52〕,诸家均试图将理内化为气之“虚位”,以化解张载而后天理与气质的紧张,其结果是气质之性不再被看成是恶之源,相反“去此气质,则性反为两间无作用之虚理”〔53〕,明善知性必须依赖欲、情、才等的正发正觉,那种试图飞越日常生活直截通透本体的洞达之教,在学理上被宣告正寝。更有甚者如陈确,以道德实践本身即为尽性,对“未发已发之说存而不论”〔54〕,可谓发东林学风余绪之极。
再看西学一方。利玛窦刊行《天主实义》而东林有所存纳,便已能说明“合儒”成功。只是这种“合儒”,是基于东林仅取西士哲学架构之逻辑链的首尾而不论其间正体的重构性解读,它直接导致西士异质性文化本位的滑落,也就难以提供给合儒之后计划展开的“补儒”以实质内容。由此,从逻辑上讲,《天主实义》第七篇以专题议论性善,是利玛窦深化合儒的同时,也在为补儒寻求出路。
篇中指出,“性”乃“物类之本体”,即人的类本质,其情则是“能推论理”(理性);“善”乃“可爱可欲”,恶则反之。〔55〕人性“以理为主,则俱可爱可欲,而本善无恶”〔56〕;而人性一旦发用,又唯赖主体对理性的自由运用,“用之善恶无定”,或用恶,则人“悮感而拂于理”,是非“鲜得其正”。〔57〕另一方面,又不可因用之善恶无定便以恶出乎理性,盖本性既善,则理性是为良能长存于心,终究可“认本病而复治疗之”。〔58〕故“恶”非实有,是“无善之谓”〔59〕,有善或无善均倚靠理性的取舍。利玛窦认为,作为人之自然禀赋的性善乃是一种“良善”,但造就“良善”者并非道德主体,而是天主,故良善之功应归绩于天,而儒家道德工夫始终直指良善,便是错认天德为我功。君子真正应用力的是运用理性纠正情用偏颇,久习义念而生义行,此“习善”方是我之功,方是真正成己,是故“德加于善其用也,在本善性体之上”。〔60〕于是所谓“学”,并非效法先贤行动语录以求达本,而即是成己之“习善”本身,“学之贵全在力行”,“在行德不在言德”。〔61〕
利玛窦人性论的关节是良善与习善的分疏。在性善的前提下,他最终将学问之道归结为“力行”,面貌上似乎颇与东林学风投缘,但这种分疏也直接导致了由合儒向补儒转身的困境。良善与习善之别,在于主体自由意志的参与程度。根据利玛窦,性体作为人的类本质秉受自天,它的存在必然先于人的意志所指,不可能是自由意志参与形成的结果,也即:人面对良善时,本质是失语的,只能为其所规定。所以良善对人而言乃是一种预成,针对良善展开道德工夫,即如拾补已然圆满者,缺乏实际意义,不是张扬主体性的有效途径。对西士而言,“善”终归是“可爱”或“可欲”的意向性表达,其归属根据的是意志之所出,而非人性之源处。由此,在他铺陈的天人关系中,良善与习善便分属于天主与人,人无法通过道德实践消泯天人藩篱,天主始终只是处于人之外的对象化存在。
这种异质文化的语境基础决定了利玛窦的天人谱式与东林学风难以折中。西士已使得天的客体性被定格,视天人的相异性为绝对,人便不可能以天人相通求得自身对宇宙全体的意义渗透,客体的存在也不可能经由性善之发越而在主体世界中获得最终的价值,那么回归到儒学语境中,天对于人间社会而言毕竟显得缺乏意义。故而在天人疏离与相互对象化之下,人的主体性本身也成为一种客体之客体的相对,人便在宇宙间丧失了稳固性,人的价值将被动摇。
事实上,中西之间的这一根本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已在明清之际揭示。张星曜曾颇为大胆地为西学辩护,责备“孔子之教能行于学人,而不能行于不学人”,此乃“孔子之疏略”。〔62〕作为孔门第一要义的“学”,是主张通过下学以求上达,最终于性体与天理的同一性中实现“万物皆备于我”式的天人合一。而利玛窦之“学”,仅是习善的具体开展,其全部内容接近于儒家的下学,却无法达成消解主客体界限的天人合一,故其对儒学的上达诉求而言是失效的。所以张氏设定不学者为补儒之侧重,以回避儒学共同体之先见的意欲,正显露出中西双方在性善问题上相互呼应的表象之下,难以弥合的深层断裂。
从此意义上说,《天主实义》所构建的性善论,实质上已将中西之分歧结构化,补儒陷入困境。这固非西士所欲,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实在于利玛窦同样误读了东林学风的内涵。东林特拔道德践履的倾向虽与西士倡导的习善若合符节,但其归旨仍在善的形上意义,也即在于“立人极”。无论东林立善为元,还是清初气论为“气质”正名,强调道德本体落实于生活的真正精神,是为了进一步拉近天人距离,以使传统形上与形下的范畴区分不至演变为割裂宇宙与主体的动因。而利玛窦则恰恰行进于东林精神的反向,而西学在清初之后逐渐淡出儒学视野,走向影响力上的式微,就并非仅仅由于“礼仪之争”等外部事件,本质则是西学天人二分的执念,只能使儒者囿于下学层面,终归无法满足他们的上达诉求。西士即便立根于实而重在践履,对儒者的精神世界而言,依然是道统之外的存在。东林领袖高攀龙曾以郭钦徙戎故事,暗讽西学“非关卫道之正”〔63〕,方以智亦曾评价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64〕,无论“卫道之正”亦或“通几”,正陈述着东林学风对道统整体性的底线立场。
四、结语
鸟瞰历史,东林人集结的每一关键时间点上,均有《天主实义》的实质性进展。1593年神宗定性清流结党,东林精神初现;一年后利玛窦开始修订《天主实义》,并先期出版《交友论》,颇有助于清流以道结交。1598年,顾宪成等东林核心成员以“性善”批驳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之谓,东林求实思潮掀起;不过一年,利玛窦便在与黄洪恩的辩论中阐发自己的性善论,并将之录入《天主实义》,以唱应东林学术。而《天主实义》最终出版,又在东林书院成立后一年。可以说,《天主实义》文本中与利玛窦展开对话的“中士”,正是浸淫于东林思潮之下。事实上,《天主实义》的出版《交友论》那样,是为拓展交流空间所做的文化试探。在利玛窦常居北京之后,更多地充当着被问者的角色,无论冯应京亦或冯琦,乃至叶向高,东林人之接近西士,是为能从对话之中获得对其自身心灵有所补益的内容,他们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进入西学语境。因此,《天主实义》承担着这样一种责任:在儒者关于西学那既有却尚属支离的印象支配下,利玛窦需进一步系统化儒者的认知,回应儒者的问题意识,并且,这种回应被自觉地置于哲学范畴内。然而,东林人对现实的政治与人生已有先见,他们接触西士寻求学理摄取,更多是因耶教与东林之同,而非两者之异。而当利玛窦意识到“合儒”的成功,可能导致西学的文化异质性为东林的哲学诉求所消解时,他阐发的性善论,实为设定一条“合儒”的底线,也即“补儒”的基点。不过,天人相分的思维方式是难以被东林接受的,也正因此,利玛窦直接应和东林思潮与时代精神的性善论阐发,竟只字不见于冯应京与李之藻的序文中,这一点颇值玩味。
〔参考文献〕
〔1〕〔2〕〔3〕〔4〕〔5〕〔14〕〔26〕〔31〕〔32〕〔35〕〔36〕〔55〕〔56〕〔57〕〔58〕〔59〕〔60〕〔61〕利玛窦.天主实义〔M〕.兖州府天主堂活版,1936:11,54,11,2,11,3,12,48,41,65,20,62,62,63,63,63,63,67.
〔6〕〔27〕〔38〕杨廷筠.代疑篇〔M〕//吴祖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4:503,507,513.
〔7〕黄贞.尊儒亟镜叙〔M〕//夏瑰琦主编.圣朝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155.
〔8〕邹维琏.辟邪管见录〔M〕//夏瑰琦主编.圣朝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289.
〔9〕冯应京.天主实义序〔M〕//利玛窦.天主实义.兖州府天主堂活版,1936:6.
〔10〕张晓林.天主实义与中国学统——文化互动与诠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296.
〔11〕邹元标.答西国利玛窦〔O〕//吉水邹忠介公愿学集:卷三.明万历刻本.
〔12〕李贽.续焚书〔M〕//李贽全集注:第三册.张建业,张岚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09.
〔13〕〔30〕李之藻.天主实义重刻序〔M〕//利玛窦.天主实义.兖州府天主堂活版,1936:2,4.
〔15〕〔20〕〔21〕高攀龙.王仪寰先生格物说小序〔M〕//高子遗书:卷九下.明崇祯刻本.
〔16〕高攀龙.答泾阳先生论格物〔O〕//高子遗书:卷八上.明崇祯刻本.
〔17〕黎靖德.朱子语类: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9:1496.
〔1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756.
〔19〕高攀龙.塾训韵律序〔O〕//高子遗书:卷九上.明崇祯刻本.
〔22〕〔49〕〔50〕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90,1461,1175.
〔23〕高攀龙.东林会语〔O〕//高子遗书:卷五.明崇祯刻本.
〔24〕〔25〕〔28〕〔44〕冯应京.天主实义序〔M〕//利玛窦.天主实义.兖州府天主堂活版,1936:6,6,5,7.
〔2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5:1100.
〔33〕〔34〕高攀龙.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M〕//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六.清雍正刻本.
〔37〕〔42〕陈龙正.几亭外传:卷二〔M〕.明崇祯刻本.
〔39〕〔40〕叶向高.苍霞余草〔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449,450.
〔41〕周炳谟.重刻畸人十篇引〔M〕//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503.
〔43〕高攀龙.答邹南皋先生一〔O〕//高子遗书:卷八下.明崇祯刻本.
〔45〕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9:83.
〔46〕顾宪成.东林会约〔O〕//顾端文公遗书.清康熙刻本.
〔47〕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502.
〔48〕高攀龙.方本庵先生性善绎序〔O〕//高子遗书:卷九上.明崇祯刻本.
〔51〕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1052.
〔52〕〔53〕颜元.习斋四存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9,39.
〔54〕陈确.陈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471.
〔62〕张星曜.天儒同异考〔O〕.国家图书馆馆藏清代抄本.
〔63〕高攀龙.与沈铭镇二〔O〕//高子遗书:卷八下.明崇祯刻本.
〔64〕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M〕.清光绪宁静堂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