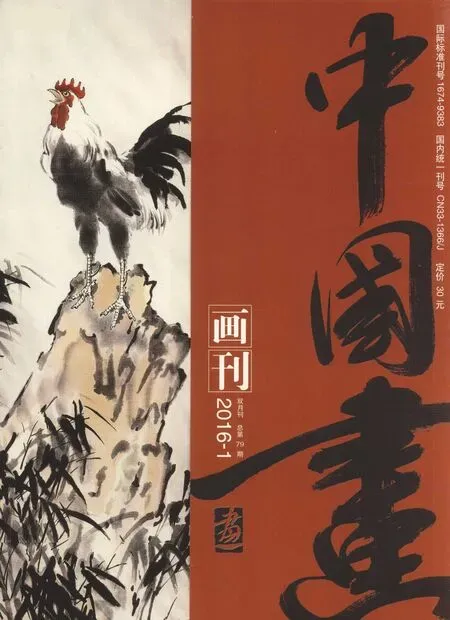谈颖人为人与颖人作画
文/徐永祥
谈颖人为人与颖人作画
文/徐永祥
我和颖人的关系始于1947年苏州美专同学2年。1949年,我们一起转学,考取了杭州国立艺专(现中国美术学院),又一起留校工作,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一甲子60年的沧桑,我们从未分开,共同经历了我们这辈人特有的历史旅程,风风雨雨,甜酸苦辣,至今还算不清楚我们这代人的得失账,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活得很丰富。
半个世纪的相聚交往,对于颖人的处世哲学、人格修养、待人接物我不可谓不知。凡和颖人交往过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他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性格有点内向,讷于言辞,少于人事,能容忍、肯吃亏,这些印象挺好,因为他确实是个善良君子。但也有人视他为软弱可欺,老想去占他便宜,这就叫不识“如来真相”了。殊不知我们这位朱颖人先生,当他意识到他的人格底线遭到攻击时,他会偶露峥嵘,奋起还击。曾经有一位公认为惹不起的先生,在与颖人共事中发生了矛盾,颖人先是退避三舍,一再忍让,然而对方不肯罢休,颖人反击了,并且是锲而不舍地反击,直到那位仁兄灰头土脸,远远见到颖人迎面走来就赶快改道避让,这一事件成了校园中的美谈,人们奇怪这位仁兄怎么败在朱颖人手下。
而我深知颖人柔中带刚性格的由来,哪怕是面对冲锋枪,他也会突然发出愠怒的抗议。

井冈山上所见 69cm×69cm 2007年 朱颖人
事情发生在1949年秋,我们一行4位同学,自苏州乘轮船转道嘉兴到杭州国立艺专报到。当轮船经过嘉兴王江泾的河面时,沦为土匪的国民党散兵,用几支冲锋枪向贴近轮船的水面扫射,激起的水花直溅到我们脸上。土匪劫持了轮船,魂飞魄散的二十几位旅客被驱上岸。身上财物被搜刮一空后,我们被勒令手抱着头挤在一起,不许发出声音,左右两支冲锋枪瞄准我们。土匪们开始把轮船上的货物及旅客行囊全部搬到土匪的船上,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箱子一件件地抛向贼船,心想这回是要变成彻底的无产者了。就在我们4个同学的铺盖卷也被抛上贼船时,俘虏群中突然发出颖人不无愠意的抗议声:“你们怎么可以把我们的铺盖被子都拿走,我们是学生,这里没有亲友,到晚上这不是要冻死我们吗?”这声音划破压抑沉闷,把土匪和俘虏都吓了一跳。小土匪把冲锋枪弄得格格响,威胁说:“再讲话,老子要开枪!”我心想好你个朱颖人,“裤子”都给抢走了,还想讨回“一双袜子”,这不是虎口里讨骨头吗?但颖人的抗议居然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土匪头子下令把几个学生的铺盖卷丢回到轮船上。在嘉兴火车站一个通宵,我们4个同学总算没挨冻。事后我们开他玩笑:你怎么会在这该死的时候发出如此抗议,要知道强盗心里也很紧张,万一扣动了扳机,你我不都完了吗?他的回答是:没想那么多,只觉得铺盖都不留给我们太气人了。这个“太气人”就是颖人的人格底线。

芦花明月夜 有客听爬沙 70cm×42cm 约20世纪70年代 朱颖人(题款:吴之)
2002年底,他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三四天后我询问他夫人,得到沮丧的回答:是癌症,已经动了手术。近几年来,颖人正是创作旺期,大出作品的时候,癌症的降临使朋友们都担心他是否挡得住这突然的袭击。当我去探望他时,他是出乎我意料的平静,笑嘻嘻的,精神状态至少使我有点宽心。我们平时聊天时,他曾经给癌症取了个别名叫“中头彩”。所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头彩”了?他笑嘻嘻地回答:“中头彩”了。他表现的乐天、达观、谈笑风生,如此精神状态肯定有助于他快速康复。他有着非常豁达的生死观,很多朋友也许并不了解这位平时有点过分柔和性格的先生,在这紧要关头,他会透露出无畏的精神,也许这和他小时候“真正”死过一回不无关系。

晨曦初逗 70cm×48cm 2014年 朱颖人

雪白一团洁此身 69cm×70cm 2015年 朱颖人
当他读小学时,他几乎死去,父母伤心欲绝,已经准备衣服等着料理后事了,就在即将结束他的小生命时,阎罗王大概发现拘错了一个未来的优秀画家。他醒过来了,一直活到现在。好人应该长命的,更多更好的作品还有待他完成。
在学艺的道路上我们几乎有完全相同的经历,受业于同一批声名卓著的师长。及至毕业留校后,由于当时学校的办学需要,我们在学业上分道扬镳了,他成了国画家,而我学油画。
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人品画品融而为一,颖人的花鸟作品可以说是他人格、精神、个性的图像物化,亲切自然不事造作,清纯优美,悦目动情,生机盎然发人向上,这是颖人作品拥有广泛观众基础的重要原因。
颖人的艺术观是以朴素的人民性为基础的,他始终相信作品是要给人看的,是要接受观众褒贬的。在他的《砚边杂记》中,他明白宣告了他的艺术主张:在绘画理论上“不求绝对,仅求相对,能拥有相对多的观众获得美的启示与美的享受就好了”。语言朴素简洁,切中时弊。他从不为那些高喊自我的晦涩口号所动摇,不追求“和者必寡”的“阳春白雪”,同时又摈弃了低格调和庸俗的“下里巴人”。在雅赏、俗赏、雅俗共赏这三个审美层次上,他选择了雅俗共赏,这是他现实主义观念和人民性的印证,这也是他的作品获得广泛读者的第二个因素。

指墨梅花 40cm×35cm 2014年 朱颖人
作为一个花鸟画家,颖人的绘画语言日趋丰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作品的文脉是清晰的,但他走进花鸟画这一领域则颇有点曲折。离开家乡初出吴门,在进入苏州美专前,他曾在家乡常熟跟乡贤花鸟画家蔡卓群学习。进入苏州美专后,以比别人早受启蒙的优势,国画成绩一直很突出,在同学中已经小有名气。在进入杭州国立艺专后,由于当时“旧”国画面临改造的命运,加上整个课程设置和授业老师几乎全是油画家,我们三年级的基础课老师相继是林风眠、关良、倪贻德,创作课老师是莫朴、彦涵、王流秋、张漾兮、黎冰鸿等。颖人彻底抛弃了花鸟画而迷上了“洋画”,并且他特别欣赏巴洛克代表画家鲁本斯,班上甚至有同学开他玩笑给他起了个绰号称他是“朱本斯”。这三年的学习,我们受益匪浅,打下了“学院派”所需的坚实基础。直至1959年,学校突然要朱颖人改弦易辙,重执毛笔再学国画。开始他颇想不通,最后是无奈地服从。今天看来就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毕竟成了一名出色的花鸟画家。

万年枝 69cm×46cm 2011年 朱颖人
颖人得到了吴茀之先生的悉心亲授,又耳濡目染潘天寿、黄宾虹等老师“旁敲侧击”的潜移默化。他博采众长,以乃师机巧灵变的笔墨,结合潘老“强其骨”及宾虹先生“笔墨不移”之精神,奠定了他练笔运墨的基础。他中规中矩地钻研传统,而又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形成了在坚实的传统基础上融进时代特征的画风,自成一格。它拓展了花鸟画的取材,在画面构成上,恪守法度又力求多变,柔中寓刚的运笔用墨,明快间接的造型设色,引人入胜,意蕴无穷,成了他获得广泛观众的又一因素。
剖析几幅作品,或许有助于解读颖人的花鸟画。
颖人善画松鼠,一般的花鸟画家少有涉及,而颖人对此小精灵独有钟爱。画松鼠真可算是他一绝,寥寥数笔即跃然纸上,造型准确,神气活现,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其实他为画松鼠费尽心机。且看1988年的《松鼠图》上的题跋:“松鼠松鼠,振笔追视,废纸三千,如何求是?”另一幅《顽石细藤图》是他的代表作品:大块通灵剔透的浓墨和纤细游动的细藤以及淡雅的设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又不失和谐的律动;在画面构成上,点、线、面的组合以及虚实相生的处理无懈可击。颖人重视并善于在作品题跋中拓宽画面意境和内涵。请看《顽石细藤图》的题跋:“石得透则灵,人得透则直,为政得透则廉明,廉明通达则能与民同乐,今作顽石细藤以求人之巧拙,可乎”。题跋给画面增加了深刻的寓意,结尾“可乎”二字给观者留下了自由思考的空间,因为艺术是无法强加的。

灵鹭涉清江 69cm×6946cm 2007年 朱颖人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灵秀,苏杭独占。颖人少长于苏州,发祥于杭州,他的花鸟作品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那是“天堂”里的花鸟。尽管他在苏州时间不长,但早年的情怀印痕犹在,在某些作品中,仿佛会见到姑苏流翠,听到吴侬软语。我们无需在颖人的作品中苛求风云千里、龙腾虎啸的气魄,那不属于他,用他自己的话说:“各个时代又有各个时代的成就。然而得之于雄健,失之于秀丽;得之于雅逸,失之于浑厚的人又有多少?获得全才之难可见也。”他的才能观和他的艺术取向是非常现实的,如果每个画家都是全才,也就没有了百花齐放,绘画会变得非常单调。还是用颖人的话来总结:“幸运的是社会并未强求全才。”■
原载《美术报》2008年2月2日第15版“画家”
(辑入《热烈祝贺朱颖人教授从艺60周年名家访谈·2》)
手稿原题《简谈颖人为人,浅谈颖人作画》
——记花鸟画家许常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