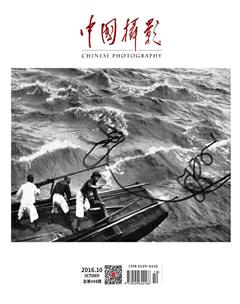马格南手稿:让经典重回母体
郑梓煜
马格南是谁?这是个一言难尽的问题。Magnum 这个在拉丁文中意为“伟大、顽强”的词语,自1947年开始多了一层特定的含义:一批自由摄影师构成的共同体,它兼容了一群个性鲜明的特立独行者,以一种世人皆曰不可能的方式岿然而立。即使今天画报时代已然终结,唱衰马格南的声音萦然在耳,它却不乏优雅地存在着。
对关注20世纪摄影史的人而言,马格南代表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持续至今的传奇,一个与历史同在的另类旁观者与记录者。1997年,英国记者卢塞尔·米勒(Russell Miller)在为马格南所写的传记标题中,以“身处历史前线五十年”来概括这种状态,而这本书的中文版则采用了一个更为形象的标题:世界的眼睛。确实,马格南自创立以来见证了全球重大事务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通过与《生活》等媒体的长期合作,树立了报道与纪实摄影的世界标杆。正是在这一历程中,马格南摄影师创造了诸多在摄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经典名作,这些作品已经成为特定时代的视觉符号。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这些经典图像的传播早已超饱和,即使并不关注摄影的普通人,也必定曾与其中的某几幅照片不期而遇。但是,作为2016深圳(福田)国际城区影像节的重头戏,于9月29日至10月22日在深圳大学美术馆举办的《马格南手稿:摄影经典的诞生》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膜拜经典的展览。相反,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解构”经典的展览。所谓“解构”,是因为经典的塑造常常伴随着去语境化、符号化与神秘化的过程,而这个展览则是把这些名作的原始底片印样和文献一同展现出来,共同构成一个复合体:经典照片与底片印样并置展示,辅以早期发表的文献资料。观者可以在底片印样上清晰地看到拍下经典名作的那一卷胶片中还记录了什么,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入摄影师的现场视角,想象他在当时的运动轨迹与观看角度,也可以试着推敲编辑过程中的偏好与取舍,为什么是这一幅而不是那一幅照片被最终选中成为正式作品?这种让经典回到它诞生的“母体”中策展思路,以还原情境的方式让经典祛魅归真。
在漫长的胶片时代,摄影始终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过程,按下快门的时刻你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底片上留下了什么,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直至底片被冲洗出来,印样第一次被制作出来才终止。底片印样是摄影师与自己作品的第一次真正对视与亲密接触,眼睛和印样之间仅隔着放大镜的距离,呼吸的气息拂过纸面,记号笔在被选中的照片上留下印记……这种初见并非总是怦然心动,艾略特·厄维特(Elliot Erwitt)说:“看自己的底片印样经常让我极度沮丧。人总是怀有太高的预期,却又经常难以实现。”大卫·艾伦·哈维(David Alan Harvey)甚至说:“我讨厌看自己的作品,经常能拖则拖,因为我清楚它们很难达到我自己的预期。”通常,每卷胶卷中只有少数的几幅照片会被放大,只有更少数的照片会进入大众传播领域,而最终成为被铭记的经典者,则更是大浪淘沙,余者寥寥。
正因如此,观看底片印样虽然是负片时代无法略过的工作程序,但却仅仅是摄影师、图片编辑、代理机构和少数亲密者之间所进行的私密行动。底片印样仅仅被当作一种中间产物,当它完成了照片初选的使命,便开始了在档案盒中的漫长沉睡,甚至被弃置不顾。就连底片本身,也可能被修剪分割,流失散佚。
但是,直至2000年,申请加入马格南图片社的新成员仍被要求提交底片印样,而非精心编辑过的作品。因为底片印样还原了一个摄影师在现场的工作状态与即时反应,所遭遇的困窘与突围。既记录了灵光闪现,也记录了阴差阳错,巨细无靡,诚实坦率。也正因承载了太多的信息,底片印样之于大多摄影师而言,是一种近乎私密的存在。又是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这位喜欢在评判新成员作品时拿着底片印样翻来转去地琢磨的摄影师说:“底片印样上充斥着涂抹的痕迹和琐碎的残余。一个摄影展或者一本画册如同一场待客之宴,主人通常不会让客人去嗅一下厨房的坛坛罐罐,更不可能让他们去嗅垃圾桶里的果皮……”1958年,一位马格南职员把卡蒂埃-布勒松的底片印样直接给了《巴黎竞赛》(Paris Match)的图片编辑,他便在亲笔信中谆谆教导:“底片印样是如此富含激情,构成了摄影师的内心独白,但却不可避免地充满瑕疵,因为拍照片不是像坐在客厅修剪插花。你不能把这份内心独白向一个偶然出现的调查者和盘托出。”卡蒂埃-布勒松把剪去自己不满意的底片形容为“剪掉自己的指甲”,卡帕(Robert Capa)也从不把底片和印样当作需要原样保存的珍贵档案。在这次展览中,卡蒂埃-布勒松拍摄塞维利亚战争废墟中的孩子的那幅著名作品的底片印样并非原始档案,而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把被他剪开的单张底片根据推测重新还原的结果。
在这个展览的中文标题中,我把这些底片印样称为“手稿”,是因为唯有这个词,才能在中文语境中准确地传达这些底片印样之于经典作品和摄影史的意义。有别于摄影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机器成像”与“化学反应”的产物,手稿之“手”,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创作者手泽余温的独特意涵,象征着曾经的亲密接触与费心劳神。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画家手稿、音乐家手稿以及作家手稿的文献价值,在艺术展览中把艺术家的创作手稿和正式作品并置呈现的成例并不鲜见,但是在摄影的世界里,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
关于摄影,有太多的成见亟待祛除。或许是因为卡蒂埃-布勒松创造的“决定性瞬间”这一概念过于深入人心,以至于很多人以为优秀的摄影师拍照片,应该如同狙击手那般精准而节制,只有在决定性瞬间来临之时才冷静优雅地按动快门。因此,他们迷信经典的诞生是妙不可言的因缘际会,又是例无虚发的盖世神功。而长期以来对经典作品的去语境化传播、膜拜、阐释更是无形中强化了这种成见,这些经典影像成为漂浮在话语空间中的冷艳孤芳,仿佛横空出世,看不清来路,也望不到去向。

然而,虽然拥有瞬间定格画面的神奇天赋,摄影却从来都不是一次性的捕获,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观看、选择与修正。时间是一具永生不灭的躯体,分秒的演进是亘古不息的新陈代谢,在摄影术发明以前,从来没有一把足够锋利的手术刀,可以从时间的躯体上切下薄如细胞的一层,置于透镜的焦点之下,凝视、封印、永存或者散佚。照片是瞬间的切片,是凝固的视线,底片印样呈现的却是一股时间流,是流动的情境,是鲜活的历史上下文。我们的视线被“好照片”的标准所禁锢,理所当然地忽略了作为必然代价的“坏照片”所可能承载的信息与价值。
未经剪辑的原始底片印样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属性,它使眼见为实的古老信条被充分证明,使摄影被认为与生俱来的“真实性”触手可及。单张照片可能被完美地摆布导演,连续的底片印样却总会留下蛛丝马迹。1972年,吉勒斯·佩雷斯(Gilles Peress)拍摄北爱尔兰军警血腥镇压抗议者的《血色星期天》的底片印样,便作为重要的历史证据,推翻了特别法庭文过饰非的调查结论,促成了北爱尔兰历史的重大转折。而在雷内·布里(René Burri)1963年的底片印样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切·格瓦拉(Ernesto" Che " Guevara)意气风发地点起雪茄,慷慨激昂地回答提问,又略带疲惫地揉捏双眼……那幅精选出来的叼着雪茄的切·格瓦拉,在广泛传播中所自带的强烈的偶像光芒,在底片印样中平实退隐。
在一个数码成像技术高度发达、图像以天文数字的量级被生产、消费与遗忘的年代,谈论这些似乎已是不合时宜,或者仅仅是一种略带感伤的怀旧,正如现任马格南主席马丁·帕尔(Martin Parr)把Magnum Contact Sheets1的出版称为“底片印样的墓志铭”。今天摄影师的烦恼是永远不够时间去仔细翻看自己电脑硬盘里动辄以 TB 级计算的海量照片。摄影变得越发方生方死,从按下快门到看见照片,时间的间隔已可忽略不计,再也不会有那种等待中的忐忑或烦躁、初见时的懊恼或狂喜,更不会有一份记录这种初见的诚实印样。哪个摄影师没有在回放照片时快速地删除掉那些记录了令人难堪的技术错误的废片呢?即使储存卡是海量的,自尊心却是脆弱的。
正当我们筹备这个展览的时候,传来93岁的马克·吕布(Marc Riboud)逝世的消息,这或许真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但是感谢底片印样,我们得以想象1953年,年轻的马克·吕布如何略带羞涩地在埃菲尔铁塔上与油漆工人们一起进退腾挪,就连他在铁塔上实践卡蒂埃-布勒松教给他的“把取景器倒过来看作品构图”的秘笈而差点从铁塔上摔下来的轶事,也变得真切起来。马克·吕布在他超过半世纪的摄影生涯中数十次踏足中国,深圳这座象征着中国现代化革新成就的城市曾经是他重要的观察对象。这次在深圳的《马格南手稿》展览包含了84件经典作品以及相应的底片印样与文献,囊括了包括马克·吕布在内的60余位马格南成员的作品,最早的作品由卡蒂埃-布勒松拍摄于1933年。这个展览经历了在意大利的Forte di Bard城堡、德国的 C/O基金会、荷兰的 FOAM 摄影博物馆等机构的巡展后首次来到中国,这也是马格南摄影师作为一个集体在中国的首次正式亮相。为了促成这个展览在中国的首展,深圳(福田)国际城区影像节的主办方付出了极大的诚意与努力。
经典之外,手稿重塑了另一部历史,一部观看方式的历史。让经典重回母体,就是试图重建这种历史情境的努力。
(本文作者为摄影与视觉文化研究者、策展人,中山大学视觉传播方向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