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革期间撰写回忆录
祖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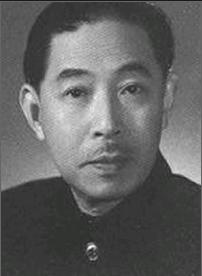
一..见猎而心动
文革开始后,茅盾除了应付纷至沓来的外调者和自理点家务外,每天大多是阅读报纸和两本“大参考”,了解国内外形势,没有多少时间再看其他书籍(其时那些“三突出”式的作品他也不愿看)。1969年国庆节,他被剥夺了出席天安门庆典的资格,连两本“大参考”也停发了。不久老伴又先他而谢世。此后,老人对一切似乎都看开了,心境反趋于平静。特别是1970年春,儿孙们搬来同住后,家务的烦恼摆脱了,老人开始利用闲暇,阅读起历史著作与翻译作品来。他在6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
三月至六月,计读书如下:郭沫若主编之《中国史稿》第一、二册,谢缅纳夫之《中世纪史》,法人EditaMorris(女)的《广岛之花》英译本。其间,曾浏览别的书,不具书。
值得注意的是,老人的兴趣忽然转向中国古代史与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时代的历史,似乎想从中思考些什么,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需特别提到一件事:1971年初,当茅盾读了杨熙龄于50年代翻译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一书后,那似乎早已熄灭的激情——对思想与艺术的追求之火,在他内心深处重又喷燃起来。辛亥革命前,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曾把拜伦推崇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之“宗主”,盛赞他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为:“波谲云诡,世为之惊绝。”64年后,已入垂暮之年的茅盾,同样给这部充满对暴政与邪恶的憎恨和对自由与正义的追求的诗篇,予以高度的评价;并浮想联翩,萌生了以骚体重译拜伦的这部抒情史诗的念头。他写道:
昨日阅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完。此为杨熙龄译本,1956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印本。译笔算是不差的,因为原作是斯宾塞诗体,极不易译;想到这一点,应当说译本是好的。原作上下古今,论史感怀,描写大自然,包罗万有,洋洋洒洒,屈原《离骚》差可比拟,而无其宏博。在西欧,亦无第二人尝此格。从这里看,又觉得译本(散文,语体)太简陋了。余老矣,虽见猎而心动,徒搁笔而兴叹。倘在廿年前,假我时日,试以骚体译之,不识能差强人意否?(1971年2月1—9日日记)
在茅盾文革期间的日记里,这种一反起居记与流水账式的写法,专就一部文学名著及其译本进行品评,流露出内心的冲动与壮志难酬的感慨,实为罕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著称的茅盾,晚年身处逆境,忽然对浪漫主义文学巨子拜伦的诗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必有某些东西强烈地吸引住他,才能唤起他沉寂已久的心灵深处之火花。茅盾的这一声长叹,也说明了这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笔耕一生的大师,即使在十年浩劫的灾难岁月里,心灵深处的火光也没有熄灭。据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后来能以近八旬的高龄,开始着手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和为撰写回忆录进行长久而认真的准备了。
茅盾逝世以后,为编辑40卷本的《茅盾全集》,在搜集整理其著述过程中,茅盾的儿子韦韬(原名沈霜)透露他父亲曾续写过《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情况。
大约在1973年,韦韬夫妇见父亲闲居无事,曾建议他把《霜叶红似二月花》续写下去。他们劝道:“如今反正没有什么事可做,你何不悄悄地写下来,虽然现在不能发表,我们把它留着也是好的。”茅盾经过认真考虑,终于同意了。
事实上,早在1942年—1943年间,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刚问世时,就有朋友劝他续写下去,终因世事变迁未能如愿。茅盾在1958年写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新版后记》里说过,这部书本来是一部规模比较大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当初(1942年)迫于经济不得不将这一部分先出版,现在就应当暂时停印,等待全书脱稿后一总再印。但是惭愧得很,荏苒数年,没有续写一字,——而且自审精力和时间都未必有可能照原来计划中的规模把它写完成了。又说:“如果我能够多活几年,找出时间,续成此书,了此宿愿,那当然更好,不过,我不敢在这里开支票。”这回,经儿子儿媳的提醒与支持,老人果真动手来了此30余年来未曾了却的宿愿。他酝酿、构思新的续写计划,写出一份比较详细的提纲,积累了一些素材,并且动手写了一些章节段落。
十分遗憾的是,1974年12月初,他们全家从东四头条搬到交道口新居后,此事就停下来。大约因续写计划规模太大而茅盾年事已高、精力不济,老人自忖一时难以完成,就索性把它搁置一旁了。现在由他亲属珍存下来的,就只有一份较详细的提纲与已写成的若干章节。
二.二十余盘录音磁带
茅盾在文革期间做的另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始为撰写回忆录做淮备。在儿子儿媳的帮助下,他曾悄悄地进行了持续一年之久的题述录音。这一工作,为他在粉碎“四人帮”后,撰写《我走过的道路》一书,勾勒了大体的轮廓,奠定一个初步的基础。
1973年以后,茅盾读过不少人物传记与回忆录,如《丘吉尔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艾登回忆录》等。这是否对他后来着手准备写自己的回忆录,起过一定的触动作用呢?
茅盾开始回忆录的准备工作,始于1975年。是年初,邓小平复出,周总理在四届人代会上重申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文艺界出现电影《海霞》事件;江青因《红都女皇》事受到中央批评;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这一消息,最先是胡愈之告诉茅盾的)——国内的形势开始出现转机。老人从知交和亲属处不断听到一些喜人的“小道消息”,从报纸上也看出这一变化的端倪,感到十分高兴,期望着国家从此能步入正常的轨道。这时,一些好心的同志通过茅盾家属,建议他着手写回忆录,为后世留下珍贵的资料。其实,茅盾及其亲属已有所考虑,只是对外没有吭声,也尚未真正动手而已。然而,不久形势又急转直下,同年8月,“四人帮”又挑起“评《水浒》、批宋江”,抓“现代投降派”的恶风;紧接着“四人帮”大批文艺界的所谓“右倾翻案风”——种种不祥的迹象,使茅盾深感不安,他和儿子分析形势,感到一场新的灾难又将来临。就在这种形势下,颇有点韬略的儿子,又向父亲提出搞回忆录的问题。此时老人也自感来日无多,很想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所走过的道路,作一次系统的回忆与清理,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经过商量,他们决定采取口述录音的办法。
当时,家里只有一个从旧货店买来的小录音机,他们就利用这台旧录音机,由茅盾一段一段地口述,儿子、媳妇帮他录下来。茅盾从家庭和童少年时代的事说起,每天讲一点,录一点。就这样,从1975年底起,直到1976年底才结束,先后录制了20多盘磁带。
在录音过程中,茅盾是顺着自己的经历,凭回忆梳理出一个大体的轮廓,其中难免有所跳漏。因此,儿子时常从旁提问,建议他补讲一些问题。凡记得起来的,老人都作了补叙。他一直讲到全国解放为止,表示解放以后的事,就不用讲了。儿子又建议,解放后也可以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讲讲,如建国初期是怎样当上文化部长的;1957年同毛主席访苏情况以及一些知交故旧的情况。于是老人又讲述了一些解放后的重要经历与交往情况。
1976年,茅盾跨进80高龄。面对“四人帮”垮台前夕风云变幻、扑朔迷离的形势,回忆起自己一生所经历的烽火岁月与文坛风云,老人不禁感慨万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为之追求、献身的共产主义理想;他通过历史画卷式的艺术世界所呼唤的祖国的春天;他亲闻目睹无数先烈、朋辈用鲜血所换来的新中国,在十年浩劫中已被“四人帮”践踏得面目全非。他只能以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来回首往事,并对以往的经历与作为产生了一种“俯仰愧平生,虚名不副实”的自责心理。他这年所写的那首著名的《八十自述》诗里,就明显地流露出这种复杂的心情:
忽然已八十,始愿所未及。俯仰愧平生,虚名不副实。昔我少也孤,慈母兼父职。管教虽从严,母心常戚戚。儿幼偶游戏,何忍便扑责。旁人冷言语,谓此乃姑息。众口可铄金,母心亦稍惑。沉思忽展颜,我自有准则。大节贵不亏,小德许出入。课儿攻诗史,岁终勤考绩。
这似乎是一首尚未写完的诗。从题目看,作者是想就自己一生的经历与道路,来抒怀述志,情真意切而又朴实无华,完全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开首的两句,带有总揽全诗的意味。下面却只写了童少年时禀承慈训,即戛然而止,留下中途辍笔的明显痕迹。其所以辍笔,大约在当年的情势下,这样的自述难以终篇。其时,“四人帮”加给他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这顶莫须有的大帽,尚如幽灵般悬在他头顶,且世事沧桑,自己毕生所从事的文学与社会活动,涉及的许多同时代人,也大多不是被关进“牛棚”就是被打入冷宫。凡此种种,都使他的《八十自述》戛然而止。不过,从字里行间,我们仍可以感受到作者沉重、压抑的心情,感受到他对自己一生的行止并未失去自信。“大节贵不亏,小德许出入”,就是一种对诽谤者的答复。
1976年10月10日,韦韬首先得悉“四人帮”已被抓捕的消息,当天兴匆匆地赶回家告诉父亲。茅盾听后十分兴奋,说:“这是件大好事,他们该有那么个结果。”有好几天,他们全家都为此事兴奋不已。老人又重新提笔,写下了4首诗。
其二
蓦地春雷震八方,兆民歌颂党中央。长安街上喧锣鼓,欢呼日月又重光。(1976年10月)
十月春雷
白骨成精善变化,人妖莫辨乱真假,乔妆巧扮自吹嘘,笑脸狞眉藏诡诈。因缘时会忽登龙,身价已非旧阿蒙,自封左派鼓簧舌,妄图只手蔽天聪。画皮未剥多威武,闷棍毙人胜刀斧;翻新帽子满天飞,喜怒随心谁敢迕?挑起武斗制分裂,破坏生产手段辣;迫害总理图夺权,人人切齿曰可杀!十月春雷布昭苏,剥落画皮验真身;万众欢呼天又晴,彻夜锣鼓庆新生。(1976年12月底)
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老人喜悦的心情。从30年代以来,他对江青的行迹及其后来的所作所为,是相当了解的,特别是对她在文革中的丑恶表演,她给广大文艺工作者带来的灾难,也是深恶痛绝的。正因为如此,“四人帮”一垮台,他立即打破长期的沉默,写下了一些辛辣讽刺江青的丑恶行径的诗篇。如果把这些相当直白的诗篇,同几个月前写的《八十自述》相比,前者的那种沉重、压抑的心情已一扫而光。
三.回忆录写作的点点滴滴
结束了十年浩劫的动乱岁月,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是年迈多病的茅盾,仿佛又注入新的血液。生命之火、希望之火重新在老人心中燃烧。他又振奋起精神,为业已凋零沉寂的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复兴与发展,重新提笔写作。国内外的广大读者,又开始听到这位沉默了十余年的文坛巨擘的声音。他在生命的最后4年多时光里,再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
茅盾在晚年发表的文章、讲话及重新出版的十多种著作中,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一部最重要的著作。那是他倾注最后几年心血精心撰写而成的。
为了写好回忆录,茅盾耗费大量心血,查阅了大量旧报刊与有关材料,也曾向亲朋故旧查询故人故事。回忆录前头的许多部分,茅盾后来又重新写过,有些章节也是重新整理、充实、改写的。为了做好这一工作,他曾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先是让儿媳陈小曼协助搜集、查借各种资料,后来改为由儿子韦韬提前离休,专门给他当助手,使得老人得以集中精力撰写回忆录。
1978年8月16日,陈小曼代茅盾去信让南京大学教授叶子铭为其借阅他的第一部翻译作品《衣》、《食》、《住》的旧版本,并表示如果能借阅的话,“保证不损坏,用完立即挂号奉还”。收到书后,茅盾将它同上海购得的新版进行比较,并于9月29日亲自给叶子铭写信,就他正在进行的回忆录写作之难处,讲了一大段话:
近来我收集旧作,因为要写回忆录。此事难在不看从前的文章,则有些事难以核实。而从一九一八起至一九二O年,我在上海各报副刊及商务各杂志发表文章之多出我记忆及者数倍之多。这个回忆从我的家庭,外祖父、母,母亲、父亲等写起,然后是学校教育,然后是职业生活。现在先发表的是商务编译所内部发行之《新文学资料》,年内出版。一些大专院校近来搞一些茅盾著作年表等,错误很多。皆因他们未查得原件,只知篇名之故。对于我的家庭及其他活动也有以耳代目之病。
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不已!为了查实叶子铭提到的那份材料中所提到的人和事,茅盾十分认真地约请一些当年的老同志帮助回忆。他在1979年9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
下午三时半罗章龙来谈,此盖我预约他,有些事,(关于一九三三年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的记录中有些人的情况)要请教他。他谈了些当时的情况(例如张国焘在办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时用了特立这个名字),并谓解放后他先在湖南大学任教,后到武汉大学。后来我将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的记录抄本(原件存上海档案馆,此为叶子铭抄来的)给他带回去,慢慢思索其中一些人名的情况。
1978年7月16日,叶子铭去拜访茅盾,得知他为写回忆录需搜集各种资料,便告之自己手头除有一些高校与图书馆编印的茅盾著作及研究资料目录外,还保存一份1962年的访问记录稿的抄件,其中有许多茅盾的朋辈与战友谈到他过去的文学活动与社会活动的情况。茅盾听后很高兴,当即表示希望叶子铭寄给他看看。
在《〈我走过的道路〉序》里,茅盾曾说过:“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搜集,务求无有遗珠。”对回忆录的材料,他全是采取这样的态度。这里不妨举个例子。根据茅盾本人和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张国焘,以及许多老同志的回忆,茅盾曾参加党的“一大”前成立的上海共产党小组,是确定无疑的事。然而,关于参加的时间以及这一组织的名称,由于年代久远,加以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说法不一,一时很难作准确的判断。1962年l0月间,茅盾就此事说:“1920年上海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我也参加了。记得是李达先跟我讲的,我同意了。……记得最早的成员有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杨明斋(懂俄文,开会时也当翻译。当时开会第三国际都有人参加),还有邵力子和我。”文革后,茅盾写到这段经历时,把时间又推后至1921年初。他在最初发表的《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上)里,说他“是在一九二一年二三月间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这一改动,主要是根据一些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特别是根据包惠僧的回忆推断的。包在1962年11月6日的谈话中说:“雁冰正式入党是在一九二一年一二月间,与邵力子同时。当时,陈独秀已去广州,是由李汉俊在上海负责。我和他初次见面是在李汉俊家里开支部会时。”这里所说的正式入党,即指“一大”前的上海共产党小组。大约包惠僧是党的“一大”代表之一,比较熟悉建党初期的情况,所以茅盾觉得他的回忆比较可靠,就据以更正。不过,对所说的时间,他又稍作更动,推迟至二三月间,其中大约另有根据。
后来,在1981年10月正式出版的《我走过的道路》(上)里,他又根据有关的史料追忆,把这个小组的名称和自己参加的时间,再次作了改动,说他是“一九二○年十月间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党小组”的。这主要是根据如下史实推断更改的:1920年底,上海共产党小组筹办了第一个党刊《共产党》。应主编李达之约,茅盾在该刊第二号上,发表了署名“P·生”的4篇译文,即《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世界工业劳动者同盟的简称)的恳请》、《美国共产党宣言》等。当时,该刊属党内秘密刊物,凡在上面发表文章的人,大多是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成员。这一期刊物出版于1920年12月7日,从茅盾应约为其译稿到正式出版的时间看,他推断参加小组的时间约在1920年l0月间。此外,据茅盾的反复回忆,他虽然不是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最早发起人,却是小组成立后被最先发展的成员之一。他的这一说法,也确实是有根据的。据张国焘的回忆,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于1920年8月成立前,他听陈独秀说过,除最初的7个发起人外,“预计沈雁冰、俞秀松等人也会很快参加。”张国焘还推断:“沈雁冰、俞秀松等人的参加,……都是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的事。”从以上两点看,包惠僧凭个人回忆的说法,并不是很准确的,茅盾根据上述情况又重新把参加的时间改为1920年10月间,虽也属推算,但应该说是比较接近史实的。至于小组的名称,过去他曾称之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马克思主义小组,后来则是根据国内党史研究的有关资料,把它改称为上海共产党小组。
茅盾对自己早年参加共产党小组的时间这一细节问题不断地进行查核、修改,不是没有道理的。早在党的“一大”以前,他就公开发表文章,明确表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向往与信仰。例如,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发表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一文里,就高度评价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预言“二十世纪后数十年之局面,将受其影响,听其支配”。1921年1月,在《家庭改制的研究》一文里,他则明确宣告:“我先欲声明一句话,我是相信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家庭的话,远如恩格尔(按:即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中所论,近如伯伯尔(按:即倍倍尔)的《社会主义下妇人》所论,我觉得他们不论在理想方面在事实方面都是极不错的(尤佩服他们考史的精深),所以我是主张照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法去解决中国的家庭问题。”这两篇文章写于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前后,对于我们从思想信仰上印证茅盾很早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可以说也是一个重要依据。
茅盾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对自己或他人的回忆,都不是轻易地据以下笔,而是要反复地查阅大量的资料,力求准确或比较接近历史事实,方感心安。虽然,1976年他搞过一套口述录音,但由于他对自己采取了一种近乎苛求的态度,所以从1978年起至1981年3月27日他逝世前,尽管前后花了3年多的时间,他的回忆录写作计划也才只完成了一半。
那么,茅盾亲自撰写的回忆录,究竟写到哪一年;余下的部分,又是由谁根据什么材料续写下去的呢?
《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一期在刊登茅盾的《回忆录》第十八节《一九三五年记事》时,有编者按:“茅盾同志的回忆录,其亲笔撰写部分已经登完;自本期起续载的,是其亲属根据茅盾同志生前的录音、谈话、笔记以及其他材料整理的。”就是说,茅盾亲笔只写到1934年为止,其最后部分,即刊登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四期上的《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这一节回忆录篇末署明的写作时间,是“1981年2月8日”。
据后来韦韬夫妇披露,茅盾住院前两天还在写回忆录。茅盾是1981年2月20日住进北京医院的。他于2月18日还写了关于《虹》的部分,这是又回过头来补叙《虹》的创作情况的,大约插进《亡命生活》一节里。当年他给郑振铎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他写完《虹》后还拟写《霞》。2月18日,茅盾赶写《虹》的回忆部分,他感到比较累。19日就有低烧,休息了一天。亲属劝他住院治疗,他不肯。第二天,精神更不好, 他才说:“看来我得住院了。”这样, 2月20日他就进了北京医院。
这就是说,茅盾亲笔撰写的回忆录,最后写的不是《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而是回头补写了当年写完《虹》之后曾拟写新的长篇《霞》的情况。这最后补写的几页文字,后来就插入《亡命生活》一节里,刊于1981年《新文学史料》第二期上。其内容,主要是依据当年他给郑振铎的信,追忆《虹》的命意及《霞》的创作构思。被郑振铎摘录发表的信,刊载于《小说月报》第二卷第五号(1929年5月l0日)的《最后一页》上。其中有一段话,唤起了老人对昔年在日本京都创作《虹》时新的艺术构思的追忆:
《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以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一座桥。《虹》又常见于傍晚,是黑夜前的幻美,然而易散;虹有迷人的魅力,然而本身是虚空的幻想。这些便是《虹》的命意:一个象征主义的题目。从这点,你尚可以想见《虹》在题材上,在思想上,都是“三部曲”以后将转移到新方向的过渡;所谓新方向,便是那凝思甚久而终于不敢贸然下笔的《霞》。”
茅盾临终之前,依据上引的这段文字,抱病补写的关于《虹》及其姐妹篇《霞》的一段回忆,成了他留给世人的最后文字。在国内外的读者中,包括茅盾研究者在内,都不知这位著作等身的一代文学大师,曾想继《虹》之后再写一部新的长篇《霞》;即使有知情者,也只知道他有过这么一个计划而已。所以,他留下的这一段最后的回忆,是十分珍贵的。令人无限叹息的是,当他写完这段久藏于心底的回忆之后,就带着衰弱的病体与霞一般的期望住进了医院,一个多月后与世长辞了。
茅盾逝世之后,他那未曾写完的回忆录,由韦韬根据父亲的口述录音,以及他们长年累月为回忆录所进行的对答谈话,包括茅盾所留下的札记、素材和大量书刊资料,加以整理、续写。
(选自《文史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