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汀的诗
正午的阳光背叛了我
正午的阳光背叛了我,
根据一份多年前的契约。
风筝飘在空中,
好似一件白色背心。
一个幼时见过的疯子
重新出现,他将穿上那衣服。
继续飘荡,在杉树之上,
在那里俯视我们乡间:
一片歪歪斜斜的房屋,
它们啜饮湖边的雾气。
它们在发黄,脱落了表皮,
它们不再适于居住。
它们渐渐听到称赞:
这是期盼中的那件事。
我们,在观看中被选中,
一切已经无法停止。
他在预料中出现,提着灯笼
在村子里走家串户。
将有一座房子是空着的,
他将明白那就是家。
丢弃了灯笼,入睡,
而阳光在天窗里摇晃,时值正午。
他将梦见自己被大水围困,
徒劳地站在唯一的屋顶上。
一 月
星期天到了,苍白而疏软,
像一张蘸着水迹的包裹单。
想到这一点,我望向窗外,
雨终于停了。
尘土的气息包裹着房屋,
仿佛冬日的外壳。
我去邮政局取书,
布谷鸟嘶吼。
厅堂里空无一人,
只有油漆的干燥。
我向它内部走去,
穿过狭长的走廊。
院子里满是积水,
邮车将要出发。
偶然地,我置身于此,
听着小贩摇晃的铃声。
我们离开城市,驶向南方,
大道上满是光亮。
后来,汽车停下来,
我也就从旅程中退出,走下公路。
现实被反复踩过,
草梗在边缘酣睡。
我注视近处的房舍,
那屋顶好像羽毛。
我瞩目山丘上的农田,
它们倦怠和安静。
诗在那儿显现,
是那分行的形式让我着迷。
验 证
真理在时间中变化着。
傍晚七点,它如同一摊淤泥。
从那里,我握住了某个女人的脚踝。
那么,你踩着那些淤泥,踩着那些伦理?
你只是作了一次散步,
恰好看到了草丛里幽暗的阶灯。
你记起一座小镇,想起那里的郊外。
天色好像经验,好像必然,
好像纯粹物质的过剩。
你摆脱我,像写尽一行文字。
你真的已经身处那里,
四周都是验证性的草堆。
直觉变得坚硬,可被手触摸,
如同典籍和梦境,
如一盏黄灯的执念。
然后,我们欠缺一个转折。
在那个瞬间,你想起我的虚妄,
那并非索然无味的本质。
给某位不相识的隐士
多年来我一直保持沉默,
唯独喜欢注视窗边的花饰。
毛边玻璃仿佛纸页的折痕,
我使用它来标记生活。
但它却变得困难,
在普通的夜晚,我没有睡着。
我羡慕那个醉醺醺的酒鬼,
他反复擦拭那盏路灯。
我坐在桌前,反复地臆想他,
我确信那绝不是一个幻影。
凌晨的马路在丁当作响,
它召唤我投入怀抱;任何一个怀抱。
我迈着儿童的步子,
假装醉醺醺的,开始敲打
街边的第一扇门。这就是那个不真实的时刻,
我看见的只是个愤怒的睡眼惺忪的男人。
我礼貌地道歉。白昼像油滴一般凝聚。
一个颓丧、贫乏的中年男人,从后面追过来,
当他的身影渐渐盖过我的,
我感到一阵不再复返的战栗。
在候车亭下
在候车亭下,我睁开眼睛。
我触到了那荫庇,
一个小小的顶棚。
它是我的限度。
向你呼唤,——我所来自的
——那个传统。
雨点落在我们的外部,
像敲打一只古代的瓷器。
这器具值得赞美,
而渴慕正在来临。
双手轻轻抚摸,在底部,
我感到一个十字的裂纹。
我不知道,
在它身上曾有怎样的震颤。
早上,世界已经存在很久了
早上,世界已经存在很久了:
从一个黑暗的房间醒来,起身,
——我莫名地意识到这一点。
没有洗漱,我开始走动。
汽车的声音在墙外轰鸣,
壁龛上佛像的脸色我看不清。
木门的把手发凉。
不知何时我穿上了拖鞋。
邻近的房间,红色的蜡烛没有熄灭。
一个宽绰的仓库在等着我,
堆积着我未结识的物品。辨认标签后,
我明白,自己偶然地占有了它们。
喑哑的冰箱旁边,我触到一个拉索——
卷帘门慢慢升起——这时我记起,
我是一个年轻的商店店主。
出门之前,我注视天花板,
那个简易的吊灯,我愿称之为室内的星辰。
我努力想要记得,我们这儿是否曾有过露天的时代。
愉悦感离我而去
愉悦感离我而去,
像随口呼出的一阵热气。
它游荡,从林木间穿过,
裁出一道微薄的裂纹。
这足以打扰别人的睡眠,
有人已经起身,从床上坐起。
仿佛他开始饮水,但在我们这儿,
渴意还没有消褪。
我无法毫无征兆地唱歌,
我已经认识这条道路。
整个街区都在烧煤,
气息在黄昏中摇匀。
但我终于看到了它,
一枚肝脏般的月亮,正在升起。
它像一件已丧失的物品,
偶然地,在栾树下被赎回。
争吵已经结束
争吵已经结束,
但船仍在颠簸。
一些夜晚的火光被我记起,
它们究竟来自哪里?
但是凉风吹来,
这是时间的凉风。
我已无法向你说明什么,
既然呆在船舱的底层。
已经就要到达对岸,
我为什么发出叹息?
我将打开窗子,眼见海藻
缚住了指针。
在某个大厅里,世界发白。
我已找不到你的位置。
卡珊德拉,请告诉我,
船儿的颠簸真会遣散一对夫妇?
一个迷雾散去的清晨,
我正辨别出神庙的倒影。
(请不要擦拭我们,
这些宇宙的尘埃。)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来自书本,
桌上传来振动,那是你的手机。
或许我在啜饮明亮的红茶,
而特洛亚人的船桨搅起了泡沫。
漠然在生长
漠然在生长,像院落里遍地的苔藓。
我曾在家乡经历这种天气。
整个二月都这么阴沉,
当着祖父家中的木窗。
你擦拭窗台了吗?
杂物一件一件地复现。
它们不信任身上的灰尘,
尽管后者已经游历了世界。
时间轻微地腾出位子。
没有人死时会穷困得身后一无所有。
也不愿听到任何声响,但在黄昏,
村子里逐渐传来嘈杂的音乐。
我想象那是一场祭祖的尾声,
人们开始走动,踩在那漠然之上。
我想要出门。一场雨开始坠下,
可是在家里,没有适合我穿的木屐。
他已经认识了冬季
他已经认识了冬季,
认识了火车经过的那片干枯原野。
城市在封闭,运河上有一片绿色的云。
进入黑暗的房间,像梨块在罐头中睡眠。
他的体内同样如此,孤立而斑驳,
不再留存任何见解。
可是旅行在梦中复现。在夜间,
他再次经过大桥,看见那只发光的塔。
它恰好带来慰藉的信息。
缓慢地移动身子,他做出转向,
在这样的中途,他开始观察
来自邻人的光。
家 乡
我依赖于自己的家乡,
那已从身上脱落的东西。
那些老年作家,他们不得不在昏暗中摸索。
但傍晚呈现绿色。
他们的智慧在下沉,像糖落入水中,
我们一同踩在柔软的底部。
仿佛我们被玻璃器皿包围。
村庄吐露几缕炊烟,虚弱地抵达顶部。
就这样回馈对等的经验。
将有一个人,如赴约一般到来,
提着童年的灯笼,在田野的雾气里
捕捉敏锐的死亡。
复 原
谈话的时候
轮回在发生。
我保持了足够的警惕。
但是一小块瓷片坠落,落在这个餐桌上。
祖父曾告诉我旧事。他追忆他的岳父岳母,
两人坐在餐桌另一端,带着粉末性质的音容笑貌。
某位考古学家洞悉这一切。
他复原出整个瓷器,轻轻握住那只微妙的柄。
他让六十年后的我坐在你父母面前,
想起祖父的那些回忆。
想象一队列的我坐在这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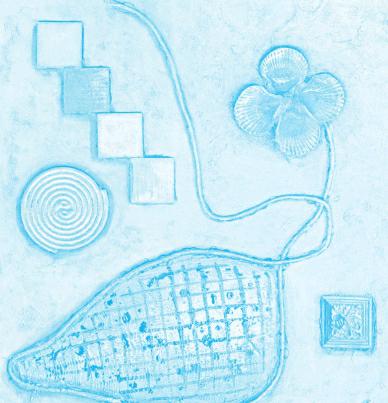
一同喃喃自语:是的,我早就认识他们两位。
我熟悉这个小区的老人
我熟悉这个小区的老人,如阅读自己的忧虑。
我每日查看,并记住他们,
不经意间,像幼时做过的众多次练习。
有时,一阵陌生的香气从天上坠落,
进入笔记簿上的确定一页。
而我恰好从城里回来。
呼吸伴随电梯缆绳的摩擦声。
忧虑跟着我回到这一层。
雾气进入了走廊,像墨汁被稀释。
像毛衣包裹着我们,你很难说出那种不适。
他们有他们的真实。
他们涌来擦拭玻璃。外面灯火通明。
一个被训练过的黄昏,进入我们的语音。
我和那么多的幽灵们互相辨认。
城市蒙上了灰尘,如白色雕塑,废弃在童年画册里。
你是我冬日认识的事物
你是我冬日认识的事物。
但这也意味着某种告诫。
我看着你,从一场聚会上离席,
尽管街上刮起强烈的风。
而你认识那么多的巷子。
它们中间,苍白的积水在结冰。
你明白,一切无可避免地成为现时,
时代的路边尽是店铺和灯笼。
那么多的梧桐和杉树在震颤,
一个小时的折痕经过我们,
某个秘密已经向你呈现。
远处灯火通明:你将动身回返。
我感到身体衰弱,天空低垂,
并且看见一颗晦暗的星。
悲 伤
我在这条街的骨髓中旅行,
每日领受一份它的寒冷。
修路工人们正在忙碌,
铺下这一年度的沥青。
但初春傍晚的红晕
正离我而去,
仅仅留下模糊的预感。
在其他场合重复呈现。
雾气堆积在地铁入口,
像受伤的动物在蜷缩。
车厢里,人们的脸部如此之近,
他们随时能够辨认对方。
以漠然,以低垂的眼。
长久、缓慢地储存在这区域。
肃穆地等待被人再次发现,
在背包中,在城市的夹层。
摘下各种式样的帽子、围巾,
意识残留在绒布上。
我们惯习于这些形式,
在一阵大风吹来之前。
没有携带随身物品
也不借助任何比喻,
从它们那里逐级堕落,
或艰难地提升。
后来,一个女孩涂抹护手霜,
气息向四周扩散。
间或有灯光灭去,
印象暂时地消逝片刻。
继续擦拭这些秩序,
这抽象的生活,这些轰鸣。
一个老人,从口袋里掏出眼镜,
观察这些陌生人。
而多余的眼睛,先于我们而在。
沉默无言的生活
与诗歌无关;
心灵像晚餐一般成熟。
幻想中的店铺悉数敞开。
因和果同时陈列。
因和果纠缠在一起
好像死人无法分开的手指。
我们跟着钟表在世上漫游。
想想勃鲁盖尔的那群盲人。
我们对空虚做出
日和夜的姿态。
但困顿将保护自己,
我要重新收集那些忧虑。
它们分散了,像面包的碎屑。
我听到外面的洒水车之声。
很快这条街将被浸润,
像钉子嵌入木板,
像浅显易懂的教诲
在一颗心脏凹陷的地方。
几十年的忧愁
悬在空中,
瞪着这个时代。
惟有它看见我们的重影。
我想追随任意一个邻人
回到他的家中,
直到他确证自己
沉入某种重复过的睡梦。
但星斗们还停滞在那里
像狗群游荡在夜间的车库,
他们向我们抛掷杂物。
因为白色的智慧无家可归。
【作者简介】江汀,安徽望江人,1986年12月出生,毕业于青岛理工大学,现居北京。著有诗集《来自邻人的光》和《寒冷的时刻》,曾参与发起北京青年诗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