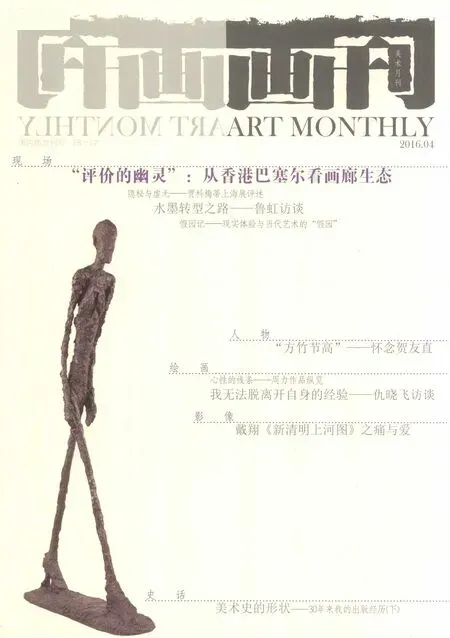我无法脱离开自身的经验
——仇晓飞访谈
本 刊
我无法脱离开自身的经验
——仇晓飞访谈
本 刊
《画刊》: 我看了你这次纽约新个展“双摆”的作品后,有一种感觉,这是你目前为止最为开阔自由的一批东西。你以前说,所有的东西都要有一个边界,你的绘画关注的是无限中的有限空间。我倒是觉得你新个展的东西,比如《乱体系(近景)》《乱体系(远景)》,展现的空间非常开阔,从画面上看,不再强调对空间和界限的控制力。这好像也是延续了“南柯解酲”的绘画思考。
仇晓飞:绘画的边界的问题一直是存在的,我觉得绘画不是一个单纯的画面内的东西;绘画是由它的边框所挤压的这个空间,然后绘画内部虚构的空间,还有悬挂画的展示空间三个空间的交错所产生的一个东西。
画的边界对我来讲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一直思考的东西,同时它也有一些引申的意义,比如说西方古代的时候画挂在教堂里边,它的边界是和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界有关系的,还有中国古代的壁画也和这种现实的边界以及一种精神理念上的边界有关系。今天看似乎绘画没有外面的边界,其实这个边界一直是存在的,一直不断地在被思考和改变。
《乱体系》这组画,“近景”和“远景”之间的关系用了一种像蒙太奇、像镜头推进一样的一种视角的变换,实际上两个视角的变化都是和空间的推进有关系,也是和它四个边缘空间的受限相关。也就是说当镜头推进的时候,四周的空间是不断被画框的边缘切割掉的。在两个视角的变化中,我保留了它们的相似性,也置换了很多内容,从红色的塑像到橘黄色的人形,还有环形建筑和螺旋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开阔和收缩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有形而上的绘画形式上的意义;另外一方面也有社会学的意义。

《乱体系(近景)》 仇晓飞 布面丙烯 207cm×336cm 2015年

……………………
《画刊》:在布展的时候,你对每张作品的悬挂或放置顺序是不是都有明确的设计?
仇晓飞:我的展览在布展之前都会有一个事先的设计,但是不排除进场之后会有调整,有的时候调整甚至会很大。其实是一种引导,有的时候我也不会把展览安排得非常合理,这种“合理”包括作品的顺序、整个的思路,因为在创作的过程里很多时候都是矛盾的,所以展览所呈现的应该也是一个矛盾,我觉得不是一种被理清楚的东西。展览的布展是一种理性的安排,但是这种“理性的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呈现思维上的矛盾性和思维本身所有的混乱无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
《画刊》:从你10来年的作品变化来看,就绘画而言,你的绘画风格不仅越来越抽象,画面结构也越来越复杂。你自己如何阐释这种转变?仇晓飞:我不太按照抽象和具象这种区分来分配绘画,因为抽象和具象谈论的都是从视觉形式的角度去入手区分绘画的风格,但是今天已经不是一个视觉形式的时代了,我在绘画背后的一些想法、概念,以及驱使我去跳跃性地选择某一种形式的东西,这些变得更重要了。
我的作品一直是跟时间的概念有关系,和时间的进程里面所呈现的绘画的一种功能性有关系的。差不多在十几年前,我的第一批作品、第一个展览都是跟记忆有关系的。随着我对时间结构不断地认识,发现记忆不仅仅是停留在过去的被不断回忆的一个时间点,而是处于一种螺旋形的结构中,它每时每刻都在重复出现。可能随着我对时间结构的认识不断地更新和变化,这种绘画的结构也越来越复杂。
……………………
《画刊》:《云雾》看起来是你这次个展上最内敛和诗意的作品,它呈现的氤氲和水汽,那种蒙蒙眬眬的质感和在场其他作品反差很大。
仇晓飞:我按照一种相对愉悦的比例去划分了这张画。先竖着划分了硬边的七条竖线,考虑了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长短关系,包括间隔关系。然后用大面积的水性的颜色喷涂、渲染去破坏了这几条竖线,把它们破坏掉以后,等画面差不多干燥了,又重新把这几条线提了出来,就是在破和立两者之间不断地反复。
这张画是在两极之间不断往复的状态中产生的。七条竖线提示我需要一种特别无序、柔软的这种雾气的方式,这种无序的方式和线的这种理性,以及它的这种结构之间有一个对抗。从空间结构来说,长度不一的垂直的竖线会跟画面的边缘产生关系,而这张画雾气的部分是与整体空间的空气感相关的。所以我在考虑两种东西:一方面,当绘画悬挂在一个空间里,它的结构的部分是和房间的结构,我们今天所居住的环境的结构,包括人所熟悉的空间性的结构有关系的;另一方面,所有画面里的内容,关于空间的部分、关于空气感的部分又是一种无形的填充物。

仇晓飞

《零重力 1》 仇晓飞 布面丙烯 300cm×200cm 2015年
……………………
《画刊》:这是你对绘画空间的理解。
仇晓飞:我是始终在二维的平面上去创造一个三维空间,如果加上时间的概念,场景的切换、推进,这就是一个多维空间了,这是我工作进行的基础。所以我在思考的一个事就是绘画里面的空间,它和绘画外边的空间,比如说展示它的空间、我们生存的空间,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一块煤当它燃烧,烧尽之后,煤的能量转换成一个热能,但是它被烧尽的煤渣剩下的东西是一种无序状态,而能量的转换是有序的,在物理学里边,能量和能量之间的转换必然是一种秩序性的这个进程,而所被废弃的部分是一个无序的状态。画画的时候我也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绘画所纠结的部分、所呈现的那个部分,一定是不能够被正常转换的部分,比如说我的情绪变化的过程里面,比如说在现实的理性里边无法被彻底排解掉的部分,都会凝结在我的心里,逐渐地形成绘画,在一种无序的、混乱的状态里,废弃的部分和升华的部分是一样的,这些不能被正常地转换的部分,我觉得是绘画的能量。
从我1977年出生到今天,我生活的这个社会已经变化得太大、太快了。因为这个社会不断地在进程中,不断地在转换,我们不断地接触这种被废弃掉的东西,所有这些被废弃掉的东西最开始是记忆,后来慢慢地变成我对人的精神和心理的兴趣,正是不断地对废弃物的转换,凝结成这些绘画。
……………………
《画刊》:思考和观念驱使你进行形式的选择,那么在你的作品里,可以将由此引发的形式和结构的变化理解为你在艺术现场呈现自己思维的线路和思考的深度。也就是说,观看和解读你的作品,需要避开常规的审美系统?
仇晓飞:我觉得绘画不是单纯由思考和观念所引发的,它本身也在生成思考。我经常在完全不清楚自己在画什么的前提下开始作一张画。不是我想好一个主题,想好一个什么东西,用绘画去呈现它,它是在画的过程里边不断地被发现的。
我也不是从审美的系统来开始这个工作的,但是我的作品里边并不排斥审美,因为最终绘画是落实在形式上的,不是在其他的地方,但是美不是一种既定的程式,所以美是在不断的实验和过程里边产生出来的。理解作品最终还是会从审美的角度去介入的,我在看所有的视觉艺术作品的时候,无论它是空无一物的,还是视觉强度、信息特别大的,它都是由一种视觉的感官直接刺激到我,来产生下一步的探寻的,不是由其他的东西,不是一种说教。
……………………
《画刊》:哪些画家的创作对你有比较大的影响?
仇晓飞:对我有影响的画家可能太多了,但是可能说影响就已经不准确了,因为我觉得今天是一个信息交互的时代,面对非常的庞杂和凌乱的信息,对于我来讲其实有一点点像音乐家在用旋律采样一样,我把过去艺术史中某一个阶段,某一种意识形态下所产生的艺术的形式、绘画的形式,把它们打乱、切碎,然后重新去组合,也可以理解为从历史的风格的切片中去采样,然后使用它们之间不同的张力关系,去构造新的东西。

《自游浮木 A》 仇晓飞 布面丙烯 300cm×200cm 2014年
前几天我在看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一个画家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 ,1415-1492年)的画册,我发现他的绘画里面的构图的方式、透视的方式是平行展开的,跟中国的宋画有相近的地方。他经常使用散点的透视来展开一种结构的构造,所以这里边有点儿背离今天的我们是以图像的方式来展开构图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我就找到了他绘画的一些理论,但是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的绘画理论却跟我所想的、所看到的东西完全相反,他极力地在强调科学的焦点透视法的重要性。他的画是从中世纪慢慢演变过来的,就是说在他之前很多东西都是一种平面化处理的方式,散点的、非焦点透视的,对于他来讲极度的有一种渴望是通过他的这种不断的努力,可能他的努力加上他下一辈所有西方艺术家一辈一辈不断地努力,最终促成了照相术,包括今天我们所习惯的这种视觉形式的产生。
今天对于我来讲,呈现一个视觉的深度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固态的对于这个世界的视觉思维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无趣。我从弗朗西斯卡身上看到了他没有被进化掉的那一部分,反而是变成了我觉得有趣的部分,但这好像是历史的车轮一样,是一种螺旋形的结构,像一个弹簧一样,在他那一环的时候他正朝向前的方向在旋转,但是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一圈,又好像从科学的,从逻辑的、深度的视觉这样一种角度转回到一种原始性的结构。当然,时代不一样,进程也不一样,但是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所以我在观看其他的艺术家、艺术史的时候,有时候带着很多的误读。
……………………
《画刊》:《女盗》这件作品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民国绘画对西方神话题材的东方式改写。我以为这件作品很有魅力,带有神秘主义的气质。能谈谈这件作品吗?
仇晓飞:是这么回事。右上角一个女的拎着一个男的头,它的构图来自于民国时候一个不太知名的画家画的一张画,我在一个很旧的旧杂志上看到了这张画,挺有意思的。有一部分民国的画家都对西方的那种神话题材感兴趣,这跟这种宗教的传入进来都有一些关系。所以在他们是一种前卫的方式,一种比较激进的方式去接受这样一种东西,同时对中国的问题进行提问或者是改造。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苏派的苏联式的左翼文化进入到中国,这种从法国、意大利来的这种左翼文化的运动就悄悄地被改变了,在这个历史的进程里边被另外一种东西替换掉了,因为苏联的文艺基础不是一种前卫的、激进的方式,美学上讲它的基础是一种沙龙文化,比如说写实的、具象的、非常缺少神秘感的、现实的,然后去替换了这种原来的前卫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历史的进程很有意思。在今天,因为我们都是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艺术的教育里边成长起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的绘画都是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思维模式的一种反思,当然我不是说排斥它,我是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进程里边去想。比如一些很有意思的神秘性的东西,因为它模糊了一些界限,东方、西方,二元论的一些界限,包括神话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它模糊了很多的界限,所以我觉得它带有某种神秘性,我愿意去续写这种神秘性,把它变成一个跟今天有关的东西。
……………………

《女盗》 仇晓飞 木板、亚麻布、丙烯及油画、旧白瓷挂钩、塑料网兜、木球 25cm×35cm 23cm×33cm 30cm×40cm 50cm×33cm 60cm×40cm 15cm×47cm×8cm 2013-2015年

《云雾》 仇晓飞 布面丙烯 250cm×300cm 2015年
注:本文录音初稿由北京恒信雅达会议服务有限公司整理
展览名称:仇晓飞:双摆
展览时间:2016年3月11日-4月23日
展览地点:纽约佩斯画廊
《画刊》:你对整张画结构的确立,是在不断地深入和绘制过程中逐渐清晰的,还是说一开始就基本明确了结构的基调。我强调的是结构,而不是绘制过程中遭遇的偶然性。
仇晓飞:2010年,我在做“登楼已去梯”那个展览的时候,那些画的结构都是在画之前就已经确立下来的。
从那之后,我越来越想放弃事前确立结构的方法,而是想让一张画的结构也在即兴的过程里面去完成、去呈现。在纽约的这次展览,包括上一个展览就是“南柯解酲”里边的即兴的那一部分,都是在画之前没有事先预设结构的。
……………………
《画刊》:你的绘画看起来越来越走向即兴和强调直觉,你的近作相较以往的作品都自由了许多,似乎也越来越摆脱你自己的叙事传统。这个阶段的绘画,你个人最满足的经验是什么?
仇晓飞:我觉得唯一有一点,我不是在摆脱一种叙事传统,我是在摆脱一种惯常视觉逻辑中的叙事传统。我还是想让画变得更直观,就是在结构、逻辑构造里面就能让人感觉到某些东西。我是通过一种形状、结构、颜色、痕迹、形象这些东西的组织去展现一种叙事性,而不是通过像那种写作文学性的去强调叙事性。但是我始终觉得我的作品不是一种视觉抽象化的,不是那样一种东西,从单纯的美感入手的。我最感兴趣的经验就是绘画的过程成为一种不断发现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不断呈现的过程。这两点我觉得是有区别的,因为在发现的过程里边绘画始终在摆脱它作为一种工具的角色,而是成为一种不断发现的前提,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事。逐渐不断地成为前提,而不是成为结果,这个我觉得是有意思的事。
……………………
《画刊》:在“双摆”这个展览里呈现的作品,你觉得哪一张是最能代表你目前创作状态和思考方向的?
仇晓飞:最和这个主题相关的是《乱体系》的“远景”和“近景”,这两张画它是一个关联性的绘画,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和“双摆”的想法最贴近的。
还有一张画叫《环蛇》,可能这张画也挺有意思。蛇的形象最早在我画面里出现的时候是一种螺旋形的图案,慢慢地、逐渐地随着我的想象变成了一个蛇的身体。在这次展览里边这个蛇的身体又变成了一个人形的形状,它回头在看自己的尾部,可能跟我对于时间结构的这种不断更新的认识有关系,所以它变成了一种隐喻吧。一个图案衍生成形象,然后在这个形象上边不断地去推进,这可能也是我的一个方向。
……………………
《画刊》: 你在一次采访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最感兴趣的是有限心理的可能性。”那么对你来说,当画笔接触画布开始,每一张画是否都意味着在此时此刻的内心体验里发现绘画表达的可能?
仇晓飞:在绘画的进程里边不断去发现这个绘画的结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是会更多地触及自己心理的有限性。因为在画画的过程中可能性总是开放的,所以这张画的一个边界或者是它的一种倾向就和一种心理的状态非常相关。像在一个进程的状态里边去展开一个心理分析,但是当然自己给自己做心理分析这个是不可行的,因为你始终是会回避开潜意识里边最隐秘的一点,但是这种不断发现的进程确实是会推进这个事情。就像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像刚才举例的《环蛇》这个画,从最开始这个蛇形形成的时候,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作为人形的那一面,就是它作为一个身体可以蜷曲的形状所给我的这个暗示,但是随着慢慢地画它确实在这个里边出现,当然这个形象可能也不仅仅来自于结构,可能也跟我记忆中的某种东西有关系。
……………………《画刊》: 你心中理想的绘画是什么样的?
仇晓飞:我无法脱离开自身的经验,就像我的绘画的根源来自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思维方式,但是我朝向的方向却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方向,完全另外的方向。就像人的来源和他的理想之间的一种矛盾一样,这两者之间拉得越开,它形成的张力越大,可能我所向往的绘画就是充满这样一种张力的绘画吧,应该是这样。有时候经验、记忆就像是一张弓的一个弓弦,所有的知识来源,所有朝向的方向、你想去的方向,包括自由这种东西都是一种像弓背一样,这两者之间拉到很满的时候是一种很危险的境地。因为拉得太猛就会折断,如果拉不开就会没有什么力量,所以我觉得我向往的那种状态是拉得很满的一种状态,当然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但无论对于个人的心理来讲,还是对于艺术的形式来讲,它都应该是一种处在危险之中的状态。

《环蛇2 》 仇晓飞 布面丙烯 180cm×180cm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