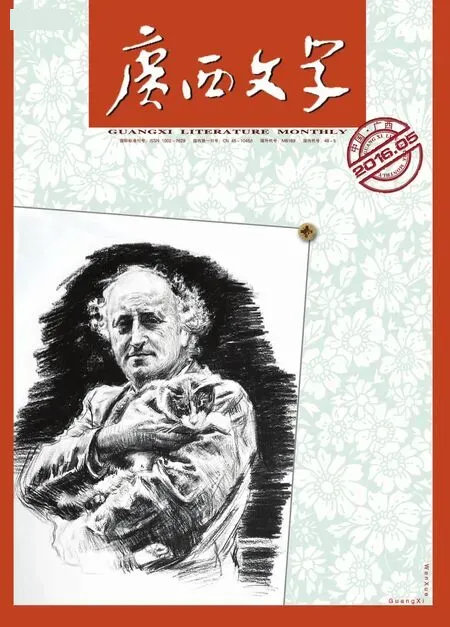湘西:山水褶皱里的人生
田 耳/著
都罗寨
想在湘西过上好日子并不容易,七山两水一分田,土质还贫瘠。再说,太多聪明人,挤在这一片山水褶皱之中。比如都罗寨,我爷爷在那活一辈子,父亲拼命从中奔出来。那地方山高水低,年年有旱,在我看来几乎不宜人居,但居然生存了千把人。父亲谈到老家,“竟有两百多笔烟子”。两百多人户,是大村寨,父亲不无得意。
我大专毕业没有工作,社会上瞎混了不少年头,心情也不免失落。父亲要给我找个榜样,时时给我鼓励,就介绍通献给我认识。通献也是都罗寨人,初中毕业就进城混事,不到十年张罗出自己的广告店,生意做得红火,娶了漂亮老婆。仅这些,也不足以成为榜样,父亲更看重的,是通献致富不忘乡亲,又杀回马枪,去都罗开发旅游。有一阵我就跟在通献身后,待在都罗寨,触目皆是土法上马、因陋就简的旅游项目,问题是,竟然有人来。野马导游拉来客人,门票八十元,导游分去五十。通献的日常工作,就是摆平那些游客,一遍遍解释门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耗尽心力。
他又不好说,退一张票,我就倒亏五十元!
他时而无奈地睃我一眼,说生意就是这样,摆得平就赚钱,摆不平就滚蛋。

凤凰都罗寨
都罗寨的旅游,好景不过两年,其后几年尽管门可罗雀,毕竟仍有人来。为节约成本、有的放矢,搞餐饮的那几家就要小孩守在村口,见有游客在远处山路上冒出,就通知家里人,赶紧将饭馆开张。若无来人,就去干农活。每天时光都不容耽误,旅游可有可无,日子照样打发。
我一堂兄也顺便搞搞旅游生意,河畔搭一间茅屋,屋外布几套石桌石椅,便是饭馆子,打游击似的,拉到客再去生火,有如电影《地雷战》的台词:不见鬼子不挂弦。有一阵他那缺大师傅,见我能侍弄家常菜,叫我帮忙。我有半月时间客串大厨,菜炒得随意任性,在这山林野地,游客吃得粗糙,反而觉得应情应景。
运气好,碰见广东游客,买下一只鸡,叫我们炖汤。广东客将汤水喝尽,一盆鸡肉还在,加些油盐干椒一通爆炒。夕阳落山,游客都离开,就着油爆鸡丁喝酒,数着一天赚下的小沓钞票,堂兄这日子仿佛很滋润。但后来,出一事故,一浙江大学生在河中溺毙。都罗寨的旅游生意强令叫停,通献赔掉不少钱,从此安心做广告业务,不敢染指旅游。旅游生意倒掉后,都罗寨像被人抽了筋,被人收了魂,愈发显得气息奄奄。
某次,有朋友来湘西,我领着他去了不少著名景点,都被朋友一张损嘴痛斥。他想吃农家饭,我就带他去都罗寨,叫亲戚弄一桌。我告诉他,不要小看这破村寨,以前搞乡村游,也有一天接待千把人的纪录。
这地方也能搞旅游?这尖刻的朋友环顾四周,终于小有感叹,你们湘西,还是挺神奇。
不二门
我真正将湘西各县份都走一遍,也是二十岁以后。有两年我跟着亲戚卖空调,接下两种品牌的地方代理,要去各县铺点,得以去到各县份。厂家代表张某跟我同行,每每感叹,说你们湘西,看着全是山,往里一走,人就像跳蚤一样,从每处旮旯里蹦出来。我也不好怎么应答。人各有命,生在哪个地方,就只能享有与此相应的活法。后有一次从保靖去永顺,半道上有人搭车,上来一拨人,把一老年妇女搁在我与张某的旁边。那妇女半死不活,眼已轻微翻白,看向我,也看向张某。据说,她昨夜怀揣心事,一早喝了农药,现赶去急救。到了永顺,张某情绪大受影响,坚持要走,我留永顺找点。
父亲在这县份工作近二十年,认作第二故乡。我去永顺,他就说,一定要去不二门泡一泡温泉。他记得,以前温泉不作任何处理,热水从泉孔喷出、流出,慢慢摊开、散开,好大一片雾气腾腾,哪里都可下人。以前,单日为女双日为男,交替使用。
我第一次去不二门,是傍晚,光线暗蓝,不二门的河流、道路与树木都是深沉向黑的颜色,所以道旁的路灯格外晶莹、璀璨。从大门到温泉,有好几里,冷寂无人,全身皮肉紧缩,正好等着热水泡发。二十来岁时,不二门冬夜的冷清,伤肌砭骨,并不容易适应。到地方,泡大池两元。我往那边瞟一眼,大池不下百人,老人小孩,少不了在里面便溺。又问包间多少?十元。千禧之年,十元能买两份盒饭。进去一泡,便连声喊值。那包间巨大,墙壁无任何修饰,只有经年的斑斑驳驳层层叠叠的水渍。水池两米见方,深有一米,水底铺满了沙。水口有人的脖颈粗,用圆木堵死,用力一拨,巨大水流喷涌而出,射在体表竟有疼辣之感。很快,一池水满,放任那水口喷涌,我躺进去,仿佛躺在涡轮洗衣机上。只要自身放松,不用力气,池中小小的涡旋就能将人翻动,在水中变换着身位。水底,一些沙被水流带走,更多的沙又涌进来。我一直没能搞清这沙从何而来。
热水稍稍一泡,人就得来诸多美妙感觉,闭上眼,沉进水中,感觉自己是一尾半熟的鱼。堵上水口,把脑袋搁在池沿,整个身体便悬空。我还在水中小睡一会,有上好的梦,睁开眼,全不记得。灯光被雾气笼罩,像在遥远地方,不可触及。十块钱,我躺了两个多小时,再从不二门走出,行到马路,看见车流,恍如隔世。
那年,在永顺找好几个电器老板,一直谈不拢。他们生意算盘拨得太精,但好酒好肉每天都管够。我倒不急,天寒地冻,白天谈会生意,晚上又去泡温泉。十块钱得来几小时的受用,现已不可想象。
青年之家
都说湘西除了出将军出土匪,就出文人,我体验过。活在这地方,看不见几条活路,既然从文一途已被前辈乡贤走通,并走得精彩,自然就成为很多人的方向,一头扎进去,九死其犹未悔。说山里人性情偏执,是因这里的环境容不得人太随性,干事必得一条胡同走到黑,要么撞见鬼,要么看见天亮。
在我想当作家还看不见丁点希望,摸着石头亦步亦趋时,就有一帮人来陪我。在我帮亲戚做生意的吉首,湖南最小的县级市,有天去酒吧喝酒认识了老板,姓黄,别人叫他松哥。知道我也爱写,他就介绍我认识文朋诗友。经常会有聚餐,经松哥一介绍,每个人皆有远大前途,眼下只是小有羁绊,暂借吉首容身。不同的脸孔,得以熟悉。松哥是铁路职工,开叉车,在火车站有房,面积不大,经常聚了太多的人,转身都困难。入夜,他也不舍得众文友离去,尽量劝说,就在房中打地铺,挤一挤,睡得热闹。他的卧室有电脑,不想睡的可以在里面上网玩游戏,通宵开放。他老婆竟然也容忍,躺在床上,听着电脑不断制造的噪音。此前松哥已离了一次婚,按某人的说法,松哥与前妻离婚的重要原因,是他前妻对他的朋友不够热情。

2 0 0 5年和朋友骑单车郊游
很快我厌倦了做生意,找着借口待在家里写小说,但这种日子并不好过,在家待久了,家人不烦自己心慌。于是,隔三岔五,还去松哥家里小住,短则三五天,长则个把月。他换了房,在河边的一处小区,环境很好,更适合青年人聚集。住那里面,由松哥发话,叫谁值日,谁就掏钱买菜,弄一天的伙食。一开始,松哥不常点我名,知道我赚不到钱。我写的小说渐渐都能发表,经常主动请缨,出去买菜。一帮青年一起吃喝,三五块一斤的壶子酒,也喝得周身畅暖。一同住在那里的文艺青年,变换各种花样,以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有的编商业杂志,有的拍微电影,有的搞编剧,有的开广告公司,尽管无人大富大贵,几年之后,渐渐都能有了稳定的饭碗。松哥的第二任妻,姓杨,鉴于她的大度包容,有一次喝酒,我建议将她侧面头像放至十寸,沿着脸廓将背景铰掉,贴至墙上。再买一张金色电光纸,裁成细条,在头像周围贴一圈,当成是光芒。众人一致叫好。
那些年,母亲经常骂我,老住在别人家里,不肯回自己家,脑袋有毛病。我也不知说什么,我就喜欢跟他们泡在一起,你疯狂的想法,总有人应和、支持。

古丈红石林
后来自己成了家,当然不好再去别人家住,但一有机会,我会将以前一起住松哥家的朋友聚起来,接着喝酒、瞎聊。后来松哥又结了一次婚,现任的妻子也欢迎大家去家里看一看,去家里住一住。
洛 塔
我去洛塔,是作家班同学国平介绍去干活。龙山县国土局要在洛塔开发一处地质公园。喀斯特地貌所涵盖的所有类型,这里都备齐,养在深山人未识,要找人写文章推介。我去时是一年最冷的时节。
当天,国土局一位科长陪同,一路解说。洛塔山高路陡,景点散布在远近五六个村庄,只能挑几处有代表性的,天坑、地漏、溶洞和石林。中午忽然下雪,还夹杂雹子,砸在车窗上,坐里面也像是连续中枪。风景没法再看,科长带我们进到一农户院落。一溜灰败的板房,板壁挂有农家乐的招牌。进去才知,这农家乐不用点菜,十块钱一人,饭菜管够,还有米酒。
屋外冷得人脸皮细跳,一进到屋内,就有热气扑腾而来。这家人的火塘,长两米,宽一米五不止,一圈能围二十人。塘内码放整捆柴,烧得哔剥作响,火焰飙起两尺高,红黄蓝三色都在里面。我一时不敢坐近。火塘周围摆了狗儿凳,只一块火砖厚,坐上去,也跟坐地上差不多,腿自然盘起,像一帮和尚跏趺而坐。当天六七人用餐,另几人,是来慰问洛塔煤矿贫困工人的政府干部。天气一冷,肚皮瘪得就快,十块钱一份的农家盒饭,让每个人怀有期待。户主留一脸连鬓胡,正从火塘上取下一块腊肉。年猪已杀过,密密麻麻的腊肉,悬在每个人头顶。火越烧越大,烤出些许人油,受不了的,踱到窗边看雪。雪在这山野深处,气势恢宏,密密匝匝,盯着窗户往外看,久看一会,不免隐隐担心,这场雪会疯掉,刹不住;屋内却又暖热,让人踏实。盯着外面,下意识紧紧衣服,再一摸额头,却沁出毛汗,屋里屋外,窗前身后,一时心生虚幻。
菜炒好,腊肉、冬笋片、豆腐干、大头菜,一并装进铁锅,弄成杂烩。女主人意外地漂亮,手脚也麻利。火塘的火此时已扒散,正中央搁一个三脚架,铁锅架上面。筷头很长,人依旧盘坐于地,身体用力前倾,伸一伸手,钓鱼似地夹菜,夹到哪块吃哪块。连鬓胡拿来米酒,胶壶装着,起码二十斤,搁在远火的地方,需者自取。
在这小屋,听着外面风声,不需劝酒,每个人都喝得过量。午后,风雪更急,每个人将手袖起,靠着板壁打瞌睡,不想睡便聊天。酒一喝,话一聊,所有男人都自来熟,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经历。
酒一喝,看看眼前晃荡的女主人,愈加觉得她漂亮,不免还有些……可惜。那年我还没结婚,心中竟暗生羡慕,忽然地想,有机会也找一美女,在荒山野岭开店,犹如江湖高手阅尽世事,金盆洗手,换来一段自在从容的余生。
锅子撤掉,火焰再次飙高。我的想象正待蔓延,耳畔听人说,雪下这么大,等下可能封路,今晚只能待在农家乐过夜。别人立时紧张,纷纷抱怨,说家里有事等着去做。我却不信,谁又真有非做不可的事,嘴贱罢了。我还暗自高兴,想着能有整整一夜围炉夜话,能听来多少离奇故事?
天将黑,雪下得没了力气。有人报信说路并没堵,要走马上走。半夜气温再降,凝雪成冰,一定会封路,可不止三两天时间。所有人都雀跃,等不及地收拾东西。我只好告别这小小的农家乐,告别火塘里一堆烰炭。
洛塔我只去过那一次,地质公园此后并没有搞起来。回头想想,我心里知道,那天陡生的羡慕,其实浸透了虚情假意。
一个兄弟
第一次去龙山,是2 0 0 3年盛夏。卖空调那时,走遍湘西,唯缺龙山。龙山在湘西北端,距吉首太远,空调发过去路费都不划算,厂家将其划归张家界的代理商。那年赶去,有个事由,我弟弟从龙山烟厂下岗,买断工龄得十来万。父母在家中盼归,弟弟却一个月不回,两个月不回。父亲担心弟弟将买断的钱轻易花光,要我去龙山将他拽回。我在家写作,随时有空,就奉命行事。那天一早出发,天黑才到,坐车坐到一身散架。弟弟领一帮兄弟接我。他1 9 9 7年中专毕业,一直在龙山工作,性情豪爽好交朋友,这时已经积攒下一票兄弟。说我要来,他的那些兄弟都不闲着,要接风,还抢着排序。当天晚餐去到夜市摊,和消夜连着一起搞,摆出打持久战的架势。
当天做东的冰哥,刀条脸上长有小胡髭,一眼看去,是他父母贡献给江湖的一份礼物。讲话当然也是冰哥主持,兄弟情谊,走南闯北的见闻,以及女人如衣服……次日,弟弟才知,冰哥当天囊中羞涩,将摩托开进当铺,换来买酒的钱。我一阵感动,跟弟弟说,你帮人家把车取回。弟弟说,这事干不得,冰哥要翻脸。
龙山,我在小说中一概写成朗山,在这里我找到不少写作素材。小说中我曾这样描写:“在云贵高原的延伸部,朗山算得是个较大的县份,六十几万人,城区就有十多万。在几横几纵的街子上,长年游荡着不少泼皮,面色不善地盯着过往行人。总的来说,这地方民风剽悍,弄性使气、逞勇斗狠,是一块出产泼皮的土壤。”这样的描写,龙山的朋友也说到位。因这县份交通不便,到最近的永顺也要三个多小时,僻远闭塞,造就了这小城一种狂欢的情绪,男人们在外疯狂找乐,回家还要打老婆。那次去,我本是要负责将弟弟带回,没想他的兄弟每天邀请,吃了就玩,日复一日不见消停,我也是有腿拔不动,待了半月。
弟弟被叫回,钱交由母亲管理,在凤凰他已待不惯,说这里人哪有龙山兄弟好玩。
那次去,印象最深、聊得最多就是冰哥,离开龙山,还时常通一通电话。我邀他有空来凤凰,不是客套。后有一次,冰哥真就过来。弟弟不在,嘱我说,你不能喝,邀几个凤凰的朋友陪冰哥。没想冰哥一来就是四五辆小车,十来个兄弟,还各自带着妹子,打扮一半是杀马特,一半是纯种杀马特。龙山凤凰,人的性情习俗大不一样,后来我娶了龙山女人,更有体会。在凤凰,朋友聚会,带着不是老婆的女人出席,是扫兴的事情,但在龙山,这能显出一个男人有本事。当天聚会,两边朋友谈不到一块,我只好苦苦支撑,不让气氛冷掉。后来在电话里联系,有了教训,不敢贸然邀他过来。
我去龙山,总要打打冰哥电话。他已经到外面发展,不常在家。有次碰面,知道我现在是干作家,冰哥就说,呃,我年轻的时候也想当作家,没有坚持,要不然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写。我说,你活路多,哪能跟我比,除了写字赚钱没有别的能耐。冰哥听出来,说你这个人其实要不得。然后喝起来,你一杯我一杯,趴下一个为止。

2 0 1 4年与女儿在凤凰小巷

满楼秋色
坐龙峡
出古丈县城,再走二十里可到坐龙峡。我三番五次把外面的朋友带到那里去,是因为凤凰成了让人吐槽的地方。而坐龙峡,实在可以帮我挣回些许颜面。
凤凰很小,因沈从文,写作的朋友常来。人在凤凰,时常尽着地主之谊,有时真会怀疑,自己就是地主。文友心思活络,往往怀揣着先入为主的印象,来到凤凰。走上一圈,却又感慨,你们这里太吵,太商业,没了《边城》的味道,不是我想象的模样。这种感慨,听得多了,我便这么解释,本来不吵,外面的人都涌来,搞成现在这模样。
再说《边城》那意境,假若今天真有存在,卖一卖门票,转眼变了质。
后来找到坐龙峡,众口难调,它能调。再说,古丈是全省最小县份,因它小,人都熟。只要找个本地熟人,都能免票。坐龙峡罕有人知晓,就像平常百姓,端不起架子。坐龙峡藏得巧妙,不让人看出端倪。走下马路,走过几户板壁农舍,寻常的菜地,寻常的山道,前来陪同的古丈朋友,一路还和行人打招呼。这时候你以为不是来看景,是要到农家做客。山路一转,两壁变长变狭,山间一道巨大的缝隙忽然摆至眼前。往里走,路迅速变窄,溪流琤,路面时现水洼,所有人都要蹦蹦跳跳,力保鞋子不湿。外来的朋友,跳来跳去,心情还放松。
再转一急弯,路陡然中断,石壁上打出道道钢钎。
这时,外来的朋友隐隐感觉不对路,就问,是要往钢钎上爬吗?我们便回,当然,只这一条路。你看,上面还有扶手,稳稳当当,我们都来过好多次。外来的朋友小心翼翼爬上去,看着悬,踩上去倒也踏实。一开始爬得小心,见有水流线瀑挂下,闪转腾挪地躲开,不让自己稍有湿身。我们本地人,此时就已暗笑,人到坐龙峡,竟想守身如玉。
走半小时,都是爬上爬下,外面的朋友,特别来自平原的客,不能适应手脚并用的行走,多少有些吃不消。此时定有人问,差不多了吧?答曰,快了,快五分之一样子。外面的朋友咋舌,扭头一看,已无退路。想原路返回,不是不行,但很多路段只容一人穿行,后面游客陆陆续续往前涌来,谁要想退回,只好从人脑袋上面飞跃过去。外面的朋友,这才知道,自己已是鸭子上架下不来,只好把牙一咬,硬着头皮走。崖壁上水流飞瀑渐频、渐大,这时候,每个人都要伸长脖子用力吐纳吸气,哪还顾上湿不湿身。水一浇,正好降温。
有几处崖壁,几乎要垂直往上爬。不惯攀爬的客,上有人拽,下有人顶,终于站到崖壁上端,大呼小叫,满是喜悦。
初来这里,是人都会担心地形险要,不安全。古丈朋友却说,当初设计路线,诸多因素都已想好,都已规划周全,有惊无险是它特色。人命关天,真要出意外,谁也担待不起。
起码两个半小时,终于走完狭长的坐龙峡,初来的朋友大都累到散架,吐着舌头。问他爽不爽,往往撅起拇指,说这里必是湘西之行印象最深的景点。
于是我就明白,外来的朋友就像小孩,不能太娇纵,让他不痛不痒玩上一天,免不了要发发牢骚;把他累得发牢骚都没了力气,只好说爽。再说,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把朋友带到坐龙峡走走,正好贴合了当下的潮流。
记忆深处那头牛
还要再说说我的作家班同学国平,没别的,他对我很重要。
2 0 0 4年我们一同去毛泽东文学院读两月,其实交朋结友,喝酒聊天。国平很少出门,身上带八百块钱,按他算计,两月能撑下来。没想省城物价比龙山桂塘坝贵得太多,他紧攒慢攒,一个月没完用掉五百多,见到喜欢的书不敢买,一颗心隐隐发疼。作为同学,看得出他的窘迫,又不敢明着帮,就说不想在食堂吃饭,饭票买了却用不着,都给你。
国平话不多,喝了酒想说点什么,找不出话头,索性就背自己的文章。他发表不多,一共四五篇千字文,全都发在地方报纸副刊,副刊主编是他大舅子。看他文章,虽然下笔吃力,但他对文学的虔诚,非一般人可比。他在一处乡间小水库当工人,平日能看到的文学书籍不多,地方文联的《神地》杂志,他一字不漏,从封面读到定价。我质疑,内刊没有定价,他竟能说出这杂志内部准印证的文号。
他背自己文章,一脸的投入,不容别人打岔。他是老实人,性情好,但他最在乎的事谁要打搅,说不定后果很严重。反正,没人敢以身试法,他要背自己文章,大家就安静地听。不想听,就溜之大吉,反正他闭目背诵,去留随君。我这人反应稍钝,一旦听得发困,抬腿想走,四下看看,房间里只有我和国平,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那四五篇副刊短文,一篇稍长,《记忆深处那头牛》是国平的代表作,他可以倒背如流。他最爱背的,也是这一篇。听得太多,我也能记住其中一些句子:“……遇上高坡陡坎如果你不叫它调头,它会勇往直前,好像把高山和云彩都踩在它的脚下。用它耕地你会感到心情舒畅。”
听他背诵文章,心里也在反复考量,国平兄的东西好吗?
……语言太老旧……大概只是一般……其实还不错噢……真不错……好!

凤凰县沱江镇政府运动会
静下来想想,我喜欢他在背诵自己文章时脸上的神采,手上不经意捏出来的动作,忘我的姿态。我乐意被他洗脑,在这过程中我感悟文学何以让人忠贞不贰。
作家班时间短暂,回家以后我们还时有联系,也去过他时时跟我提起的桂塘坝,是三省(湘鄂渝)交界之地,山高水低,草深林密。这里的人活得很自在,像国平一样,身上多少都有一些忠耿的脾气,对你好,你要接受,你不接受,他恨你。
国平认我这个小老弟,相处四五年,见我还没女朋友,就将他的堂侄女介绍给我。国平性情坚韧,女孩那边,有他帮我软磨硬泡,这事情竟还顺利。我还专门请一桌“改口饭”,邀国平来吃。昨天是兄弟,今天分了辈,无奈又幸福的事。
婚后,老婆偶尔有心情,要和我讨论缘分这种事情。我就说,哪是什么缘分?以前我听你堂叔背文章,全班同学就我听得最认真,这才把你赚到手的。
神农观光园
身边,总有些朋友,脑袋里满是古怪想法,且会将古怪想法坐实。比如这个坡头,出城十几里地,十分荒僻。一位姓吴的熟人,几年前脑袋一热,投进去不少钱财,将这荒山坡头围了一大圈围墙,建起亭台楼阁,种上各样果树,搞成自己的庄园。

土家老汉
我知道,虽然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其实大多数人骨子里都有当地主的隐秘情结,像外国电影里一样,买下一个山头,建立一处庄园甚至是大而无当的城堡,关上城门,过自给自足的日子。我想,这吴老板必定也被拥有庄园的梦想折磨着,才会在一处荒凉的坡头使尽力气。但是,仅仅建成还不够,不可能从别的地方挣钱来维系这么大一个庄园,它自身需得有造血的能力,于是这庄园就变身为神农观光园,郊游、会议、住宿、烧烤、用餐,尽皆成为它的经营项目。开业那天,请了朋友免费吃喝,杀猪宰牛,人来人往,推杯换盏,猜拳行令,好不热闹。看那气势,这里不光是吴家庄园,也是一众熟人朋友共同的乐园,往后生意好起来,应是指日可待。
但地方太偏,只经营一年,神农观光园就难以为继,关门歇业。
坡头已经承包二十年,生意做不下去,要转让也无人敢接手,就留一个人守门,荒在那里。种上的果树,在荒败的坡头努力生长,三两年后开始挂果,桃李梨子枇杷……果子成熟,吴老板又邀了各路熟人,去到神龙观光园观光,只要免费,人就蜂拥而至,这里难得地又热闹起来。有人吃着过瘾,建议说这个观光园不妨再开起来,以采果子为特色经营项目,必定招徕不少人,再辅以餐饮住宿,哪有不赚钱的道理?吴老板只是笑笑,不吭声。不仅是他,我也知道,朋友好交,生意难做,不要钱不愁没人来,真要是收取些许费用,人就像空气一般遁入无形。
我喜欢这个园子荒败的气氛,弄成不久的木质亭台,因无人看管,表面斑驳,生霉长苔,仿佛有了些年头。我也喜欢当初刻意种下的花草树木,现在已和野草灌木杂生一处,一团一团,参差葳蕤,满是生气,也让我无端地想到《聊斋》。我写小说,心里一直向往蒲松龄那样的生活,找一处荒败的院落或者园林,住下来,白天绞尽脑汁去构思,去码字,晚上想象着这荒山野岭,是否有古怪的来客造访,敲你的门,双手哆嗦着打开,要么是鬼怪,要么是美得不可方物的女人……要不要赌一把?
在这些想象中,朋友的这个荒园就和我建立某种联系,对我形成魅惑和召唤,我相信待在那里面,即使没有奇遇,笔下也能生出不一样质地的文章。我有这想法时,刚刚结了婚,老婆有了身孕。我说我想独自去朋友的荒园住一阵,老婆就认为我是不想照顾她,以写作的名义,逃避责任。那还能说什么?只好等下去,偶尔想到朋友的荒园,心里就发痒,坐了车去逛一趟,又回,想待在那里有如隐居的愿望,来得愈加强烈。接下来,小孩出生,我就更离不开家。
一晃三年,女儿能蹦能跳,小嘴不停地说话。老婆带着她回娘家住一阵,我无人看管,隐居的念头再一次浮出来,变得强烈。我备好一切必需的物品,去到荒园,心里想着,起码住上一个月,有这样的耐性和坐功,一定能写出不一样的文章,一定能使自己更加像个作家。
事实上,待了三天,我就离开那里。只这三天,我就无比清醒地发现,我更愿意活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