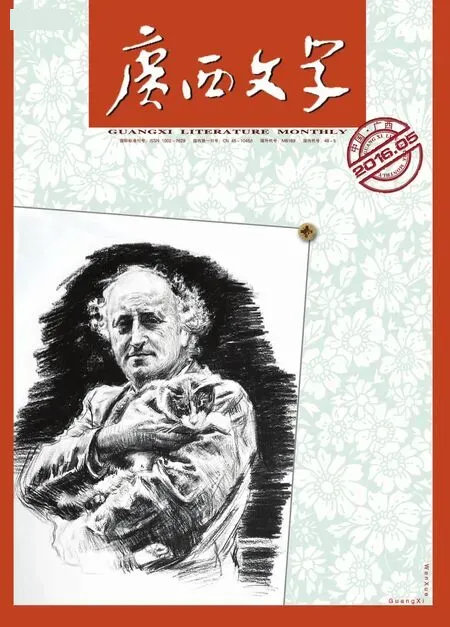中国桂剧
唐 女/著
前些日,我在梦里说,不要再搬家了,我只想住熟一座房子。一颗那么小的心,能够热爱的东西想必不会很多,能够记住的地方想必也不会很多,能够进入骨髓进入梦境的,就更稀罕了。
在离我不远的龙水镇桥渡村委,有一个小村庄,叫锡爵村,它完整地保留了我的童年记忆。走进这个小村,乡村的破败印象被清洗一空,替而代之的,是满满的人气和温暖的砖瓦。最为关键的,是小时候打着飞脚,赶去很远的村子看桂剧,那些潜伏在梦境里的神秘演员,就住在这个村里。
锡爵村明代建村,左有凤山右有印山,凤山飘扬如旗,印山圆嘟嘟的如鼓,按照堪舆者的说法,“左旗右鼓出将台”,因此取名“锡爵村”。后被简化为“石脚村”。它呈船形,依傍在全州至大西江的县道旁。锡爵村旁边万乡河的栖丘上有五百多棵古樟树。看这里的风景,会产生那么一瞬间的幻觉:这里才是上天给我们配备好的生活环境。

穿村而过的古河
再去的时候,一大群人。锡爵村里全是阳光。
我奔走在横七竖八的巷道里,被干净的地面和各式风格的民居吸引,不停拍照,很快脱离了人群。
三条发源自越城岭的小溪流,自西而来,汇聚村口,流经村庄,进入村南的广阔田野。小河水流激越,碧绿清澈。河上有古桥三座。河边有木芙蓉、桂花、枇杷等花木,横卧河上,枝繁叶茂,花团锦簇。有古洗衣埠头,掩映在树木当中,村妇洗菜捣衣,笑语盈盈。白鸭刚从河里上来,站在洗衣埠头清理羽毛。
全村有五个古门楼,门楼墙脊各异,有蜈蚣形、一字形、二级山墙形,分立在各大家族古建筑群之前。现留存最大规模的谢裕寿家族古建筑群,原为五座正房子五个天井,五座横房子,各设雨廊连通,布局井然。谢华昌家族的古建筑群面积大约占全村五分之一,有一座综合了中西风格的民国建筑,青石坪和石板路保存完好。日本军从飞机上扔下炸弹,炸毁并烧掉了谢华昌家族一片古建筑,形成一个大坪,后被称为火烧坪。
这些老房子都住着人,暖意融融。正房子大多是闭合式三合院结构。大门在两侧,门头上题写着“苍松翠柏”“丹桂红兰”“瑞霭”等字。最美的地方是天井里的照墙,多为仿木结构的牌坊式灰塑装饰,正中为一大“福”字,牌坊底下是梅兰松竹鳌鱼等图案。牌坊之上题写着“玉树临风”“佳气葱茏”等字。天井水沟全是青石铺设。廊檐下放一水缸,旁边搁置着洗脸架。天井里种满花草,尤以兰草茶花为多。看着这么个天井,我一下就回到了童年。我就是在这样的屋宇里长大的,无数次梦到这个天井,梦到天井里的花草阳光和雨水,梦到照壁上能飞起来的“福”字,和各种好看的雕塑图案。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眼睛有些湿润。我不知道缘何感动,缘何幸福,那是一种深埋心底的情愫,此刻莫名涌出,难以自制。能够让这些古建筑还保留着体温,把庭院和巷道打扫得这么干净,在天井大门口种满花草,能够延续和满足于这种旧生活的居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找到大部队,他们在谢裕寿家的堂屋里,听村民唱桂剧。
这个堂屋的箍壁,历经一百多年,由泛着木香的黄变成了嗅不到味道的深褐,老得倔强和硬挺。后壁是闭合的大门,两边开着小耳门。大门上贴着倒“福”,门边停着一辆凤凰牌单车。单车前坐着一个老人,膝头搁着一把二胡,右手一拉一拉的,曲子婉转动人。右壁上挂着一块长方形镜子。镜子里有一个草帽,是左壁上挂着的那个。一个清癯的老人站在镜子下,穿着一双绿色解放鞋,军绿色的确良薄裤,和旧得发白的蓝中山装上衣,头发灰白,身板挺拔,背着双手,昂着头,进一步,退一步,在二胡的伴奏下唱桂剧。照壁上写着“玉树临风”,阳光打在照壁,映到堂屋,他的右脸铺满暖光,长长的眉毛也亮了,那双深陷的眼睛,矍铄有光。一大帮人,有的坐有的站,都痴痴地望着他唱。从他喉里吐出的每一个字、每一句唱腔,都碰到了木壁,反弹回来,整个堂屋亮堂堂响当当。好几个听众眼睛里晃动着泪花,包括我。虽然是用全州话唱的,但我对剧目不熟,听不太懂他唱的意思,只是无缘无故的,被他的声音感动得一塌糊涂。不得不承认,他唱的有一种强烈的震撼力,一下征服了所有人。透过泪花,我看着那个瘦小的老人,想不出为何他具有如此大的能量。同去的人群中有全州桂剧团的人,他由衷赞叹,比专业演员唱得还好。
后来一个中年女性唱了一段,音调很高,用假嗓子唱的,咿咿呀呀,也怪好听。
一晃就到了晌午,一群人要走了。我着急,我还不知道这两位歌唱者的名字呢。他们说,下次再来吧。
存了他们的录像,一段时间,我放来听,听得一愣一愣的。他们唱的到底是什么?在他波澜不惊、宁静如水的眼睛里,到底暗藏着多少故事?在她阳光般的微笑里,又融汇着多少幸福往事?
一个人来到锡爵村,谢裕寿的房子找不到了。我不着急,慢慢感受雨中青石板路的光滑平整,和青石两边鹅卵石子的光芒。倾听雨水在屋檐上跳跃,又流下,落在天井里。这样的雨水并未让村庄起一点泥泞,只洗得村庄更加清亮洁净。村里巷道见不到人,一只白色的小狗发现了我,躲在围墙边朝我吠叫。
我望着各条巷道有些迷茫,努力分辨自己在村中的位置和方向。雨中飘来了歌声,一个男声,嘶哑高亢,唱的正是桂剧。没有二胡声,只有这全村的雨声为其伴奏。我有了方向。循着歌声,穿过几座古宅,横越几条巷道,最后站在谢裕寿的家门口。
进屋,看见谢裕寿在右长房里高唱,宽阔的背对着我。我不忍打断。收伞的声音惊动了他,他回过身来发现了我。说明来意后,他把他们桂剧团的团长谢崧恕叫了来。谢崧恕就住在那座民国建筑里。他没有带来二胡。我先做文字采访。
桂剧是广西的主要剧种之一,广西汉族地方戏曲。清代嘉庆年间,湖南祁剧传入桂林后,经过一段时期的语言变化,才渐演变为桂剧。
《全州县志》记载,“桂剧的产生系源于北而流于南,流传于桂林、柳州、南宁、河池及梧州北部讲‘官话’的地区”。全州县是广西的北大门,接邻湖南,常有祁剧团来县演出。“清代中叶,全州县内外较大的祠堂、庙宇和会馆都建有戏台,固定戏台有二十座,临时戏台无数”,可见民间戏剧表演之盛况。“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全州所辖西延分州油榨坪首建‘秀’字科班,为广西桂剧最早的科班。”之后科班如雨后春笋,从全州大地上冒出来。

村民家的照壁
由于桂剧的历史与徽剧、汉剧、湘剧、祁剧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它的剧目多与皮黄系统的剧种相似。它融合、吸收昆山腔、弋阳腔和乱弹等几种戏曲声腔,形成了以弹腔为主,兼唱高腔、昆腔、吹腔及杂腔小调等五种声腔艺术的剧种。桂剧唱做念舞俱重,尤以唱工细腻、做工传神见长。伴奏乐队亦与其他皮黄系统的剧种一样分为文场、武场。文场使用二弦(似京胡)、月琴、三弦、胡琴以及曲笛、梆笛、唢呐、唧呐(即海笛)等,兼配部分中、低音乐器;武场使用脆鼓(板鼓)、战鼓、大堂鼓、小堂鼓、板(扎板)、大锣、大钹、小锣、小钹、云锣、星子、碰铃等。桂剧角色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还有一些跑龙套的下手,称为杂。
民国时期,锡爵村有个唱男旦的叫谢玉洁,出自“玉”字科班。农闲时,被请回村里唱桂剧,谢崧恕的父亲偷偷跟他学。谢崧恕的爷爷发现后大骂:学什么不好,学这下九流的桂剧!他爷爷没有制止住他父亲,他父亲在村里组织了十多个人,跟着谢玉洁学戏,之后成立了桂剧团,他任团长。剧团演出到解放时,剧团里的演员大多被划为地主,剧团自然消亡。父亲在谢崧恕的童年播下了桂剧种子。1955年,全国大兴文艺,谢崧恕时年十六岁,在桥渡大队组建了一个二十多人的桂剧团,请来全州县“桂全”科班出身的桂剧男旦桂香任老师,成员大多为十岁左右的小娃娃,后发展为四十多人,他任团长。锡爵村剧团在桂香老师手上四年,后请湖南“最”字科班出身,湖南景德圩的祁剧艺人“德国花脸”陈最利为师,还请了桂林桂剧团的老小生向金武、武艺超群的小霸王蒋德才等艺人为师,经这些老师严格正规训练达十几年,学会的剧目有上百部,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桂剧演员。

村民家门口
当时,县内业余剧团一下冒出了九十多个,大多只在本村唱唱,能够在各地巡回演出的剧团不多。锡爵村剧团被请去唱戏的村落多达二十多个,每年要唱四十多台戏。唱戏时间多为双抢后的农闲时节(唱二十多天)、割了二季稻(唱两个月到过年)、正月里(年后唱一个月)、庙会、办喜事等。由请家过台子来,写明唱戏时间、几台戏、剧目、费用等。近的地方来请,对方来人抬盔头箱,演员们走路去;远的地方用车来接。一天唱两场,下午一点到五点,晚上八点到十一点。受欢迎的剧目有《三娘教子》《拾玉镯》《杏元和番》《斩雄信》《拦马过关》 《打棍出箱》《九世公上寿》《白蛇传》《薛家将传奇》 《隋唐演义》等。最受欢迎的是整本戏,一台接一台,演上好几天,跟看连续剧一样,观众说,这才过瘾。观众看上瘾了,通常会加场,本来写了三天的,再追加三天。下一个请家,也只得等他们看完了,才过台到自己的村子去。唱得最长的,是在石塘镇广竹塘村,唱《薛刚反唐》整本戏,唱了十多天。也有人漏掉了喜爱的剧目,比如《白蛇传》,要求重演的。每去一个地方都不能唱重复的,所以要经常更新剧目,学新戏。有些剧目难度大,有花旦怕《和番》、花脸怕《讲邦》、老旦怕《造汤》、生角怕《开箱》、丑角怕《过关》、小生怕《拦江》之说。唱戏得的钱除了给老师开工资,演员们从未分钱,有点剩余就添置道具了。他们说,不图别的,只图娱乐群众,也娱乐自己。
最让他们难忘的,是在凤凰乡穿山村的那次演出。
穿山村住着谢、周两姓,中间一条村道隔开。谢姓家族势力较弱,历史上,他们谢家请来戏班唱戏总有人捣乱,没有一场戏能唱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不信这个邪,过了年,请来锡爵村桂剧团,要求锡爵村剧团一定要把戏唱下来,这关系到他们谢氏能否在穿山村树立威望。
他们在戏台上架了一台机关枪,主事的人先说明缘由,说用这台机关枪镇台的,不许捣乱。第一台戏三个小时,完整唱了下来。这是他们请来的剧团第一次唱完一台戏。他们一高兴,请剧团一连唱了七天戏。演出的时候,下起了大雨,观众一个也没走,一个也没打伞戴帽,怕挡住后面的观众。其实,这七天的戏,唱得惊心动魄。穿山村的邻村阎家村,也请了一个戏班在唱。相当于在跟他们唱对台戏。那边唱了一出《过火焰山》,这边的观众赶到他们那边看戏。之后,这边的观众越来越多,连阎家的村民也跑了过来。那边剧团着了急,去请名角来救场,也没救住。
穿山村谢家人脸上有了光彩,说话的声音洪亮了,腰板挺直了。他们杀了羊,炆了正菜(炖了肘子),煸了几个碗(菜),盛情款待锡爵村剧团。他们说,这个新年是最喜庆的。观众称他们为“王牌剧团”。附近村的一个教师给他们写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文艺超群”。全州老艺人唐义武也说,锡爵村剧团是全州业余剧团里唱得最好的。

锡爵村的祠堂
说到受欢迎,他们在石塘外枧村演出,人山人海,轮到上台的演员找不到人,后来才发现演员出去解了个手,在外面挤不进来。唱到开了春,村民还不让他们走。他们说,家里的田要下秧了,你们的秧都手指那么高了。村民哄骗说,还没到下秧的时候,这些人赶鬼,下早了。剧团的人着急啊,有的在当地买了尼龙竹,早上没戏的时候,就坐在戏台前削尼龙竹。本来唱完最后一个白场就回去了,村民又央求唱夜场。唱完夜场已经深夜十一点,他们一刻都不敢留,半夜赶了回去。这样的事遇到过好几次。
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断了几年,一眨眼就到了20世纪80年代,电影逐渐进入村落,请电影的也多起来。石塘镇广竹村分作两派,一派请电影队,一派请桂剧团。一部电影一个钟头就演完了,一台戏剧要演三个钟头。看完电影的村民想来看桂剧,桂剧看门人死活不让他们进。他们拿钱买票,也不卖给他们。那时候,很多村子都出现了这样的对峙,而且矛盾非常尖锐,水火不容。到后来电视兴起,《霍元甲》 《陈真》火遍全国,对桂剧甚至电影有了巨大冲击。90年代,当电视机摆上千家万户的家堂,一家人都围着电视机,看雪花乱飘的电视,桂剧这台活生生的戏就被群众遗忘了。
现在回过头来,想看一台桂剧,却突然发现,曾经红了半边天的桂剧,已经消失了。很多名角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谢崧恕的爱人李桂英,身材高挑,一生饰演小生。她文武双全,唱功好,武功也好,情感充沛,表达温婉细腻,缠绵悱恻,唱《杏元和番》《柴房别》等剧目,常常唱得台上台下哭成一片,流着泪水的观众跑到台前去放鞭炮,以示对其表演的夸赞。提起她,谢崧恕便低下头,沉默不语。一旁的谢裕寿说,谢崧恕也演小生,他们两口子经常同台唱戏。如《双卖武》,两人同仇敌忾,与牛皋对打。两人的功夫都了得,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惜她去得早,剧团损失了一个好小生。
看着谢崧恕黯然的神情,我试图转移话题,说,我只见过你能拉一手好弦,还没见识过你的唱功和武功呢。
他顿时来了精神,说,我这就给你唱一段。因为只有他会二胡,找不到伴奏的,他就清唱。唱的是《三娘教子》,唱完之后,打了几个哈哈。我想起谢云妹唱的,应该也是《三娘教子》。他出去找来一根木棒当枪使,在堂屋里一边吆喝,一边舞起棒来。那根粗大的木棒在他的手里旋转,看得我眼花缭乱,出现了很多重影,打得风呼呼作响。还要转身转圈,从木棒上跳来跳去,惊心动魄。他说,单是在手指上转枪这一功夫,他就整整练了一年。除了耍枪,还有耍刀、鞭、剑的功夫,哪一门都是硬功夫,戏台上却是武戏文做,风度翩翩。

锡爵村的门楼

谢华昌演唱桂剧,谢崧恕伴奏
进来一位老太太,身着红色毛衣,项上挂着一条珍珠项链,一头鬈发,肤色红润。谢裕寿说,来得好,来唱一段给小唐女仔听。她说,死了半截了还唱什么唱。谢崧恕说唱一段就唱一段吧。他回去把二胡拿来,调好弦,说,来一段吧。这位老太太像个孩子,对谢崧恕百依百顺。开始唱,音起低了,说没找到感觉。谢崧恕说,可以,唱下去。平常他给别人伴奏,总是低着头拉自己的,这会儿,他一边拉,一边望着老太太,老太太也望着他,不断调整自己的音高,终于找到感觉了,唱得非常大声,唱腔也拿得准确。谢崧恕说,这就对了,就这样放开来唱。后来才知道,她是他现在的老伴。她在全州县城工作,退休后,想组个戏班唱戏,找到锡爵村来,最后找到谢崧恕,与他产生了感情,嫁到锡爵村,守着他过日子。看着他们情投意合,一唱一和,心里突然一热,哎,幸福不就是这样的嘛,两人耳鬓厮磨,度过每一个有情有义的日子。他们住的老房子便有了温情,有了光泽。
谢崧恕的女儿在富川桂剧团,还是唱小生。
晌午了,一位大姐让我去她家吃饭。她家院子里有菜地,一垄一垄的,在雨水里绿得逼人眼。吃的是刚熏好的腊肉,旁边烫着刚摘的菜花。米饭非常香。她说,这还是中稻米,晚稻米更好吃,可以不用菜。我破例吃了两大碗饭。这个村不单产好米,还产禾花鱼和南丰蜜橘,吴茱萸茶也是一大特色。看着青烟迷蒙中的几片亮瓦,听这位大姐说,不管楼修得再好再高,还是想要这么一个火房,有这么个火塘,有火塘上一大堆腊肉,心里就踏实了。外面又下起了大雨,烟被压在屋里出不去,我的眼睛被熏得泪流不止,嘴上还连连说,是啊是啊,就是这样的烟火味。
打着雨伞,经过一座竹林,拐入村道,我又迷路了。大姐把我领到谢裕寿家。堂屋的炭火燃着,谢裕寿趴在炭火上的方桌上写桂剧谱子。以前学桂剧是没有这样的谱子的,全在师傅心里。现在好了,他说,有了这谱子,就跑不掉了。我看有《杏元和番》《三娘教子》《拾玉镯》,这都是他们以前常唱的剧目。
谢裕寿,1951年出生,十几岁唱样板戏,后来跟着锡爵村剧团学桂剧。他唱净角,就是花脸。花脸的脸谱他自己画,他说,锡爵村剧团的花脸脸谱比桂林班的花脸脸谱勾画更细致、更精美。我问,你还记得怎么画吗?当然记得,他说,他还保存了好些脸谱图案。说罢拿出来指给我看,这是张飞,那是雄信。原来一张脸谱固定了一个角的。这些凶神恶煞般的脸谱要是画在他的脸上,他反过身来,准会把我吓得双腿筛糠。不过,当他嘶哑着唱出一台《平贵回窑》来,我又觉得这些花脸也并不是那么可怕了,他们是忠孝仁义的化身,是老版英雄。
谢裕寿的爱人谢云妹,就是第一次给我们唱花旦的那位。她现在去了城里带孙子。说起她来,谢裕寿如数家珍,只要她待在村里,村里便立马有一群妇女围聚在她身边,跳个舞,健个身,唱个戏,热热闹闹的。她一走,队伍立马便散了,村里变得冷冷清清。她到了城里,又能在广场集聚一帮妇女,跳个舞,唱个戏,热热闹闹的。她身上那个文艺热情,终身不散。跑村唱戏那会儿,她正怀着身孕,他们的角是一个眼儿一口钉,谁都缺不了。正唱戏,肚子疼了,剧团派人送她去医院生产,走到半路,她的肚子疼得厉害,走不动了。离医院很远,天又黑了,急死了谢裕寿。另一个人跑去医院叫来担架,把她抬到医院,就生了。后来又带着这一岁的孩子东奔西走去唱戏,终因百日咳,没养大。后来的戏班都拿她说事,谁要是怕苦怕累,他们就说,谢云妹要生了,都还腆着肚子唱戏,谁还敢跟她比苦比累?
随后,进来了一位男子,这个清瘦的老人就是第一次见面唱戏的那个。他叫谢华昌,唱生角,十四岁登台唱戏。著名桂剧老艺人宾菊清看了他的表演,要收他为上门弟子。谢华昌的外婆不准,说这是下九流的事情。他的父亲很爱桂剧,经常请来剧团在家里唱戏,自己打鼓。谢华昌与小弟一起学戏,小弟唱花脸,唱得非常好,可惜,很早走了。
我好奇,能够请剧团在家唱戏的,家业肯定殷实。
你猜对了,他家的成分是地主。谢裕寿说。
我是地主后代,没有做人的资格的。谢华昌低头说。
不能这么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说,八岁那年,他睡在县城天主教学校的楼板上,听马蹄响了一夜,第二天,就解放了——
天一下就黑了,我要回家。出门拐弯,就是火烧坪。谢裕寿说,当初我们就在这里排练桂剧。走进巷道,看着谢华昌家族的民国建筑和清代门楼,心想,之后他住在哪里呢?带着这个疑问回了家。当然是夜不能寐了,心太小,装不了事。
再次来到锡爵村,我让谢裕寿带我去看看谢华昌住的房子。在一座正房子的左边,靠着几座矮小的瓦房,相当于以前的杂物房,谢裕寿指着里面一间说,那就是谢华昌的房子。那么小?怎么住得下一家人?谢裕寿再指了指旧房子对面的两间小红砖房说,那是他后来修的。
他不在家。
跟谢华昌搭戏的花旦黄发群回来了。谢崧恕开了辆小三轮车把她接来。他们说,她都八十岁了,嗓子还跟做姑娘时一样好。
她面目清秀,身材娇小,腰板挺直,除了头发有些灰白,看不出老相。她爱笑,一两句话就笑,跟个姑娘家样。语速快,她说,打小我就喜欢看戏,最爱看小姐,花脸出来就别过脸去不看。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喜欢小姐喜欢得不行。花旦角,就是天真烂漫、活泼开朗的妙龄女子,背后留你这样的青丝。她扳了扳手指说,从二十岁开始唱花旦,到现在已经唱了六十年了,人家笑我“戏婆子”。我笑着说,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永远是个小姐,是个妙龄花旦呢?她说,我很喜欢穿上花旦衣裳,戴上花旦的头饰,往台上一站,觉得自己就是另外一个人了。刚在台下跟人聊得泪流满面,眼泪一抹,到得台上就会笑靥如花。台上台下两重天呢。你过得不好吗?谢崧恕接过话说,她生养了六个小孩,丈夫在兴安上班,工资少,没有多少口粮,缺少劳动力,孩子吃不饱。后来分田下户,她一个人种那么多田地,很不容易。多亏了剧团的演员,她说,一帮人来帮我插秧,三亩七分田,半天就搞完了。我爷爷在桂林剧团拉弦子,我母亲也喜欢喊一两嗓子。十二岁那年,我想去学唱戏,但是我姐姐不同意我去,对母亲说:干什么不好,偏要给她去做戏婆子。后来锡爵村剧团成立,我带着吃奶的女儿去学戏,表演时把女儿放在盔头箱里,别人晓不得,出场时衣服往里一丢,女儿在箱子里哇哇大哭。大冬天,观众都提着火箱来看戏,穿上薄薄的戏服,登上戏台就不觉得冷。早上没戏的时候,总是被村里的大妈拉去喝剁剁茶,还有很多老人要认我做干闺女。看戏的时候,这些干娘就骄傲地对旁人说,瞧,台上唱小姐的就是我干闺女。也还有一些人领着自己的孩子要认我做干娘。她们遇到我就从口袋里搜出点零食,或者一个煮鸡蛋来塞给我。那时好开心,什么烦恼事都抛下了。
水粉往脸上一打,汗都不出。扑上香粉,打上腮红,箍紧头饰,眼皮往上一拉,就有了凤眼,甩着青丝,挪着碎步,一扬水袖,风情万种。她边说边走(腿间像夹了个鸡蛋),一位大家闺秀便逶迤而来。

谢崧恕与谢云妹

锡爵村民居
唱一段吧。我说。
好,我试试。
唱完一段,她跟谢崧恕说,二胡音调太低,嗓子唱不出,让他换京胡。
谢崧恕回去拿来京胡,竹筒比二胡小很多,音高很多。她要唱难度极大的《杏元和番》,京胡一开腔,音便极高,起板走完,我担心她能否唱得出来,没想到她嗓子一扯,声音亮丽婉转,第一句就咿咿呀呀的,转了东、南、西、北四个唱腔,转得字正腔圆,技艺非同寻常。一路唱下来,没打半个囵囤。几十年没唱,以为忘掉了,没想到还能唱出来。
谢崧恕说,她年龄比我们大,记性比我们好,嗓子一点没变,不得不服。
我想,这些年轻的表象跟她一生饰演花旦角色有很大关系吧?假如我老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姑娘,到了八十岁,我的记性会不会跟她一样好?我的想象力会不会还能天马行空?我的情感会不会还是那么饱满?
能不能把谢华昌叫来跟黄发群对唱一段?我突发奇想。
谢裕寿说,行,我去叫他。
谢崧恕突然说,华昌受了很多苦,当时他还戴了“帽”,他的戏唱得好,我们去求情,才让他出来唱。他到四十岁才结的婚。华昌在她村里唱戏,那时她守了寡,她也爱唱戏,被华昌迷住,不顾一切跟他来到锡爵村。因为户口没迁过来,她生了孩子都没分到田地。我们跟队里求情,才把田地分给她。华昌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做豆腐和发糕卖,把两个孩子送上了大学。
很快,谢华昌来了。他说,刚从全州回来。听说要唱《梨花斩子》,他连连说不行,太长了,记不住那么多,自从被电倒了一回,记性大不如前了。
黄发群说不要紧,我把词说一遍再唱。她快人快语,边唱边讲,与谢华昌讨论了几处模糊的地方,便来真的了。黄发群用假嗓子唱,谢华昌用本嗓子唱,一个唱兵马大元帅樊梨花,一个唱二路元帅薛丁山,谢裕寿打下手,跑龙套。两人站在谢崧恕右边,一唱一和,全州口音浓厚的念白、反复的曲调和夫妻俩生分地打哈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要杀子,一个要救子,两人翻旧账,打舌战,到闹翻,心理活动细腻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如果懂得《薛刚反唐》这个故事,看起来真是津津有味。还有插科打诨的秦窦二将,念白是地道的全州话,带有丑角色彩,极具喜感。两人求情不得,反而要赔掉自己的脑袋。秦将军反过身来说:二八一吊六啦。窦将军被秦将军唆使去求情的,对着秦将军捞衣扎袖,狠狠地说,这架打不成那就打不成了。粗犷诙谐,生活气息浓郁,地方色彩突出,破了樊梨花一心要斩子的沉郁气氛,让观众有个窗口透气。这样诙谐有趣又沉郁深沉的表演,难怪深受群众喜爱。
小时候,挤不进人群,只在外围敲点丁丁糖吃,突然听同伴喊,快来看,快来看,就要砍头了。听得这话,我吓得面无血色,还往人群里挤,看见高高的戏台上,一个女子凶巴巴的,身穿战袍,头戴插着两根长翎毛的漂亮帽子,背上还插着很多小旗子。一个男子跪在地上,用头甩着长长的发束,发出悲痛的咿呀声。一个花脸手举砍刀,白花花的,对着那男子的脖子。之后一个长胡子老人跟这个男子抱在一起唱了很久,唱得很多人偷偷抹眼泪,也没见刀砍下去。不过,光这个场景,就够吓人了。回家的路上,我前后都不走,只走在人群中间。梦里总是出现这样的镜头,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砍头,为什么唱得那么凄惨,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现在似乎明白了。
谢华昌唱完一段,对我摆手,示意不唱了。
他说,他清唱一段《斩雄信》。
这个角儿是花脸。试了试音高后,他唱:盖世英雄绑将外,呵呀哈呀哈(豪笑),不由雄信笑开怀。单人独骑某把唐营踩,只杀得唐营鬼哭人哀,只杀得血流成河海,只杀得尸横无地埋。誉骑公擒某某不怪,怪只怪,瓦岗一党狗投胎。唐童啊唐童,我与你冤仇似山海,纵是那九泉之下,某也丢不开。
唱完之后,他对我说,雄信三世不投唐。
还唱了一个丑角儿,有难度的《拦马过关》。“……金鸡叫来犬又鸣,打扫了店内把门开。家家户户挂起了招牌,我将招牌挂在店房外……”
我听得有些熟悉,就是他第一次唱的。
之后他还唱了《陈香莲》,角儿是老生,唱的是宰相王燕龄下朝后,街头一民妇拦轿喊冤,宰相决意不袖手旁观的事。
他的心里住着一位英雄,生活中的苦,都在戏台上得到了化解。
去我们村子唱过吗?在我的记忆中,总是跟着大人跑很远的村去看。
黄发群问,你们什么村子?
鲁板桥新八甲。
去过。新八甲有个叫唐昌伟的,在自家院子里搭了个戏台,我们去唱过。
啊——我家就在他家对面。我知道有这么回事,我母亲也常常去看,那是1994年到1997年的事。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回家难得碰上。
我们也是接单到处去唱,没有固定戏台。黄发群说。后来大家都不唱了,连戏服都不要了,我把它们都买了回来。
还是你有心。现在还能不能组一台戏唱唱?
难。谢崧恕说,演员凑不齐,中场(乐鼓)也要很多人。
锡爵村剧团还剩多少演员?
十多个吧。谢裕寿说,两口子唱戏的就有八对。
那,一台简单的戏应该能唱吧?戏服又不用找。

谢裕寿家的照壁
年轻人领个头,事情应该能成。黄发群说。谢崧恕也同意。
谢华昌说,现在谁还想看这老戏。
我说,就算没有观众,也不能否认桂剧的艺术价值,没有观众,它仍旧是我们的瑰宝。2006年5月20日,桂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不能让桂剧就这么躺在“文化遗产”这个词上寿终正寝,它还有星星之火,就不能让它熄灭。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有些发虚。也许真的像唐义武老先生所说,要想救桂剧,只能利用残剩的老艺人创办“科班”,招收儿童强化训练,然后让他们存活下来,桂剧或者还有一线生机。
不过,还有一个锡爵村,住着这么多老艺人,他们吃着香喷喷的大米饭、鲜美的禾花鱼,喝着吴茱萸茶,赏着各类花木,延续着中国人特有的民居文化和戏剧文化,让我零距离感受中国的魅力,再次走进深远的梦境,心头的缺口得到些许弥合,也算是一件幸事。锡爵村的人还能自守自觉地活在中国人的梦境里,多多少少,算是一个神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