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浩波:先锋二字,何其难也
□ 王 琪
沈浩波:先锋二字,何其难也
□ 王 琪

名家档案
沈浩波,诗人、出版人。1976年出生于江苏泰兴,199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为世纪初席卷诗坛的“下半身诗歌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出版诗集《心藏大恶》《文楼村记事》《蝴蝶》《命令我沉默》。曾获第11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人民文学》诗歌奖、《十月》诗歌奖、中国首届桂冠诗集奖、首届“新世纪诗典”金诗奖等。
伪抒情与学生腔
王 琪:你好浩波兄!最早知道你的大名,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某期《大学生》杂志诗歌栏目读到你的诗,当时你取笔名仇水,以北师大中文系学生的身份初涉诗坛。时过境迁,几年以后,你诗风骤变,给人一种“不曾相识”的感觉,请问你是在怎样一种心灵背景或什么影响下完成了这种变化?
沈浩波:感谢王琪兄,还记得我从学生腔十足的写作向一个专业诗人的变化过程。很多人对我的阅读,都是从“下半身诗歌运动”以及《一把好乳》这样的作品开始的,更早一些的话,也无非是追溯到,我1998年写的那篇被称为“盘峰争论”导火索的文章——《谁在拿90年代开涮》。这篇文章是我进入所谓中国诗歌界的起点,也因此成为我个人诗歌写作史的起点,这令我非常骄傲。我写作的起点和其后的个人诗歌发展,都是发生在中国当代诗歌的主脉络上,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与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主脉络同呼吸、共命运。而你提到的,我使用笔名“仇水”时期的写作,应该算是我个人的“史前期”。你还提醒了我一点,我好像就是从《谁在拿90年代开涮》这篇文章1998年在北师大《五四文学报》和《中国图书商报》,1999年在《文友》和《东方文化周刊》发表时,才正式将我写作时的署名,从笔名“仇水”,更换成了本名“沈浩波”。因此,“仇水”这个名字,代表着我个人的“史前”写作,而从《谁在拿90年代开涮》起,署名“沈浩波”的写作,意味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杀进了中国诗坛。没错儿,是杀进来的,从引发诗坛近20年来最大规模论战“盘峰论争”的《谁在拿90年代开涮》,到新世纪第一个影响力巨大也争议巨大的诗歌流派“下半身诗歌”,再到至今万夫所指的《一把好乳》,我不是拿着刀,也不是拿着剑,是抡着板斧杀进来的。
有些人一辈子都没能走出其写作的“学徒期”,一辈子都在写着某种“学生腔”的诗,一辈子都活在自己写作的业余期,从未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个人写作,心智的不成熟,精神的不独立,理念的陈旧与落后,都让他们永远进入不了写作的“成年期”。我从1996年在北师大中文系读大一时开始写诗,写了两三年学生腔的诗,1998年的《谁在拿90年代开涮》,令我从理念成功进入成年期。2000年,伴随着“下半身诗歌运动”的发端,进入个人写作的成年期。是什么令我发生了嬗变?当然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那种青春期的伪抒情,和象牙塔里毫无人生重量的造句游戏、修辞游戏不是诗,而是诗的敌人。
让我觉得可怕的是,快20年过去了,我现在读到的很多大学生诗歌,尤其是那些所谓名校的大学生诗歌,依然和20年前我刚刚写作时,北京的那一批大学生诗人一样,不是青春期无病呻吟的伪抒情,就是造句和修辞。而且那帮玩儿造句和修辞的学生腔们,和20年前的学生腔们一样,都把诗写得整整齐齐,每段同样的行数,每行差不多的字数,从上到下摞一块儿,看上去像砖头,也像棺材。20年来,那几所所谓名校的学生们一直在写着这种棺材体的诗歌,毫无长进,这一定是这些学校的诗歌传统和诗歌教育的问题。
自由度与反抗性
王 琪:你所理解的先锋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他和口语诗歌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沈浩波:在我看来。先锋有四大要义:自由、反抗、创造、生命意志。
要把诗歌往自由的方向去写,要有内在的心灵自由和外在的语言自由,当然,没有内在的自由也就不可能抵达外在的自由。和艺术一样,诗歌也永远向往着自由,一直在向着更自由的方向发展。自由是一种永恒的艺术追求,但又永远无法完全实现,这才是我们向往自由的原因。每个先锋派都将自由往前推进了一点。为什么今天的很多诗人越来越推崇布考斯基,因为他把诗歌的自由边界向前推进到了一个令一般人无法企及的程度。所谓自由,并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更不是乱写胡写,要与自己的心灵完全匹配,有什么样的内心才有可能抵达什么样的自由。不忠诚于心灵的写作抵达的不是自由的诗性,而是诗性的丧失。这种自由,是最难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反抗,反抗束缚我们心灵的各种枷锁。反抗传统美学的枷锁,主流价值观的枷锁,世故的枷锁,功利的枷锁,并在这种反抗的挣扎和压力中,形成创造。艺术的真谛永远不是对经典的摹写,而是创造出新的美。毕加索之所以伟大,正是基于其反抗与创造。对于一个有更高追求的诗人而言,必须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诗歌,辨识度高的诗歌,一看就是你的,只能是你的,而不可能是别人的作品。经典一旦写出,就会成为自己以及后来者的枷锁,经典越来越多,枷锁就越来越多,能打破这枷锁,别开生面,创造出新的美,才能被称为杰出。经典的仿写者,原创的反对者,永远不在真正的艺术发展脉络之中。
正是由于这牢笼之坚固,传统之强大,既往经验之顽固,反抗之艰苦,创造之难,唯有强大的生命意志才能催发。没有内在生命意志的先锋,一定是伪先锋。内在的生命意志和外在的语言自由相结合的先锋,才是真先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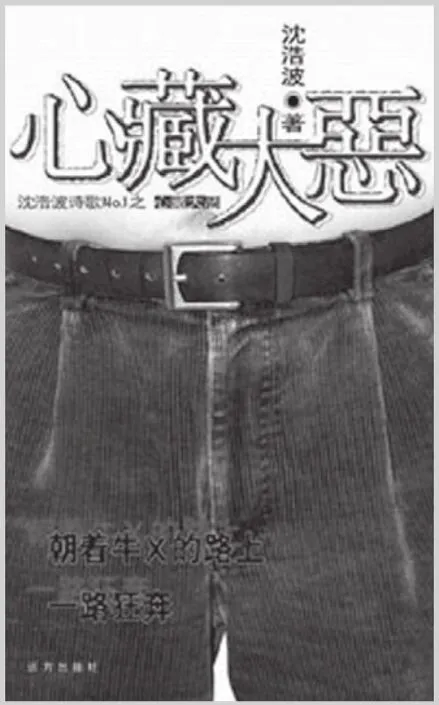
中国的诗人中,往先锋方向去写的很多,但真正在我前面所说的四大要义方向上落实了先锋的,其实凤毛麟角。5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欧阳昱算一个;第三代的诗人中,最有可能算一个的是杨黎,但他写着写着就只能算半个了,废话主义误了他,非要给自己的写作加一个主义,加一个框框,加一个牢笼,等于自我阉割;早期的韩东有先锋的部分,《有关大雁塔》和《你见过大海》完成了先锋的使命,但韩东在整体上更是一个经典主义的诗人,不算先锋派;第三代之后,伊沙算一个,是个大个儿的先锋;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我算一个;8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春树算一个。
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先锋派,包括并不先锋的韩东,其先锋的部分都是用口语完成的。因为口语天然与自由相关,与反抗相关,所以更能承载先锋的心灵。再往世界看,金斯堡和布考斯基,只能是口语的,出不了非口语的金斯堡和布考斯基。口语也好,书面语也好,都可以写成杰出的诗篇,都可以成就伟大的诗人,但伟大的诗人不见得就是先锋的;但先锋的伟大,一定比不先锋的伟大要更伟大一些。至少在汉语中,书面语几乎不可能抵达先锋,这就好比,你穿着一副贞操裤衩,还搞什么搞?
很多诗人,在其最好的生命岁月都是先锋的,但当他们自以为成长和成熟了,就越来越背弃先锋。殊不知,当你背弃了先锋,你的写作就再也回不到你本能抵达的最好,因为你背弃了最高级的文学意志,那是你生命中本来有的,但被你掷若敝屣。
当年和我一起发起“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一群年轻诗人,个个才华横溢,但今天还有几个敢说自己的写作仍然是先锋的呢?下半身时期的他们,都曾经是先锋的,“下半身”这三个字,就意味着先锋。没有几个人敢说自己仍然是“下半身”了。那我就告诉你们一个残酷的秘密,仍然敢说的赢了,改弦更张的输了,越写越软的输了。如果说2000年到2004年,我们的“下半身”时期的先锋,还带有某种青春期的本能色彩的话,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要有能力将其转化为拥有成熟心智的、自觉的、内在的、本质的先锋,而不是往后退。先锋二字,何其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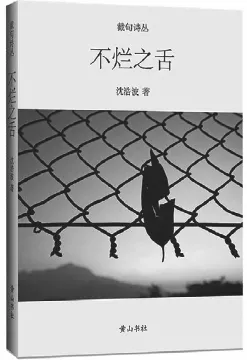
先锋性与经典性
王 琪:你的诗歌的确充满了实验性,走在时代的前沿,和我们绝大多数人接受的传统教育相比,你认为这是一种冒险的事吗?
沈浩波:我没有觉得我在冒险,也没有觉得我在实验。都没有。我觉得我这么写是对的,我觉得我就应该这么写,我觉得这么写就是在通往某种我理想中的写作。所以,不是冒险,不是实验,而是本该如此。我并不认为,先锋的实现,需要依靠冒险和实验,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不觉得梵高在冒险和实现,他知道自己应该那么画,我也不觉得马蒂斯和毕加索是在冒险和实现,他们胸有成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不过世界跟不上他们。就诗歌而言,惠特曼不会觉得自己在冒险和实验,他只能那样表达。布考斯基也不会认为自己在冒险和实现,他才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呢,就这么写了,一写就对了,自由的边界就又被推远了一些。
冒险和实验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你的先锋性必须匹配你的内心,先要有先锋的内心,然后才能推开自由的边界。我不是一个实验诗人,我认为我所写作的方向,才是处在诗歌发展的真正的方向上。先锋的方向,既是诗的方向,才是美学发展的方向,而不是相反。
王 琪:批评家陈亮在一篇关于你的文章中,认为你正在从先锋写作转向经典写作。你能谈谈他的这种判断吗?
沈浩波:陈亮的这个判断,应该是一种对我的写作的阶段性判断。不仅仅是陈亮,这个阶段有很多诗人和批评家都对我作出了类似的判断。甚至有人认为,我从“下半身”转向了“上半身”。这样的判断,主要是对我近年来某一部分写作面貌的一个响应。在这一个阶段,我确实写了不少使用书面语的诗歌,并且更广泛使用意象、修辞、抒情等经典化写作的常规武器。其实这一路的写作,也是贯穿我的全部写作时间的,从1999年到现在,熟悉我写作的同行会知道,我一直有这样一条写作脉络,从未间断。只不过以前被我那些口语的、先锋的代表作覆盖了,不那么引人注目。而近年来,随着这一路写作的不断成熟和丰富,开始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我并不排斥任何一种写作方式,很愿意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达不同层次的内心,这也是我对自由的理解,我不想拘泥和束缚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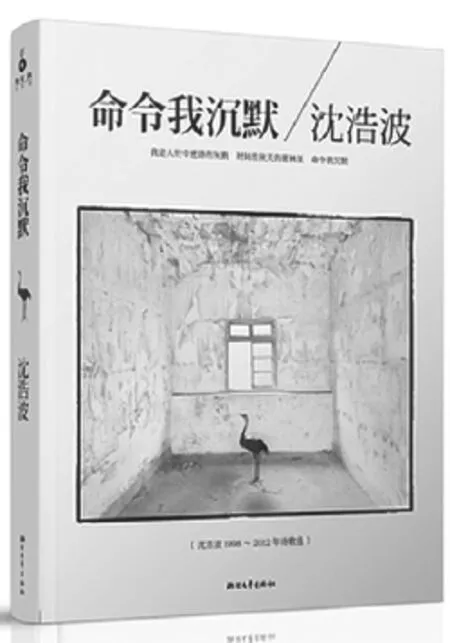
但我很清楚,这并不是我个人写作的主线,我的心灵主线和写作主线就是从《一把好乳》《淋病将至》到《饮酒诗》《文楼村记事》,到《玛丽的爱情》到《理想国》《时代的咒语》,再到《花莲之夜》《在圣方济各圣堂前》这样一条先锋路线。我的长诗《蝴蝶》是我这两条写作脉络的一次大融合,从整体上我也认为先锋性很强。
正因为我的写作中一直存在着这两条写作脉络,才让很多论者和同行摸不着头脑,认为我的写作变化多端,其实没那么多端,说破了就是两端,先锋的和没那么先锋的。当然在很多时候,这两种向度也在不断地融合。也正因为有着两条脉络并存的写作经验,我才更深刻地知道,口语对于先锋的意义,也更深刻地知道,先锋对于一个诗人的意义。
当我首先是一个先锋诗人时,那些不那么先锋的诗歌,能够构成我个人写作经验和心灵经验的非常重要的补充,令我的写作更加具备心灵的全息感;但如果我只是一个经典主义的诗人,那我就只能是一个二流诗人了。也就是说,我的先锋主脉令我在非口语端的尝试变得有了更大的意义,也令我在非口语端所获得的另一种写作经验在融合进我先锋性时,能够产生某种独属于我的化学反应,对我来说,这同样意味着一种创造。我不认为除了我之外,中国还有第二个诗人有可能写出《蝴蝶》这样的诗歌。
往更深刻地剖析自己的话,我其实是一个矛盾体,既热爱和理解杜甫,我认为他是一个完美的囚徒,被规驯的完美囚徒,我热爱这个囚徒。也热爱和理解布考斯基,他是真正追求自由的诗人,绝不允许自己被任何既有的人类价值观规驯。他在诗中操守一切,包括他自己。我更亲近布考斯基,但又向往杜甫。我最近在一首名叫《囚徒》的诗中写过这种感觉,我是天秤座,杜甫和布考斯基一边一个,扯着我的睾丸!这既给我的写作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令我挣扎,但这种挣扎,也未必不是一种财富和可能,我自己对此还下不了结论。走着瞧吧,最后总是要扯出个结果来的。
精神锋芒与诗歌秩序
王 琪:的确,你的作品本身《一把好乳》《心藏大恶》《玛丽的爱情》《约翰不吃煮鸡蛋》等,无论是诗歌的标题,还是诗歌作品,无不显示出你超前的写作意识,和胆大、自由、丰富的创造力。你希望你的这种探索精神和诗歌观念,会给更多的年轻的写作者会构成怎样的启示?
沈浩波:谢谢你提及我的这部分作品。它们是我诗歌的锋刃,是最锋利的部分。一个诗人的写作,应该有更多这种锋利的部分,应该更锋利。我很庆幸,我的诗歌是有锋刃的。四平八稳的诗人,永远没有这样的锋刃。精神不先锋,写作理念传统的诗人,也永远不可能有这样的锋刃。诗歌的锋刃来自精神的锋刃,你首先得磨砺自己精神的锋芒。你得是一个有锋芒的人。你得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睥睨。我非常热爱鲁迅,鲁迅之所以能成为鲁迅,因为他“一个都不放过”地骂遍文坛,绝不给自己任何妥协的余地,精神的刀尖永在砥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干得还远远不够,称得上锋刃的诗歌还不多。我得更坚定地弃绝自己的世故、软弱和庸俗,永远不要和平庸为伍。在这个世界上,平庸每天都在磨损着我们的内心,不但得经得起这磨损,还要在和磨损作斗争的过程中养心,磨刀般养心,砥砺自己的精神,奋扬自己的锐志。古人说得好:工夫在诗外。
王 琪:前不久,你主编的“中国桂冠诗丛”第一辑,出版了严力、王小龙、王小妮、欧阳昱、姚风等5位优秀诗人的作品集。让我感兴趣的是,你在谈及出版缘起时说了一句:不要让好诗成为秘密。为何口出此言?是否有别的含义?
沈浩波:将这套诗丛命名为“中国桂冠诗丛”,当然包含着某种重塑当代诗歌史的野心。所有当代史一定都仅仅意味着浮云遮眼,而所有试图厘清当代史的努力,也都无法在当代呈现出其真实的意义和成就,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按照自己的审美尺度去为之努力。
我想为之做的努力就是,尽我自己所能,穷尽我自己的视野,通过诗歌出版的方式,去呈现一种可能的真相。既然是想呈现真相,那就意味着,至少在我的审美尺度里,当代中国诗歌在它的表面所呈现出来的那些秩序是一种艺术的假象,是遮眼的浮云。我看到了我们时代的那些杰出的灵魂,他们诗歌中有诚实、真挚、朴素的内心,有尖锐、先锋的艺术立场,有自由而现代的艺术精神。他们潜伏在时间的迷雾中,忠实于自己的心灵、精神和艺术立场。他们在假象的迷雾之外,在真相的石头之中,在时间的淘洗之中。我想通过出版的方式,向有心的或有缘的读者展示他们的诗歌,呈现一种我自己想象中的,可能的真相。
既然我想呈现一种可能的真相,那就意味着我认为当下中国诗歌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秩序是一种假象。很多所谓知名诗人构成了这样一个虚假的秩序,比如一提起中国当代诗歌就谁谁谁,它形成了一种名单,这个名单在各种诗歌活动中都会形成一种排名顺序,这些都构成了一个秩序。那么这个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呢?
首先是在中国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开始有了一个新时期的文学。在这样的一个文学过程中,在一个文学起点很低的时代,一个萌芽期,稍微有点才华和想法的人,是很容易出名的。那个时候的诗歌受万众瞩目,不像现在,现在我觉得诗歌反而回到了它应该有的位置。就是你不要跟大众娱乐的东西抢话题吧,你不要去跟电视、电影来争夺受众,因为诗歌不是大众项目。但是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尤其在八十年代,诗歌是中国人的主要精神食粮,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事情,实际上是因为那个时期太贫乏了,包括大众娱乐,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大众娱乐机制,所以大家把情感寄托到诗歌这样一个小众的事情上;所以那个时候诗人很容易出名,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可能一首诗就出名了,可能两首诗就出大名了。也可能一首诗里有两句特别像格言警句的诗句就出名了。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是个文学文化水平非常低的时代。在一个非常低水平的格局里你出名了,但不代表你的写作是杰出的,或者放在更严苛的水平下你的写作就不成立了。但出名了就是出名了,因为此后中国诗歌的发展,或者中国社会的发展,使诗歌越来越小众化,可是大家记住的永远是当时出名的那一些诗人,那一个秩序。
第二个秩序,是由学院里的专家、教授推崇的一些诗人,比如玩修辞玩得很好的,不好好说人话的,能够总结出好像有特别大意义的,他们有一套标准。我从来不相信学院里学者、教授的标准,因为你自己连诗都不会写,你自己都没有生命力,你自己都是书呆子,你来跟我谈论什么诗歌。他们会构成一个集体的标准,这个标准也会推举出一个秩序。

还有一个秩序,比如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人民文学》杂志等等这样的官方体系里,他们也有他们的趣味,那么这个趣味是安全的、不能出事、不能越雷池的、保守的,它也有一个秩序。那这样的三种秩序形成一个合流,对于这个三种秩序,我都不认可。我认为它们都有致命的问题,所以它一定是荒谬的。我认为真正的真相是被这样的荒谬所覆盖的,而且从本质上来讲,所有的当代史一定是荒谬的,因为我们离它太近了,离得越近越看不到事实,包括我们学的历史课本也好,一切的东西也好,只要是当代的一定是假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既然当代的一定是荒谬的,所谓当代诗歌史一定也是荒谬的,那就给了我们寻找真相的空间和意义。
我相信我自己的标准,万一我呈现的真相是对的呢?万一我的标准就是正确的呢?至少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而且我至少比学院里的专家或教授的水平要高,我至少比中国写诗的官员的水平要高,我至少比所有官方杂志的编辑水平要高。那还有几个人水平比我高呢?如果我不来做这样一个编选工作,那就意味着,很多作为编选工作的人,他们的诗歌审美水平是比我低的。
写得多与写得好
王 琪:尼采的野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都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浩波兄早年曾有一句诗: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你能具体说说在诗歌写作上的野心吗?
沈浩波:这个问题有点不好回答。我当然是有野心的,但又好像说不清楚了,越来越说不清楚了。年轻的时候,可以用“牛逼”一词来概括,但到底什么是牛逼的呢?写作不是成功学,不需要成功,甚至反对成功。那么,野心该落实在何处呢?越写越好?又太虚了。那么也许就是,如果把一生的写作比喻成一生淬炼一把刀的话,我希望这把刀,刀背够厚,刀刃够锋利!写得多、写得好、写得丰富、写出人生、写出生命,此为刀背!更先锋、更锋利、更能刀口滴血,此为刀刃!
王 琪:能和浩波兄在我们《延河》下半月谈论诗歌,非常高兴,这个话题似乎远没有结束,也不会结束。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沈浩波:不客气,有空了咱们再聊。在此,也祝愿所有关心《延河》杂志的青年朋友,诗心永存,诗心不老!
沈浩波是一位个性鲜明的诗人,他的反抗意识与独立精神,造就了他诗歌的先锋性和叛逆性。这种遵从于内心地去写,实质上是在看似一种闲散无畏的写作状态中,获得了更广阔的自由空间。这对于众多写作者来说,我以为,仍然面临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
纷繁驳杂的生活, 永远是我们写作的土壤,是我们寻找素材、取之不竭的源泉。假如沈浩波的见解对我们有所顿悟,那么,开启我们更为宏阔的视野,适时调整并改变一种写作思路,算不算这次访谈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责任编辑:阎 安 马慧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