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与虚的交响
齐珣
一座理想的城市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相反,一座糟糕到走向毁灭的城又是如何?理性让社会森严有序到不容一点差池,也会让“众生”冷漠猜忌,甚至不敢流露半点真情。感性的光辉可以温情脉脉地调和着一成不变的刻板,也能让人迷狂到物我两忘、虚实难分。这部小说则是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 1940—1992)在这两个极端中弹奏的一曲奇谲的交响曲,小说中霍夫曼博士建造了一台机器来生产欲望,使得都市中的人因此沉沦于爱欲,幻觉浮现,魅影重重,商业生产、政府公务都停滞不前,全城陷入恐怖与混乱之中。一位小公务员受部长的委托前去寻找霍夫曼博士,并不惜一切代价摧毁这个魔鬼般的机器。在公务员德赛得里奥寻找的途中,危机四伏,他原本相信秉承理性之光定会完成使命,拯救全城的混乱,却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博士的女儿——阿尔贝蒂娜。安吉拉·卡特的这个故事在“寻找”主题下展开,却在虚虚实实中梦幻地跳跃,实在让人称奇称快。
“ 一切我还记得。没错。一切我还完完整整地记得”,就像那些陪伴我们入梦的无数个童话故事一样,老德赛得里奥给我们讲了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可越是强调就越值得怀疑,这个说故事的人杜撰了多少“故事”,故事之外的安吉拉·卡特又企图让我们看到哪些“杜撰”,虚实悖谬的游戏在小说一开始就上演了。
德赛得里奥从混乱迷狂的城市出发,秉持着最后一点理性之光,途经欢快明丽的S小镇。在算命摊前他找到了一个靠拉洋片度日的瞎眼老人,老人号称这架洋片机能够看到世界奇观,事实上他正是霍夫曼博士当年的基础物理老师。至此,主人公寻找霍夫曼的任务初见线索,透过这架破旧的机器,他看到了七幅触目惊心的哥特式画片:有艳丽斑斓的丛林,有露骨色情的生殖器官,也有阴森血腥的无名女尸。这里或许是暗中契合了《俄狄浦斯王》中明眼人是瞎眼人的典故,安吉拉·卡特用这七幅画预言了故事的发展脉络。透过图像预言未来,经由符号解码成语言是现代人的把戏。电影作为如今一种活跃的艺术形式是最好的证明,相信现代人都有这样的体验,面对现实发生的事件忽然会联想到自己在电影中看过的情境。诚然,个体生命无法重新来过,却因为电影的世界延长、透支了生命。电影导演虚构的影像不仅反映着未来,甚至支配着未来的我们对某一事件的认识。安吉拉·卡特是短篇小说的大家,她将这七幅图景幻化成一场场有毒气的烟花盛会,是那么璀璨又是那么短暂,布下整部小说运行的线索,其中阿尔贝蒂娜的出现就是霍夫曼博士为德赛得里奥藏下的一副毒药。

阿尔贝蒂娜是博士的女儿,从出现在德赛得里奥面前起,就迷住了他。她时而婀娜动人,时而楚楚可怜,时而变身成一头野兽,仿佛她也是受欲望机器操控的玩偶,幻化躯体,魅惑人心。与其说德赛得里奥是部长选出最理性、最具独立判断力的杰出部下,不如说他根本没有体会过情欲的馥郁芬芳。在阿尔贝蒂娜的陪伴下,他们相伴相拥穿过了野人围困的原始丛林,回到自己出生的部落,甚至与神话中的人物相会,目睹了马戏团色情冷血的游戏。就像所有沉沦爱情的男女一样,庸常的生活都是梦幻的奇遇,但德赛得里奥的性高潮却迟迟不来,直到抵达霍夫曼博士的实验室。一场有关理性与欲望的对抗在小说的最后终于要揭开分晓,博士设置了最后的关卡,一旦这对情侣享受了欲望之欢,这台魔鬼机器就会打开最后的机关摧毁整座城市,幸运的是,德赛得里奥在最后的时刻醒来,杀死了这对父女,摧毁了欲望机器。
惯常的故事结尾往往以“正义战胜了邪恶”告终,各位读者若是也将其混为一谈则埋没了卡特的才华。细数英国众多的女作家,从勃朗特姐妹的洞察现实,到伍尔芙的冷峻艰涩,如果写出《金色笔记》的多丽丝·莱辛被誉为是英国文学的“老祖母”,那么这位熟练掌握拼贴、戏仿、重构技法的安吉拉·卡特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怪阿姨”。 她凭借旺盛的精力整理出了全世界风俗故事的合集——《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涉及非洲、南亚、北欧等多个区域,同时改写、翻译了大量的童话故事。在她的童话王国里,嗜杀成性的蓝胡子最终被妻子和赶来的丈母娘开枪打死,白雪公主的父亲对母亲言听计从,小红帽则是与狼人关系亲密无间。因为她的笔法前卫新潮、故事凶险刺激,无法想象年轻的母亲怎样在深夜用她的故事温情说教,或许这些故事从一开始就是写给大人看的。中世纪暗黑色彩的哥特风格加上锋芒毕露的女权主义视角奠定了她在文坛别具一格的地位。尽管这些华美到极致也幽暗到极致的故事依然在今天被评论界视为卡特的代表作,但翻开她的这部长篇小说,则会看到一个更加成熟、更加深刻的卡特。那里的卡特已经不是一位单曲作家,而是能够和谐演绎一曲交响乐的灵魂歌者。
1969年,安吉拉·卡特倍感婚姻的沉重,拿着一笔毛姆奖奖金只身前往日本行游,没有朋友,语言不通,文化背景悬殊,这个为写作而生的女子对世界的忧思与关注变得更加细腻动人。她努力学习日语,却怎么也学不会,这使她更加依靠简单的符号与人交流。这些生活的印记也同样反映在这部旅日期间的作品中,瞎眼老人用看洋片的方式预言了小说走向;歌剧、交响乐等众多不依靠语言实现表达的艺术元素都成全了这部小说。同时,东方文化的相关思想也在作品中有力地体现着,比如霍夫曼博士的妻子是中国人,异常痴迷于玄学八卦,他们的女儿阿尔贝蒂娜甚至会背诵先秦典籍。东方哲学对卡特而言意味着阴柔和神秘,相反卡特在《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中呈现的美是张力之美,在这场真实与虚幻、理性与感性的角逐中,东方哲学恐怕是最好的内在调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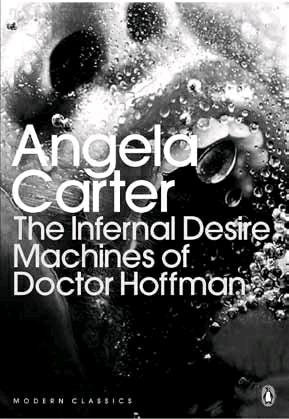
写有趣的小说而不囿于象牙塔内的学术研究是安吉拉·卡特一贯的自我要求,她做到了。她的作品从一出版就深受好评并摘得奖项无数。她曾担任布克奖评委,被 《时代》周刊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1992年,安吉拉·卡特患癌症去世,她逝世后的三天里,作品被抢售一空,该年甚至被媒体称作“卡特年”。1996年,英国更是将一条街道命名为“安吉拉·卡特巷”。卡特的作品尽管在国外赞誉有加,但在中国却仅限于英语研究的学者知晓。2000年以后,逐渐有学者译介推广安吉拉·卡特,余华、格非、张悦然等当代作家都曾公开表示过对安吉拉·卡特喜爱不已。当中国读者有机会认识这位 “怪阿姨”时会发现:她对那些昔日伴我们入梦的童话略施魔法涂涂改改,有时变得恐怖,有时变得疯狂,有时打破了一本正经。2015年,这本《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有了中译本,这部作品像一棵繁茂的大树,读者能够找到卡特此前那些短篇小说的枝叶,也能领略一个更加厚重的作品。对中国读者而言无疑这是一本迟到的书,但作品自身的超前性与未来感似乎又像是在等待历史的验算。
如今,科幻文学自成一家。中国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获奖鼓舞人心,电影《魔兽》上映以来热度不减,经典科幻文学系列《魔戒》三部曲早已成为高校学生毕业论文的热门选题,这些都证明着科幻市场前途无限。卡特的《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不热衷于打造一个逼真的虚拟世界,却深入到了科幻文学的骨髓,揭示了虚实之间的对抗。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科幻作品只有在虚拟的空间内阐述复杂的人性,才能真正激发读者内心涌动的热血与感动。或许正因为那个世界子虚乌有,用想象搭建的乐趣才得以生成,我们才得以在那个陌生的世界中得到更加深邃的思索。人类如何在亦梦亦真的社会中实现精神的充实已经成为一个有必要思考的现实问题。卡特没有机会见证科学家如何让Ai机器人观看美剧 《生活大爆炸》以实现人机对话的准确性;她也不曾听说AlphaGo是如何打败围棋大师李世石的;VR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游戏、影视、医疗等多个领域,以希求通过虚拟画面带给用户更逼真的体验。就像霍夫曼老师的洋片机预言了小说,这个了不起的“女巫”早已料到这个时代的动向。如果科技的发展让虚拟愈加真实,那么政治权力是否还具备制约社会的可能,人类的伦理问题恐怕会遭遇更大的危机。这些矛盾都在这部书中先验地彰显,阿尔贝蒂娜向所有现代人露出毛骨悚然的笑。

